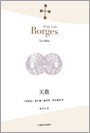 |
编号:S63·2170911·1418 |
|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 |
|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30.00元亚马逊14.00元 | |
| ISBN:9787532772070 | |
| 页数:101页 |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韵律、奇巧比喻、惊人感叹,也写不出结构精巧或者长篇大论的文章。我只能写点通常所谓的文人诗。语言几乎就是一种矛盾。智能(头脑)通过抽象概念进行思索,诗歌(梦境)是用形象、神话或者寓言来组构。文人诗应该将这两种过程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博尔赫斯在《天数》里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当然,对其效果,显然,不无怀疑。《天数》在开篇强调“智能(头脑)通过抽象概念进行思索,诗歌(梦境)是用形象、神话或者寓言来组构”,而博尔赫斯宣称自己在书中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
《天数》: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
你不是别人,此刻你只是
自己的足迹布下的迷阵的中心。
——《极点》
此刻是一九八一年,此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四月二十九日,博尔赫斯写道:“文学创作可以教会我们免犯错误而不是有所发现。文学创作能够揭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严重局限。”什么样的错误无法避免,什么样的无能和局限会被自己揭示?提出一个问题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韵律、奇巧比喻、惊人感叹,也写不出结构精巧或者长篇大论的文章。”没有优美的韵律,没有奇妙的比喻,没有惊人的感叹,博尔赫斯说自己只能写点所谓的文人诗,一种自谦,并非是文人诗自身的不足,当一种体裁结合了抽象概念进行思考的智能和用形象、神话或寓言构建的梦境,它本身就是某种完美的代表,自谦反而变成了自信:“这个集子里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当然,对其效果,显然,不无怀疑。”
对于文学创作的提问,用文人诗来回答,从文字走向文字,博尔赫斯像是故意绕过了一个圈,而所谓的错误,所谓的无能和局限,依然没有做出回答。而不管是头脑在思考,还是诗歌构建的梦境,其实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就像那个悬置在文学里的问答一样,是从现实意义上抽离出来:可能犯的错误是不是在有生之年没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人的无能和严重局限是不是无法挣脱时间的约束?或者可以将四月二十九日的“序言”看成是对于生命的喟叹:将死之人如何在诗歌世界里延长时间?如何用文字留下永恒?
半个月之后,博尔赫斯在“题词”里终于试图将无能和严重局限变某种希望,“题词被认为是一种付出、一种赠予。除了出于善心施舍给穷人的不图回报的钱币之外,一切赠予都是相互的。”因为施赠者没有失去赠品,而被赠者又得到了赠品,也就是说,给予和接受变成了同一件事,甚至以双倍或多重的方式延续了意义,而博尔赫斯想要把文字赠予的是另一个人:玛利亚·儿玉,他在五月十七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深情地喊道:“玛丽亚·儿玉,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您的名字。多少个清晨,多少处海域,多少座东方和西方的园林,多少遍维吉尔。”
她是自己口头文字的记录者,她是自己行走万里的拐杖,她是自己看见世界的眼睛,所以在这一份题词里,博尔赫斯在付出和赠予中,感觉到的是生命在文字的保留中得到了延续,这种延续就是“教会我们免犯错误”,就是“揭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严重局限”,一种赠予的关系建立起来,似乎一九八一年也不再是一个可能走向生命终结的时间刻度——即使离博尔赫斯的逝世也只有五年的时间,但是在不通向未来的此时此地,在文字可能永恒的希望中,博尔赫斯甚至是平静的。
但是那面镜子还在,那场梦境时时困扰,那把剑真的已经锈迹斑斑,博尔赫斯已经无法看清世界却还在看见,选择遗忘却总是走向回忆,一粒药片能够“将整个世界抹去并制造出一片混乱”,为什么博尔赫斯还会留下几滴眼泪,活在“哀歌”的基调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一个孤独、深情、苍老的人,/刚刚躲在屋子里面/为万般世事呜咽。”他流下了眼泪,他以为没人看到,“就连镜子也不知晓”,但是却留在了文字里,“那眼泪是在为一切值得痛惜的事情哀悼”;能够在忘却夜幕的甜蜜景观中发现存在的意义,为什么博尔赫斯还会想到和命运一样的“天数”?“天数有定,谁也不能改变,/你已经到了限定的终极。/即使打开世界上的所有窗户/也于事无补。晚了。你再也找不到月亮的踪迹。”这可能是“最后的机缘”?镜子里不再是自己的那张脸,不再想到另一个的监视,可是当那只叫“贝珀”的宠猫站在镜子前,为什么博尔赫斯还是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幻象?“我们人类又是/哪个天堂生成之前的亚当、/哪位不可探知的神明的破碎镜子?”
一粒药片制造的睡眠,一间房子掩饰的哭泣,一只宠猫在镜子前的幻象,其实都是博尔赫斯对时间迷宫的某种逃避,“我不可能有新的作为”,因为开始一遍又一遍演绎同一个寓言,已经开始重写已经重写过的诗句,已经开始复述别人说过的话,每天夜里做着同样的噩梦感受迷宫的困锁,在茫茫黑夜的同一时刻有着同样的感受,是不是那种令人恐惧的被复制命运又将袭来?博尔赫斯说失眠是痛苦的,“失眠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满怀恐惧地计数那恼人的凄楚钟声,是徒然地希冀着让呼吸平和,是身体的猛烈翻动,是紧紧地闭上眼睛,是一种近似于发烧的状态而且当然并不清醒,是默诵多年以前读过的文章的片断,是知道别人熟睡的时候自己不该独醒,是渴望进入梦境而又不能成眠,是对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恐惧,是懵懵懂懂地熬到天明。”但是长寿呢,何尝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不是按秒针的跳动来计算的失眠”?“是大海和金字塔、古老的图书馆和连续更迭的朝代、亚当见到过的每一道曙光的重负,是并非不知道自己摆脱不了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名字、对往事的不断回忆、自己没有掌握的西班牙语、对自己不懂的拉丁文的痴迷、想死而又死不了的心情、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现实。”
这是两种形式的失眠,而药片、哭泣和镜子一样是死亡的征兆,所以博尔赫斯说:“我感到有些头晕。/我不习惯于永生。”是因为它们“同时也是梦幻”;所以博尔赫斯说一切都是你自己布下了迷阵,因为“你是那每一个孤独的瞬息”;所以在《圣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启示下,重复是最难以逃脱的宿命,“我是一面静止的镜子的倦怠/或者一座博物馆里的尘埃。”
但是,这种哀叹、悲伤甚至宿命是不是真的是难免的错误?真的是我们的无能和“严重局限”?文人诗总是在的,头脑和梦境也是在的,甚至赠予和获得的人也是在的,所以在现实自造的迷宫里,也一定有可以暂时离开的出口:那个被伊斯兰教的利剑毁灭的“龙达”,在失明的迷茫和庭院的沉寂中,不是还能听到“清幽流水声”?梦境中感觉有点冷、有点怕,感觉自己没有出生过,但是不也是在12个梦境里坚守着“笛卡尔以及他的先辈们的信念”?两座教堂是翻版,山鲁佐德或隐身人的夜晚不是创造了无限的可能?而当购得一部百科全书,即使再也没有可以看见的眼睛,即使只有颤抖不已的双手,那里不也还存在着新的秩序,不是还有“那贯注于对我们漠然又不相关的器物的/神秘的眷恋情意”?
是的,博尔赫斯在寻找“神秘的眷恋情意”,在建立新的秩序,在倾听不被阻隔的流水声。重复的诗句和日子是不重复的开始,“我是地球上唯一的人,而且很可能没有任何土地、人,/乃至于神能够将我欺骗。/也许是某位神明让我承受时光那漫漫梦幻的熬煎。/我梦见过月亮以及我那看到月亮的双眼。/我梦见过混沌初开第一天的黄昏与黎明。”已经发生的事还有另外的可能,就像皮埃特罗·达米亚诺所说的修改过去的奇妙把戏:“如果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南方打败了北方,今天将会回到昨天,李的人马就会于一八六三年七月初在葛底斯堡大获全胜,多恩的手就会写完他那首关于一个灵魂轮回的诗,老态龙钟的绅士阿隆索·吉哈诺就会得到杜尔西内娅的爱情,黑斯廷斯的八千撒克逊人就会像曾经打败过挪威人那样战胜诺曼底人,而毕达哥拉斯也就不会在阿尔戈斯,的一扇大门上认出自己还是欧福耳玻斯时用过的盾牌。”任何应该发生的事都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都是一种永恒的形式,当翻开地图可以看到苏门答腊的形状,当黑暗中划亮火柴就是制造了火焰,当步入江川就是走进了恒河,当望见沙漏就是看到了帝国的覆灭,而玩起匕首就预示着凯撒的暴亡。
“整个历史如同浪涛的回转,/那些往事之所以再现,/因为一个女人亲吻了你的脸。(《赞歌》)”尽管带着哀伤,尽管流着眼泪,尽管在已逝的事物面前博尔赫斯显露了从未有过的沉重,但是,“今天早晨/空气中弥漫着天堂的玫瑰/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香气。”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亲吻了脸,还带来了一双眼睛,一些文字,一种被赠予和收获的快乐,以及让历史吟唱出赞歌的那些事物。一根手杖,被玛利亚·儿玉发现,它是漂亮的,结实的,是轻盈的,当拿在博尔赫斯手里的时候,“觉得它是那个筑起了长城、开创了—片神奇天地的无限古老的帝国的一部分。”于是,想起了“那位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道自己是梦见变成蝴蝶的人还是梦见变成人的蝴蝶的庄周”,想起了“那位修裁竹竿并将其一端弯成恰好可以让我用右手把握的曲柄的工匠”,想起了工匠是不是在翻查着六十四式的卦书——“我们永远都不会谋面。/他消失在九亿三千万人之中。/然而,我们之间却有着某种联系。/不是不可能早就有人设计好了这种联系。/不是不可能世界需要这种联系。(《漆手杖》)”
看见而想象,想象而具有了联系,这便是博尔赫斯的新秩序和神秘的眷恋情意,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博尔赫斯的掌心攥着一颗小小的围棋,这一种东方的弈术所必需,“那如同摆布星宿的游戏”带给博尔赫斯的是另一个迷宫:“我要感谢诸路神衹,/他们让我得见这处迷宫,/尽管我永远都不能探知其中的奥秘。”而在日本神道教里,博尔赫斯发现了神明的力量,“神道的神衹共有八百万,/他们悄然地巡行于天地之间。/那些小小的神明时常会将我们光顾,/光顾而后又倏忽不见。(《神道》)”而俳句里的大山、长夜、琴弦、杏树、名月、宝剑、火焰,让博尔赫斯发现了和罗素提出的集的理论、斯宾诺莎无限样态的实体、魏尔兰的文字一样的神秘的日本,“日本啊,我了解了你的概貌。那个复杂的迷宫……”
手杖、围棋、神道、俳句,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构建了神秘的迷宫,它是逃离了现实的梦境,却又制造了活着的秩序,它是不真实的,却并非是虚无,“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可能是一块柱石或一次战役/或一片天使聚居的天空/或一个神秘而又必需的无限境地/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神衹的欢欣/或另一块苍穹里的银色星系/或一个没有玫瑰形状的/硕大无朋的物体。(《布莱克》)”所以何必执着于真实?而在这离真实的遥远世界里,一种梦想和以及可能的秩序里,博尔赫斯又以返回的方式审视自身,不在镜子里寻找“我是谁”,而是在“没有玫瑰形状”的物体里寻找另一朵玫瑰。
我是谁?我是博尔赫斯,我是阿根廷老头,我是失明者:
见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发展与衰落。
记得泥土的庭院和葡萄藤、门厅和水池。
继承了英语,研究过撒克逊语。
喜欢德语,留恋拉丁语。
在巴勒莫同一位旧时的杀人犯做过交谈。
痴迷于象棋和素馨花、老虎和六音步诗。
用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语气朗诵过他的作品。
了解形而上学的那些著名疑点。
颂扬过宝剑,却又从理性上热爱和平。
并不觊觎任何海岛。
未曾跨出过自己的图书馆的大门。
只是阿隆索·吉哈诺而没有胆量去做堂吉诃德。
向比自己博学的人传授自己并不掌握的知识。
欣羡月亮的光华和保尔·魏尔兰的品德。
拼凑出过十一音节的诗作。
重新讲述那些古老的故事。
用当今的语言整理了那五六个比喻。
曾经拒收贿赂。
是日内瓦、蒙得维的亚、奥斯汀和(像所有人一样)罗马的公民。
推崇康拉德。
那个谁也说不清的东西:阿根廷人。
是瞎子,
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件有什么特别,但是,加在一起却给了我以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弄懂的名望。
——《名望》
博尔赫斯排列了一个有过过去的自己,书写了一个还活着的自己,即使带来了名望,那是不是也是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之外的自己,不正是和自己有着“神秘的眷恋情意”的人?就像莱茵河,一条是有着固定形状的莱茵河,一个是被想象成在天上流淌的莱茵河,而另一条则是“停留和长存于永恒的现在/并成为在我口授这篇诗作的时候/在德国不息奔流的莱茵河的根基”,所以流逝和存在中,“也许,只有待到死了以后/我才能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名字还是真的存在过。”三条莱茵河是三种秩序,是无数中关系,而我也是那个“第三个人”:“我要把这首诗/(权且借用这个称呼)/献给前天夜里同我擦肩而过、/跟亚里士多德一样神秘的那第三个人。”那个星期六走出了家门,会遇见或不遇见另一个他,也许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也许干了不同的事,也许两个人从来没有发生过交集,甚至“不是没有可能他已经死了”,但是关系却在那里建立起来,“我知道他会有某种嗜好,/我知道他曾经瞩望过月亮”,“他也许会读到我此刻正在写着的诗句,/却不可能知道我在把他提及。/在那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可能成为对手而互相尊重/或者成为朋友而互相爱慕。”
博尔赫斯说,这种关系或者正在在平庸无奇的世界上建立了“一根无尽链条的开端”,就像《一千零一夜》的结构,所以一个人可能是两个人,两个人之外会有第三个人,“肯定会有那第三个人,/就像有过第四个和第一个一样。”关系在扩展,在交错,在蔓延,在改变,就像梦见伊朗石塔的那个梦,“在那间圆形的禅房里有一个样子像我的人在用一种我不懂的文字写着一首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写着一首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谁也读不到被囚禁的人们写下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开端,只要有一种存在,就会无限循环,就会交错重生,就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迷宫——那是世界,是生命,是文学,是梦境,是宇宙,是第一次的无数次,是无数次的唯一一个,是偶然生成和必然死亡的生命,是生命的偶然可能和必然关系构成的秩序,还有什么局限,还有什么无能,还有什么错误,甚至连我都是无能、局限和错误中的一种可能:
如果处我以极刑,我就是那十字架和铁钉。
如果赐我以药酒,我就是那毒芹。
如果要将我欺骗,我就是那谎言。
如果要将我焚烧,我就是那地狱。
我应该赞美和感谢时光的每一个瞬息。
我的食粮就是世间的万物。
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欢乐的全部重负。
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
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
我是诗人。
——《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