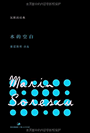 |
编号:S38·2180204·1455 |
| 作者:【罗马尼亚】马林·索雷斯库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亚马逊21.60元 | |
| ISBN:9787208110809 | |
| 页数:248页 |
“这说明他/不会走得太远。/马上就会回来的。”1996年12月6日,马林·索雷斯库因患癌症逝世,年仅六十。诗人死了,或许他的诗歌会一次次回来。马林·索雷斯库,是罗马尼亚著名的先锋诗人,他是以反叛者的姿态登上罗马尼亚诗坛的,因他的写法完全有悖于传统,所以评论界称他的诗是 “反诗”。他的诗让人感觉亲切和自然,亲切到了就像在和你聊天。他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爱情、死亡、命运、瞬间与永恒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与融合、世间的种种荒谬、内心的微妙情感等等都是他常常表现的主题。《水的空白》是高兴先生从罗马尼亚文译出,收录了索雷斯库各个时期的诗作一百多首。《水的空白》隶属于 “沉默的经典”系列诗丛。
《水的空白》:灵魂啊,你走在前面吧
我们居于一个世界,
但为了更加舒适,
使用玻璃墙
将它分成了两个。
——《玻璃墙》
玻璃墙里面有人在体面地洗澡,洗澡的人一直在肥皂泡后面,里面和后面是世界的两个部分,但是是透过玻璃墙看见里面的世界?还是当肥皂泡破灭进入原先的世界?两个世界,是两个人,你和我,或者我和你,但是当他们组成 “我们”的时候,世界到底是被隔离的,还是有一条共通的通道?玻璃墙提供了透明的世界,所以在阻隔中被看见,于是变成了一种夸耀: “我们人人拥有/一套两个世界的公寓”,里面配有不同的家具,而且这个世界,连太阳也可以共享——被分成两个世界,不是隔离,而是增殖。
那是不是反而成为了 “我们”真正的荣耀?生与死,得与失,理想与现实,诗歌和生活,以及脏的水和干净的天空,都是区分了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都在被看见的时候分处在玻璃墙的这边和那边,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如何变成 “我们”,如何拥有这一种增殖的荣耀?还是从洗澡开始,还是从肥皂泡开始, “这个女人/在浴室里藏着什么人。”仅仅是 “这个女人”,不是《睡眠》中那个出现在梦中\有着酷似字母S的乳房的女人, “在事物的语言中,/那表示复数。”所以,她一定是单个的人;仅仅是 “这个女人”,也不是《环节》中最后都会 “彻底忘掉对方”而选择洗手的女人,所以,她一定是做着和自己有关的事;仅仅是 “这个女人”,却是 “我们是两人”的分离的人, “由于我们是一对,最后的一对,/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看法》)”所以一个单个的人,一个做着自己有关的事的人,一个最后一对解体的人,就是在 “那边”的人。
浴室里藏着未知的人,从浴室走出去,隔壁的屋子里也有另一个人,另一个屋子里也有另一个人, “街上的某个地方,/另一座城市,或一片林子,/要不,就在海底。”都有那个躲着的人,他在 “窥探我的思想”,他的眼睛 “盯着表/倾听我不朽的情感”,他在那边,他在彼处,他在透明而可见的玻璃墙另一侧,他在相异的 “我们”里。为什么偏偏是女人?为什么偏偏是浴室?关于爱的分离和解体,总是在发生,找不到别处却总是在别处,于是 “吃进她们成吨的口红后”,上当受骗的女人 “终于找到了报复唐璜的/手段”,她们等待一个单人,等待一个丈夫, “五官俱毒地等他”,目的只有一个: “每天都有一位?在错误地亲吻妻子时/殉职的深情的丈夫/下葬。(《唐璜》”
女人的口红,男人的葬礼,构成了 “最后的一对”的我们变成两个世界的存在,其中毁灭的是什么?是爱情?是诱惑?是神圣?还是现实?最后一对原本应该紧紧结合在一起,应该吧不同的观点变成合一的信念,甚至要打开浴室的门、隔壁的门、另一个世界的门,像水一样形成一体,但是在其中却有着无法弥合的裂痕,水分开了水,天分开了天,我们分开了我们,于是即使彼拉多 “使劲用肥皂搓手”,在洗刷的快感中却让水变黑;于是生于一阵大笑的人也嘲笑过女人,最终死去之后, “人们已为他换过/七个墓地。”于是我用艰涩的字体誊写的文章,只不过是在研究 “我额头上的皱纹”;于是那一只扑火的蛾子竟然在点亮灯盏的时候,以为 “又多活了一个晚上”……
这是紊乱,这是混乱,这是解构,这是对于 “我们”的真正颠覆:没有了神圣,因为耶稣受到了嘲弄, “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迫在十字架上滚动,/就像在一张茉莉花床上,/被迫饮下毒汁,/被迫死去——/被迫在第三日复活,/被迫升上天堂——(《如果水不变黑……》)”而神圣之解构,是因为十字架被扔进了火里,是因为 “火药在搅动”,是因为 “光照的煤渣宣布现代黎明的来临”;没有了文明,当老师问历史,我说 “刚和土耳其人/签订了永久性合约”,老师问重力法则,我说: “一切物体都必然会?落到我们头上。”老师问我们处在文明的那个阶段,我说我们只在旧石器时代,老师问伟大的希望蓝图如何绘制,我说用彩色气球, “每一阵狂风吹来时,/都会有一只气球飞走。”当冲突变成永久,当重力砸中我们,当文明倒退,当未来如气球空无,还有什么是应该属于我们的存在?
一定是现实改变了这一切,那里有 “太多的管子的风琴”,它是危险的,因为即使用麻絮塞牢,将管子截短,甚至拆下它们,那些乐手仍然 “坚持他们的立场”;那里有紧握着铁锹却像是 “手执着戟”的士兵,在他面前, “载活乘客或死乘客——都是一码事!”这里也有被小偷小摸刺激了胃口的 “监视者”,和一条叫奥斯曼的狗组成小分队,去发现和澄清线索;这里有在剧院里不停上演的 “愚蠢咳嗽”, “嘶哑的,刺耳的,破裂的”;这里有廉价的烟草,让人 “不知不觉中/你就度过了/一生”;这里也有遮蔽了最重要词语的 “直角尺”: “在它的衡量下/声音、形象、心灵/都大得有点夸张,/可以用直角尺听人说话,/也可以用直角尺看演出。”
现实里危险的风琴、像戟的铁锹、监视者、咳嗽、直角尺,都是政治有关的隐喻,在这个 “我们”的世界里,其实从来没有透明的玻璃墙,肥皂泡也不会破裂,它是一种颠覆的秩序,它是一种取消了神圣的状态,而在 “我们”之外的 “我”,是不是像女人浴室里的那个人一样,是在别处的?从 “我们”到 “我”,一种分裂,一种孤立,我是点上太阳代替句号的 “创造者”,可是在九十九中元素中,我的炼金术之不过在炉子里 “头投进一天,/投进一年,/投进一个年龄”;我是背负着生命意义的行走者,但是只是一本小书,却也刺痛了我的背;我是穿上盔甲的战斗者,却只是用 “后脑勺”的眼睛 “从背后观察”——因为正像上帝把亚当逐出天堂一样,我之存在的罪名是:超现实主义,即使为了讨好上帝,我将文字写在纸上,在聋子的上帝面前,一切都是无意义,甚至, “我唯恐自己也会变成聋子,/于是,忘掉了想对他们说的话。(《深渊》)”
 |
| 马林·索雷斯库:唯有我还活着 |
“我们”变成了 “我”,是断裂为一种生命的个体,但是在紊乱、混乱、解构的现实中,在充满了隐喻的政治中,在不断迷失的生命里,真正陷入玻璃墙世界的问题是:我的灵魂在别处。身体之外的灵魂,欲望之外的灵魂,失落之后的灵魂,它会呈现怎样的状态,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希望? “只是有关灵魂/我一无所知,/我的灵魂白天总会/滑脱,/就像浴室里的/一块肥皂。(《复写纸》)”白天滑落,是因为肥皂泡后面的世界,可是在历史深处的黑夜里呢,塞内加是尼禄的老师,却受到谋杀案的牵连而自杀,在那间浴室里,当水已经煮开,打着哈欠,望着窗外,在死亡面前,却只有 “无聊地要命”的等待——思想在何处,为什么面对死亡没有恐惧?神圣在哪里,为什么只有无聊才能释放生命?
命名为灵魂,它可能只是在节日戴上面具的一种 “嘉年华”演出,只是 “舔着自己嘴巴的词语”寻找的碎片,只是发出 “类似一些噼啪声”的奇怪存在,只是 “可以估测两只蛾子间的距离”的死亡预兆。灵魂就像拍摄树、石头、椅子之后洗印出来的照片, “所有事物都与我/惊人地相似……”相似而取消了独特性,取消了神圣性,所以灵魂和肉体相似,灵魂和肥皂相似,灵魂和非灵魂相似,所以我最后又回到了 “我们”的世界, “为了避免孤独,/我要让许多东西/入眼睛的圈内:/月亮、太阳、森林和大海,/我将和它们一起/继续打量世界。(《眼睛》)”这种相似性彻底将世界变成了一个 “在别处”的所在,变成了对于命运讽喻的结果:
电车上的每个乘客
都与坐在自己前面的那位
惊人地相似。兴许是车速太快,
兴许是地球太小。每个人的颈项
都被后面那位所读的报纸
啃啮。
我觉得,有张报纸
正伸向我的颈项,
用边角切割着我的
静脉。
——《判决》
从玻璃墙分隔开的不同世界,再到所有事物都惊人相似的同一世界,其实是一种异化,命名的不再是自我,审判的不再是上帝,抗拒的不再是理想,于是遇见椅子便有了进入天堂的可笑预言,有了遇见山将进入椅子的可怕征兆, “避开这一征兆,/避开所有的征兆。(《征兆》)”这一征兆是我,所有的征兆是我们,在一和所有、我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一场梦是一场永远的梦,一片水是无数变黑的水,过去是复制今天的时间,所以历史只是现在的记号: “我也一样,用一个新世纪的/涂鸦在陶罐上留下记号,/如此,4000年的研究者/就能大致确定/20世纪中叶/我曾在地球上生活过。(《陶器》)”所以文明只是一片废墟: “我曾在所有文明的废墟上,/在成堆的写字板/和瓷砖上嚎啕大哭,/那么,此时此刻,为何/不在自己面容的废墟上痛苦呢?(《面具》)”于是,思想只是为了活着: “这么多的思想又有何用,/如果那一刻,从所有的/哲学中,唯有我还活着,/偶然,却真的活着。/摸摸我。(《真的活着》)”
时间、文明和思想,曾经站在那高处,仿佛和上帝、神性一样,俯视着这个世界,但是在玻璃墙的透明中,没有什么可以隔开,在无区分的 “我们”之中,每一个女人,每一个我,每一种爱,都失去了而唯一性,都变成了共有名词,都接受同一个命运——所谓水的空白,像水一样流动,像水一样变黑,再无发区分此岸与彼岸、崇高与卑微,欲望和灵魂,生存和毁灭,死者带着不是我的面具,离开是马上就会回来的状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见了从空中抛下的天梯,那也只不过是天花板悬挂着的一缕蛛丝:肉体太沉重,救赎太艰难: “尽管我瘦得要命,/只是昔日之我的幽灵,/但我想我的身躯/对于这纤细的梯子来说,/依然太沉太重。”但还是发出了 “灵魂啊,你走在前面吧,/慢慢的!慢慢的!”的喊声,因为那些灵魂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在玻璃墙的透明世界里,以为是肉体,以为是现实,以为是 “我们”。
最后的喊声,最后一首诗,最后抵达死亡,只有这 “最后”才在挣扎中看见了从 “我们”中挣脱出来的那个 “我”:我是诗人,我爬上 “天梯”,我叫马林·索雷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