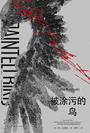 |
编号:C55·2190421·1565 |
| 作者:【美】耶日·科辛斯基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6.00元当当26.00元 | |
| ISBN:9787208155657 | |
| 页数:336页 |
“他用记忆的艺术再现了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2014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文学奖委员会这样描述他的作品。《星形广场》出版于1968年,是莫迪亚诺的处女作,获当年的罗热-尼米埃奖和费内翁奖。小说通过叙述者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的谵妄幻觉展开,这位主人公变换千百种怪诞离奇而又互相矛盾的犹太身份,却将痛苦的悲剧隐藏于诙谐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诸多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鱼贯而行:莫里斯·萨克斯与奥托·阿贝茨,列维-旺多姆与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医生,马塞尔·普鲁斯特与法国盖世太保,德雷福斯上尉,弗洛伊德,希特勒及其情人爱娃……有如旋转木马一般在时空中疯狂地转动,而当我们合上书,星形广场就镌刻在“痛苦之都”的中心位置。
《被涂污的鸟》:这些声音因有意义而沉重
我大声地不停地说话,先是像农民们那样,然后又像城里人,尽我的最大能耐越说越快,因那些声音而欣喜若狂——这些声音因有意义而沉重,像带水的雪因有水而沉重一样——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证实我的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
——《20》
大声地说话,越来越快地说话,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能说话,即是说给自己听,说话也变成了存在的唯一证明,从医院到教会,从乡村到城市,从没有父母的生活到被父母领走,所有经历的重要性都比不上“说话”——说话是言语的开始,当它作为一种开端被标注的时候,就意味着人的诞生,那一刻,说话者不再是一个经历了苦痛、见证了暴行的孩子,而是如上帝一样命名了一个人。
最后一章,是结局,但是当说话开始,终点便是新的起点,它确认了人的诞生,在一个孩子身上言说。但是,当声音像带水的雪一样因沉重而富有意义,当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我是被一种巨大的欲望裹挟着,甚至说,一个会说话的孩子是沉浸在自我言语的封闭世界里,一个人的言语,一个人的狂欢,一个人的起点,是不是最后反而变成了一种囚禁?耶日·科辛斯基一定是反对囚禁的,因为囚禁的反面是求生,“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遏止的。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想象和孩子一样冲破藩篱冲破束缚,到达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世界,在这篇《序》里,科辛斯基表达了自己的渴望,但是正如这篇原文的标题一样,1976年增加的此文就叫《后来》,在1965年缺失了序言之后,他终于用文本开始说话,像小说里最后的自己,“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
“后来”开始说话,是因为必须证实自己又能说话,此前因为沉默,因为确实,是因为读者误读了文本,甚而误读甚至故意歪曲了厉害,无论是听到那些“资源流亡者”认为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记者添油加醋的结果,还是在小说出版之后西方文坛的评论“含有不安的底色”,无论是自己祖国的那些人对小说的肆意攻击,还是自己陷入到一种言语的围攻和行动的限制中,科辛斯基都无法沉默,“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但是当他从社会科学转向小说,当他用想象创造出一个真实的时代,他是想让自己不成为那一只“被涂污的鸟”,“尽管离群索居和默默无闻是我儿时的日常状态,但我却感到某种力量驱使我,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
农民们逮住一只鸟,把它的颜色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当这一只鸟返回鸟群,换来的不是同类的羡慕和尊重,而是攻击和撕扯,最后鸟群将它活活杀死。这是赤裸裸的暴力,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些取乐的农民,但是当被涂污的鸟成为一种异类,他的命运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孤立的死亡。科辛斯基的小说中的“我”当然不是自己选择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它是暴力的牺牲品,科辛斯基用小说谴责暴力,当然需要每个人都能进入小说的世界,只有这种进入的状态,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暴力,这种残酷,这种反人类的行为,开放而让人进入,却又面临着了这样的无奈:“这本小说有如那只鸟,非得把它从鸟群中驱逐不可;他们逮住了那只鸟,给它的羽毛涂了颜料,然后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
用小说写出了“被涂污的鸟”,却使小说也变成了“被涂污的鸟”,这是不是变成了囚禁自己的一个牢笼?科辛斯基希望让每个人都进入小说世界,却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说话,而且本不想让声音从自我世界里逃逸;科辛斯基不想像父亲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却用自己的想象囚禁了写作的自由,毋宁说,科辛斯基在用一种强烈证明自己写作合理性的方式来开放想象,而开放想象却让自己成为被涂污的鸟——不是在历史暴行层面失去了公正,而是一种写作手法上,因为带了太多情感的因素,反而使得小说成为了一种被过分想象劫持的虚构之物。
“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想象不可囚禁,孩子不可囚禁,是针对那些被歪曲的历史、那些误解的读者而言,但是当返回内部,自己用文本囚禁孩子囚禁想象,如何能变成一只不被涂污的鸟?在第七章之前,那个希望让所有人进入的小说世界,与其说和历史有关,不如说和神话有关。一个找不到父母的孩子,当然失去了所有被现实定义和支撑的元素,只是一个“我”:没有父母,没有名字,没有出生,他是被抛到这个世界的人,是一个非人类生存的传说,而不管是他遇到的人,听到的话,经历的事,也都在一种神话学的想象中展开:住在小屋里等待父母来找自己,我第一个认识的人是玛尔塔,她把自己的乱发叫做“妖法”,认为里面居住着邪恶的精怪,她把蛇蜕皮看成是一种“变形”,并告诉我说:“人类的灵魂也以相似的方式抛弃肉体,然后飞到上帝的脚边。”一种原始意义的上帝出现在我的认知里:“在人的灵魂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上帝用温暖的双手把它捧起,吹一口气使它复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天使,或者把它打入地狱,到火中受永恒的磨难。”
村子里的奥尔加给我讲的也是上帝和魔鬼,当她把我成为“黑人”的时候,认为有一个邪魔依附在我身上,所以让我吞下她配制的涂有大蒜汁的木炭,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让我除了头之外的整个身体都埋在泥土里;磨坊主因为怀疑老婆卖弄风情并和一个年轻农夫调情,于是把他们看成是魔鬼,他脱掉老婆的衣服毒打,还用餐匙将农夫的眼睛剜了下来,就像妇女们刮土豆的那个腐坏的霉点一样,“那只眼珠像从被打破的蛋壳中冒出的蛋黄一样,从他眼眶一鼓而出,顺着磨坊主的手落到了地板上。”“傻娘儿卢德米拉”因为年轻时拒绝嫁给丑陋而残忍的男人,于是未婚夫将她视作魔鬼,引诱到野外让一大群醉醺醺的庄稼汉轮奸了她,在他们看来,卢德米拉被死了魔法,尤其是在大腿间被注入了邪火,于是,“在其他人喧闹沙哑的笑声和鼓励声中,她在卢德米拉的双腿中间跪下,把那整个瓶子硬塞进丁卢德米拉腿间那饱受凌辱和强暴的裂缝之中。”最后“傻娘儿卢德米拉”被活活折磨而死;木匠的妻子吧招来闪电的黑头发看成是“魔鬼的跳蚤”,他也曾经把一只只生病的猫放进袋子里,然后投向“鼠海”之中,而最后木匠却死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木匠的身体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他的脸和一半的手臂已没入鼠海之中。一群一群的老鼠正爬在他的肚子和两腿之上。他完全被老鼠湮灭了,鼠海翻腾得更猛烈了。”最后鼠海表面只剩下一具完完全全的骷髅。
头发是妖法,招来闪电是“魔鬼的跳蚤”,偷情、性欲也都是魔鬼的一部分,只有去除了附在身上的那些魔鬼,才能让上帝接纳,在我所经过的村子里,那些磨坊主、木匠、农民构成了一个愚昧的体系,他们建立了魔鬼和上帝对立的系统,这是一种善与恶的对立,但是在上帝没有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带着魔鬼的气息,甚至在他们的现实里,上帝似乎从来没有露面,而这也残酷地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恶魔统治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神话所构筑的巫术世界里,尽管我在其中逐渐获得了知识,逐渐看见了希望,逐渐拥有了人的意识:在玛尔塔那里,我知道了人不应该向疾病和痛苦屈服,千方百计和它们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奥尔加那里,我知道了必须了解动物和植物,才能熟悉毒物和药草;知道了火的涌出,当有一个自己的“彗星”就可以化解很多困难;在磨坊主的暴力中,我想象了没有眼睛的生活,它一样可以通往自由,“说不定失去了眼睛之后,那小伙子会看见一个全新的更迷人的世界哩,谁知道呢!”而在莱克的鸟世界里,知道了各种鸟生活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知道了“被涂污的鸟”的命运:起先是鹳鸟家族的样本,因为莱克被鹳鸟欺负,于是他把一枚鹅蛋放进去,从而引起了鹳鸟家族的矛盾,甚至变成了屠杀——母鹳鸟被怀疑通奸,于是鹳鸟家族用喙子和翅膀的猛攻不忠的母鹳鸟,直到最后被折磨而死;那一只被涂污的鸟,拥有了彩色的羽毛,但是回归鸟群之后变成了异类,于是在众鸟的攻击中,菜鸟孤独地死去。
知识、希望和人的意识,是对于恶魔现实和巫术世界的一种告别,也正是因为在那里有着太多的暴力和死亡,才使得我不断逃离——逃离神话世界构成了前七章的一个主题,而当那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德国老兵”出现之后,似乎科辛斯基才开始在现实中说话,和人有关的因素不断增多,和时代相关的场景不断出现:那是一个德国分遣队经常到来的村子,这是纳粹针对村民实施暴力的世界,这也是我第一次被怀疑是“吉普赛人”的阶段。所以流浪成为了我经历的主题,在流浪中,我也不断进入到人类世界:在冬天,我在森林中歇宿,用“彗星”的光照亮和温暖我自己;我在农民面前背诵诗歌,还用所谓的导火索和“肥皂”砸毁了那一个牲口棚;我在德国士兵经常光顾的村子里,发现在路堤边、铁轨间,有无数的碎纸片、笔记本、日历、全家合影照、印制的身份证、旧护照和日记……
 |
|
耶日·科辛斯基:我用想象自我囚禁 |
当那个德国老兵在森林里将我放走,似乎我还见到了人性,尽管那个名叫“彩虹”的犹太女孩被德国士兵活活弄死,但是在这个远离了曾经的巫术世界里,一张可能的秩序正在产生。人性之外,还有上帝,神父把我带到了村里,收留我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加波斯不断毒打我,虽然我被骂成是“吉普赛吸血鬼”,尽管被扔进了满是污秽物的粪坑,但是神父眼中的上帝毕竟不在是巫术世界里的存在,我了解了圣器的含义,直到了清晨弥撒和晚祷的意义,甚至想要用背诵祷辞的方式挣来最多的免罪日,十岁的我告别了原始意义的懵懂,“我过去太蠢了,不理解主宰人、动物和事件的世界的原则。现在人间有了秩序,也有了正义。”而在宗教之外,我的欲望世界也被打开了,马卡尔的农夫有一个叫尤卡的女儿,她用她的肉体让我变成了一个男人:“我经常紧贴她的小腿,开始从两个脚踝慢慢地吻,先只是用双唇触碰它们,用手轻抚那绷紧的肌肉,然后亲吻她膝盖后的凹窝,接着是她光滑白滑的大腿。渐渐地我撩起了她的裙子。”
人性、宗教和欲望,都让我不断接近人类的存在,当从神话世界脱离出来,我作为一个人的特征似乎也越来越明显。而在人类存在之后,我进入的则是一个政治世界:我的身上有了身份:可怜的吉普赛佬或者犹太弃儿,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接纳,听说了红军击败了卡尔梅克匪徒,知道了德国纳粹被击败了,而从医院出来之后,加夫里拉和米特卡照看我,加夫里拉是政治官员,他让我读书,米特卡是个狙击手,他则引导我学习诗歌为我唱歌。但是这个政治世界依然有许多陌生,甚至有许多潜在的规则,比如加夫里拉说:“按照人类历史的法则之一,时不时地会有一个人从无名的广大民众之中升起;这么一个人希望其他的人也过得幸福安乐。”而这个男人就叫作斯大林。而在孤儿院里,那些士兵还砸烂了院长的办公室,还追着护理员,“扇她们耳光,拧她们的屁股。”
神话世界、人类现实和政治生活,构成了我人生经历的三个阶段,在里面有不同的暴力,有各异的死亡,无论诡异也好,残忍也罢,也无论我的存在是幸运也好,是传说的一部分也罢,总之,我活着,没有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但是在所有过程里,我是见证者,但是却是沉默的,也从来没有过主动,即使逃跑,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受尽屈辱,即使在孤儿院里我的父母终于来到我身边,让我不再是一个孤儿,但是我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成为某个人的真正的儿子——被抚爱、被照顾,不得不顺从别人,不是由于他们更强壮并且能伤害我,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并且具有别人没法剥夺的权利。”所以沉默而不说话成为我“非人类”的一个标志,而终于那个照看我的滑雪教练让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证明其为人的唯一理由,是对于世界的唯一态度,是活着的唯一理由。
没有被囚禁的孩子,是可以自由说话的孩子,没有死去的孩子,是可以越说越快的孩子,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是向自己证实又能说话了的孩子——当说话成为人活着、获得尊严、不是被涂污的鸟的一种证明,这个隐喻的世界是狭窄的,是脆弱的,甚至是封闭的,而科辛斯基所谓“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因为,一个人仅仅说话,以为像上帝一样言说,其实依然是一只被涂污的鸟,“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