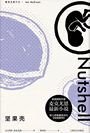 |
编号:C38·2190617·1578 |
|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46.00元当当20.30元 | |
| ISBN:9787532778805 | |
| 页数:223页 |
第一句:“哦,天哪,要不是我噩梦连连,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中,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坚果壳》是伊恩·麦克尤恩的最新作品,小说以一个未出生婴儿的视角重述了一个现代版《哈姆雷特》的故事:特鲁迪背叛了丈夫约翰,与丈夫的弟弟克劳德勾搭成奸,与此同时,身怀六甲的特鲁迪还居住在约翰的祖宅中,却将丈夫拒之门外,特鲁迪与克劳德密谋杀害约翰,从而霸占这栋豪宅,但一切都被特鲁迪腹中九个月大的婴儿所洞悉……无限宇宙是否被打开,也许并不取决于那个果壳是不是存在,重要的在于和世界如何构筑一种关系,如何用有限窥探无限:“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孽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坚果壳》:我也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子宫
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第一章》
没有经历,没有体验,没有是非,即使有那么一点点意识,对于出生还要两周的胎儿来说,外面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空无的存在,但是当子宫里住着一个“我”,起先天真无邪的生命如何变成了阴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一个隔离外部世界的子宫如何变成了一个现场?
伊恩·麦克尤恩似乎并不是展示一个生命的降生过程,并不是在探讨意识的形成过程,当他已经把生命命名为“我”,一种隐喻的世界慢慢在构建慢慢在扩展。胎儿的世界本来是未知的,是一种空想的存在,即使有过生命萌芽时的某些感觉,但也和真正的想法相去甚远。但是一个“我”,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虽然依附在母亲的身体里,生长在母亲的子宫里,但是在“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已经将未知世界和已知世界联系起来,甚至那种联系已不再是“幻象”,它赤裸裸、活生生地发生着。
“于是我在这儿,倒挂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当我的耳朵贴在血淋淋的墙上,当倾听而在脑海里做着记录,我不是一个隔绝在事件之外的存在,“此刻我听到意图不轨的枕边细语,对前方等待我的一切,以及我可能卷入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我参与了一场阴谋:母亲特鲁迪有了情人克劳德,他们正在约会,为了能让这种隐秘的约会变得合理化,他们必须要除掉我的父亲约翰,于是那个夜晚的阴谋便成为我参与的事件之一,“下毒”是我从母亲那里听到最清晰的一个词,接下去有关的词还包括:“我想要他死。明天就得死。”
密谋之后是实施,起先是克劳德向父亲约翰借了钱,之后在那个还未实施的夜晚,却听到了父亲的态度:他不仅得知了母亲出轨于克劳德,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女人艾洛蒂,当母亲的奸情被暴露之后,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介绍艾洛蒂是他的情人,于是两个将婚姻带向终结的故事同时发生,而那场密谋似乎反倒没有了太多的意义。但是下毒还是实施了,因为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作为,“明天就得死”成为她报复父亲的一种手段。当第二天告别的父亲喝了掺有乙二醇的奶昔,在开车离开之后倒在了车上,“一个男人被发现伏在汽车方向盘上,已经死去。”当这样一个计划变成了实施,听到这个消息的特鲁迪反而说出了“我害怕”,并且把一切的罪责怪在克劳德身上,坚称自己是无辜的,那句“我恨你”和对父亲说的那句“我不爱你”都成为母亲逃避害怕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起初鉴定是“自杀”的案件里,艾洛蒂却认为:“不过,一点……一点也不像是他的作风。”于是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当母亲第二天要去警察局的时候,“我的羊水。破了!”于是,“嘎吱一声,我急匆匆地滑了出来,赤条条地来到了这个王国。”要两周才能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却因为羊水破了提前出世,暂且不管“我”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在我未出生之前,在见证而且“参与”了阴谋的情况下,我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或者说,当我在空想中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伊恩·麦克尤恩在题辞中引用的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台词:“哦,天哪,要不是我噩梦连连,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
这个被引用的题辞,至少包含着麦克尤恩的两种意图,一种是“噩梦连连”,它指向的是和密谋有关的现实,另一种则是关在坚果壳这个庇护所里,自己便成为了“无限宇宙之王”。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存在感,其实构成了一种矛盾,或者对于生命来说,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下活着。在“我”作为胎儿的经历中,噩梦当然是自己作为本来天真无邪的生命,却参与了一场阴谋。这场阴谋体现着参与的直接性:当母亲和克劳德约会时,我见证了他们两人的烛光晚餐,我感受到了爱欲里那一出“克劳德的夜间性交前戏”,当然我也听到了那个阴险的词:下毒,“最后,她说出了她的决定,她轻声下了指令,她口中蹦出了那个单个的阴险的词,这一切似乎都是从我这张未开口过的嘴里发出来的。他们再一次接吻,她对着情人的嘴说了出来。我这个婴儿的第一个词。”
但是,这种直接性却又在无法参与的情况下让我变成了局外人,父亲将被毒死,无论如何我想要终止这次密谋,但是一方面对我的打击是:母亲所做出的这个决定,一定是不爱我了,我曾以为她在户外是为了让我获得骨骼发育所需要的维生素D,她把收音机音量调小是为了更好感受我的存在,她用手抚摸我的脑袋位置是一种关爱,但是当母亲钟情于克劳德——父亲约翰的弟弟,背叛了父亲,也意味着会毁了自己的孩子,“我不确定她爱我。”不爱我却又带着我进行密谋,我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变成密谋者,“无情的母亲!这将是一种毁灭,我的沉沦,因为只有在童话里没人要的小孩才会成为孤儿被养大。”所以我要把这种爱带给父亲,“亲爱的父亲,把我从这个绝望的河谷里拯救出来吧。带我走吧。让我在你身边一起被人下毒吧,好过被安置在某个地方。”
我渴望成为有力量的人,成为年轻、黑豹一样的自己,然后告诉父亲是谁要杀他,然后“拯救”父亲。但是当听到“下毒”,听到“明天就得死”的时候,父亲却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叫艾洛蒂的女人是父亲可以离开母亲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说,我也被父亲抛弃了,“我算什么?我已经死了。我被送进了坟堆,那是在他恨之入骨的前妻的肚子里。”我既无法警告也无法付诸行动,这一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就是噩梦连连的生活。我想象自己写给父亲一封信,信里我说“我害怕被遗弃”,并且希望父亲能逃过这次谋杀,“不要下楼梯。大声地、无忧无虑地说再见,坐上您的车就走。或者,如您非得下楼,那就千万别喝果汁,在楼下告别完就走。以后我会解释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会是您听话的儿子……”
但奶昔里还是放进了毒药,父亲还是喝了下去,开车出门的他还是死在了路上,这一切的噩梦还在继续上演,“命运对我的安排是成为一个夭折的死胎,然后归于尘土。”但这并不是终结,当父亲死去,当克劳德依然进入母亲的身体,我的感觉是丑陋,“我的不忠的母亲几乎没有将我与这个即将要成为杀死我父亲的凶手分开。”但是当母亲将这个计划怪罪于克劳德并且开始“害怕”,我却想要报复——报复杀人者克劳德,我的行动便是“自杀”,只有这样,因为叔叔肆意侵犯一位晚期妊娠的孕妇,致胎儿死亡,无异于杀人,所以克劳德就会被捕,受审,获刑,坐牢,这样,我父亲的仇就报了一半。”而这种复仇也成为生命的本能,“复仇:这是一股本能的冲动,十分强烈——可以原谅。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后,没有人能够抗拒为报仇出谋划策的诱惑。”但是当克劳德还在浴室里高声唱歌,我的复仇其实也失败了。
噩梦连连的现实,我是见证者,参与者,甚至也是实施者,但是不管是母亲的背叛,还是父亲的出轨,甚而至于克劳德的参与,艾洛蒂的出场,其实都体现了一种错乱,也是人与人隔阂现实的一种注解,所以对于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理想,不仅是坚果壳里的存在,也是现实的一种折射。父亲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诗人,经营着穷困潦倒的出版社,虽然独具慧眼刊印了女诗人的诗集,但是当她们声名鹊起之后,却抛弃了父亲,而在母亲面前,“一个宽宏大度的壮实男人正用一首毫不时髦的十四行诗向她苦苦恳求,哪怕毫无希望。”而母亲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空间”,也许是借口,但一定是婚姻没有给她带来浪漫和快乐,克劳德这个阴谋家的介入,让两个人的婚姻走向了末路。但是在面对隔阂的现实时,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不管口中所说的十四行诗和空间,其实都想让自己成为无限宇宙之王,可以在被动中变得主动,所以母亲要毒死父亲,所以父亲带着“猫头鹰诗人”艾洛蒂宣布自己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他们都希望自己不是受害者,所以父亲在那次走之前说,““谢谢你提醒我。爱情是否天长地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存在着。所以,敬爱情,敬我们的爱情,敬爱情原本的模样,也敬艾洛蒂。”
活在噩梦连连的现实里,却希望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只有在隔阂的世界里,他们才会这样为自己命名,所以在这一事件中,每个人都像活在坚果壳里,都在坚果壳的现实里矛盾着,被禁锢,成为他们无法逃离的生活状态,“被禁锢在一个坚果壳里,只能从两寸象牙、一粒微沙中窥探整个世界。”所以和母亲肚子里的我一样,被禁锢而无法左右现实,被禁锢而虚构了自己的生活,被禁锢而为活着寻找借口,所以“子宫”不仅仅属于无能为力的自己,也是所有人的“隐秘之地”,“将来等我上了学,我也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子宫一样的环境,把英国佬、苏格兰佬和法国佬的启蒙精神都在一边。什么真实,什么干巴巴的事实,什么讨人嫌、装腔作势的客观性统统滚开。情感才是王后。除非她自称为王。”而这也是人类自我的空想,是用“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已知世界的爱欲与阴谋,已知世界的逃避和虚构,已知世界的仇恨和间离,已知世界的谎言和死亡,只有在子宫那个“隐秘之地”,每个人都拒绝现实的噩梦,成为自己的宇宙之王。但是必然发生的事是:孩子总会出身,坚果壳总会破除,现实总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到来。羊水破了,胎膜被抖去,赤条条来到世界,我成为了一个真正参与世界的生命,而一出生,“我柔弱的胸腔被一名杀人者的双手谨慎地牢牢抓住,我被放在另一位凶手的如雪一般柔软、惬意的肚子上。”面前是凶手,面前也是母亲,当出生遭遇母亲的这种双重身份,坚果壳里的存在又投射于外,世界是更大的坚果壳,“我想我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整个世界。”母亲是美丽的,是慈爱的,是残忍的,世界也是美丽的,也是慈爱的,也是残忍的,但是当坚果壳被打破,当再无可能退身回去,一种命运被降临,是更大坚果壳的存在,“我也在想我们的牢房——希望不要太小——在那道沉重大门的另一边,磨损的台阶逐渐上升:起初是懊悔,继而是公正,随后是意味深长。其余则是一片混沌。”
母亲背负的杀人罪名,使得我的生命一开始就在监狱里度过,在那里,母亲的懊悔,法律的公正,以及意味深长的生活,会成为我最初的生命记忆,但是在这个之外,“其余则是一片混沌。”——甚至没有在子宫这个隐秘之地的逃避可能,十四行诗在哪?自由的空间在哪?最纯粹的爱和恨在哪?空想中的幻象,其实是最无奈的宿命:“在母亲体内,我憧憬着我应得的权利——安全,不受搅扰的平静,没有压力,无罪无愧。我在思索,到底什么本该属于幽禁中的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