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X24·2200615·1658 |
| 作者:[清]孔尚任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5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19.00元当当9.40元 | |
| ISBN:9787020051823 | |
| 页数:278页 |
《桃花扇》是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完稿,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刊成初版。《桃花扇》全剧四十四出,除试一出《先声》、闰二十出《闲话》、加二十一出《孤吟》、续四十出《余韵》之外,全剧结构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出《听稗》到第十二出《辞院》主要写侯、李的结合及由合而离,同时联系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左良玉欲东下就粮,为马、阮迫害侯方域埋下伏线。《桃花扇》所写的是明代末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全剧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揭露了弘光政权衰亡的原因,歌颂了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层百姓,展现了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桃花扇》是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重大事件均属真实,只在一些细节上作了艺术加工。以男女情事来写国家兴亡,是此剧的一大特色。该剧作问世三百余年来长盛不衰,已经被改编成黄梅戏、京剧、话剧多个剧种,频频上演。
《桃花扇》:儿女浓情何处消
(外怒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第四十齣·入道》
从癸未三月李香君的“却奁”,到癸未十月侯方域的“辞院”,再到乙酉七月的“入道”,两个以桃花扇作为信物订盟的相爱之人终于在“不觉别来便是三载”的长久分离中相聚,这三年,他们经历了“杳杳万山隔鸾凤”的相思之苦,这一刻,他们说出了“天老地荒,此情无尽穷”的喜悦,面对那桃花扇,李香君惊见而吟:“书难捎,梦空劳,情无了,出来路儿越迢遥。”而侯方域则看着扇上沾血的桃花,发出了“看鲜血满扇开红桃,正说法天花落”的感慨——“你是侯郎,想杀奴也”的惊喜成为两个人共同的心声。
但是这一出爱情并不是以最后的团聚相守为最终的归宿,在白云庵里,已经挂冠归山的张瑶星面对着痴男怨女却嘲笑他们:“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当侯方域辩解说:“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一个修仙有分涉世无缘的道士为何要管这些男情女爱?面对侯方域的质疑,张瑶星怒斥道他们是“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于是在叹息儿女之情,甚至将其定义为“艳语淫词”之后,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明道:“怎知道姻缘簿久已勾销;翅楞楞鸳鸯梦醒好开交,碎纷纷团圆宝镜不坚牢。羞答答当场弄丑惹的旁人笑,明荡荡大路劝你早奔逃。”而在张瑶星指道之后,不管是侯方域还是李香君,都遵从了,“弟子晓得了”便是他们“早奔逃”的开始,在“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的悔悟中,侯方域前往南山之南修真而去,李香君则在“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感慨中前往北山之北学道而去。
南方之南进入“男境”,北方之北进入“女境”,南北和男女,在通向截然相反的修真学道之路上,两个人的花月情根不再,而已从此没有“天荒地老”的永恒,于是,这一幕“桃花扇”在“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中落幕:当“桃花扇底送南朝”作为一个符号,当“儿女浓情何处消”找到彼此的归宿,这一幕爱情或者正如这世事一般,只不过是一场梦。但是,当“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成为孔尚任的一个观点,以“入道”的方式完成一种救赎,是喜还是悲?无疑,侯方域和李香君作为弟子遵从了张瑶星的指点,是毫无怨言的,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乱世中的预设,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当国和家、君和父都在兴亡梦中不见,何来男女之情?或者说,一个朝代都已覆灭了,爱情怎可能是“无穷尽”?
男女钟情之上是国,是家,是君,是父,而且在张瑶星为侯方域和李香君指点入道的出路之前,早已经为各人安排了归宿,“世态纷纭,半生尘里朱颜老;拂衣不早,看罢傀儡闹。恸哭穷途,又发哄堂笑。”史可法、左良玉和黄得功作为死难之臣,一个被册封为太清宫紫虚真人,一个被封为飞天使者,一个则被封为游天使者,都在张瑶星“奉上帝之命”中走马上任去了;而被雷击死于台州山的马世英,跌死在仙霞岭的阮大铖也都在恶有恶报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种是功臣被封而走马上任的“荣耀”,一种是“福有因,祸怎逃,只争些来迟到早”的罪恶,在这最后的因果轮回中走向终结。无疑,最后的安排也是在延续着兴亡梦,生前是忠臣死后享荣耀,生前是佞臣死后则皮开脑裂,这最后的兴亡梦与其说是熄灭了,不如说得到了延续,而在这和政治有关人物的命运有了最后归宿之后,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在南山之南和北山之北的修真学道中分道扬镳,也便成为一种合理的安排。
实际上,这无疑是爱情被宗教化的写照,而在宗教化之前,则是爱情的政治化,或者说,孔尚任本就没有想要书写一幕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血溅桃花扇无疑是这个政治化故事的最悲苦的色彩,他的一切出发点和归结点似乎都在寻找“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在“桃花扇”小引中就直接表明了自己创作的意图,“《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明朝之兴亡,不是远古之事,是近世之事,用存者之父老演绎南朝新事,就是要回答三百年的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如此,并非子虚乌有的儿女钟情就像“全无假借”的朝政得失一样,是真实的,也更具有醒世的意义。
这醒世意义便是桃花扇的传奇所在,在“桃花扇小识”中,孔尚任解说了写这出传奇的意义,“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传奇之奇在何处?奇在桃花扇,但是桃花扇只不过是妓女之扇,只不过是荡子之题,只不过是游客之画,只不过是“为悦己容,甘剺面以誓志”,只不过是“伊其相谑,借血点而染花”,只不过是“私物表情,密缄寄信”,这些都是鄙事、细事、轻事、猥亵之事,皆不足道也;传奇之奇到底在何处?穷奇在桃花扇,桃花扇之桃花是美人之血痕,美人之血痕是“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而致,而权奸者是“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则是“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所以,“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如此一个循环,无疑就是将桃花扇预设为一个符号,“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所以这一出用以醒世的桃花扇传奇带有更为宏观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且书写这一出传奇也不在这个已经破灭的兴亡梦中,而是要有一种对后世的警示意义,“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身为种桃道士,孔尚任希望这一传奇可以长远流长,在“桃花扇小引”中他也表达了这样的诉求,“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当传奇之奇只为找出“隳三百年之帝基者”,当种桃道士只是在“历千百春,艳红相映”中吸取南朝兴亡的历史教训,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真的成了点缀,而纵观桃花扇,从“试一齣”的先声到“续四十齣”的余韵,都贯穿着这一主题。“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桃花扇无疑是点睛之笔,这个有着美人血痕的象征之物,如何变成一种政治之物?或者说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是如何被一步步政治化的?
桃花扇在整部传奇中出现过五次,第一次是在媚香楼“眠香”时,秦淮佳丽李香君年及破瓜,梳栊无人,杨文骢推介“家道才名,皆称第一”的侯方域,于是在闲花添艳野草生香的媚香楼,侯方域拿出一把宫扇,题赠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上面题写的诗句是:“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这是桃花扇作为定情之物而出现,实际上也是他们爱情的开端。桃花扇第二次出现也是在媚香楼,只是当时的场景完全变了,侯方域因为暂避史可法府中而使两人分离,守望着侯方域的李香君却要变成田仰之妾,在“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的抗拒中,李香君坚决不下楼,最后以倒地撞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坚贞,于是桃花扇被血点污坏,杨文骢便在“几点血痕,红艳非常”的桃花扇中“添些枝叶”而成一画,“补衬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而这也成为李香君“桃花薄命”的写照。
第三次再现桃花扇已是乙酉二月,此时距离他们分别已经快两年了,而两个人的命运也各异,侯方域是在“逢舟”知道李香君为了替他守节不肯下楼,最终血溅桃花扇,当侯方域打开桃花看见扇上画着的溅血桃花而生感慨,后来又亲自去媚香楼,只是人去楼空,李香君已经被迫入宫,此时侯方域看见了桃花盛开,想起两年前的定情之日也是桃花盛开,于是掩泪而泣,“今日小生重来,又值桃花盛开,对景触情,怎能忍住一双眼泪。”而溅血的桃花扇也成为这一段悲苦感情的写照,“溅血点作桃花扇,比着枝头分外鲜。携上妆楼展,对遗迹宛然,为桃花结下了死生冤。”等到第四次桃花扇现身,则是乙酉六月,在栖霞山上,侯方域遇见了柳敬亭,当柳敬亭问侯方域三年来可有李香君的消息,侯方域取出当初订盟之物的桃花扇,最后发出了“把他桃花扇拥,又想起青楼旧梦;天老地荒,此情无尽穷。分飞猛,杳杳万山隔鸾凤,美满良缘半月同”的感叹。等到第五次桃花扇出现,则已经是“入道”之前了,当两个人最后相见,侯方域再次拿出桃花扇,“看这扇上桃花,叫小生如何报你。看鲜血满扇开红桃,正说法天花落。”最终桃花花落似乎也是这一出历经跌宕的爱情的归宿,从此南山之南和北山之北成为各自的方向,而这一个溅血桃花的故事也在“啧啧在口,历历在目”中成为一种传奇。
从第一次的订盟到最后一次的入道,两个人在其中的三年时间里都没有重聚,这也就意味着桃花扇这个象征他们坚贞爱情的信物,缺失了主人,在缺失了完整性的传奇中,留下的也只有各自的无奈和悲叹。主人的缺席,是爱情完整性的缺失,而这无非是一个“青楼旧梦”,实际上,李香君和侯方域之间的关系很难界定为真正的爱情,它甚至只是种桃道士虚设的一种点缀。李香君已经到了破瓜之年,杨文骢想要为他物色一人,而此时的侯方域刚到南京这个六朝佳丽之场,在春情难按中需要寻找销魂美人。于是在“访翠”中,侯方域听得媚香楼传来琵琶声,“玉玎珰,一声声乱我柔肠。”又传来吹箫声,“这几声箫,吹的我消魂,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两个人见面之后,便是相互敬酒,接着便是才子佳人的交心酒,接着便是择日迎亲,接着便是题扇赠美人,于是两人喜结连理开始了春宵一刻,“这云情接着雨况,刚搔了心窝奇痒,谁搅起睡鸳鸯。被翻红浪,喜匆匆满怀欢畅。枕上余香,帕上余香,消魂滋味,才从梦里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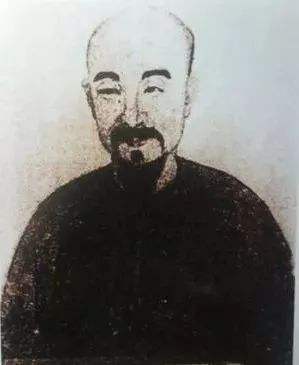 |
|
孔尚任: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才子佳人的传奇没有那种海誓山盟的感觉,当一切被安排,爱情似乎只是一种必然发生的过程,而这个从桃花扇开始的男情女爱便在“杳杳万山隔鸾凤”中走向了分离,也在家破人亡中变成了传奇,一切也都是为了实现孔尚任所说“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的主题。爱情的政治化是明显的,两个人为何会分开,一切的起因似乎是“却奁”,李香君到了破瓜的年纪,杨文骢为她梳栊,而二百余金的梳栊之资就是阮大铖所出,杨文骢告知他们实情,但是似乎在为阮大铖说话,“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侯方域听信了这一解释,认为阮大铖只要悔过亦可接受,便接受了妆奁酒席的费用。但是李香君却表现出更决然的态度:“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她一边指责侯方域,一边拔簪脱衣以示抗议,“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李香君“名自香”便是一种自洁,在李香君的决然面前,侯方域对李香君更加怜爱:“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正是李香君的决然态度,让侯方域从最初的被美人销魂的肉体感受升华到“更觉可爱”情感体验,这似乎也是第一次在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爱的感觉,但是他们之间情感的第一次完美呈现也是最后一次,一方面对于李香君来说,从桃花扇订盟而结婚,到却奁表达态度,她其实已经有了守志的意念,这种意念并不只是对侯方域的忠诚,更是对自身爱国主义的忠诚:之后是“拒媒”,当侯方域躲避史可法家,李香君面对田仰用三百金娶妾的打算,李香君表达了“奴便终身守寡,有何难哉,只不嫁人”的决心;之后是“守楼”,“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李香君就死不下楼并以倒地撞头的方式抗拒,“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梯。”之后是“寄扇”,“想起侯郎匆匆避祸,不知流落何所;怎知奴家独住空楼,替他守节也。”一边是对自己“烟花薄命飘摇”命运的感慨,一边则是“保住这无暇白玉身”的自洁,桃花薄命,扇底飘零,李香君看似为与侯方域的爱情守节,题词的桃花扇便是明证,实际上是为风雨飘摇的国家守节。
而另一方面对于侯方域来说,也一样从李香君逐渐政治化的行动出发,萌发了爱国主义情怀。其实从一开场侯方域就被置于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侯方域的家族是“夷门谱牒,梁苑冠裳”,他在文章上的成就是“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来到南京,看到碧草念粘天,看到黄尘匝地,便陡生了“谁是还乡之伴”的疑问,发出了“独为避乱之人”的感慨,“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之后遇到了复社的陈定生和吴次尾,还听说了阮大铖“蓄养声伎,结纳朝绅”可耻行为,并得知吴次尾写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但是不管是亲眼所见“烽烟未靖,家信难通”的惨相,还是听说权奸的罪证,他都是旁观者。但是自从认识李香君并从爱情中感受到家仇国恨,侯方域也开始了自己政治化的人生之路。因私信左良玉,阮大铖告发了他,侯方域为避祸暂居史可法家,“尚无定局,好生愁闷”的他听说崇祯煤山自缢福王又要自立,侯方域向史可法提出了否定的观点,他认为福王有三大罪,一罪是:“福邸藩王,神宗骄子,母妃郑氏淫邪。当日谋害太子,欲行自立,若无调护良臣,几将神器夺窃。”二罪是:“骄奢,盈装满载分封去,把内府金钱偷竭。昨日寇逼河南,竟不舍一文助饷;以致国破身亡,满宫财宝,徒饱贼囊。”三罪则是:“就是现今世子德昌王,父死贼手,暴尸未葬,竟忍心远避。还乘离乱之时,纳民妻女。”如此三罪,“这君德全亏尽丧,怎图皇业。”接着他又提出了“无不可立”:“第一件,车驾存亡,传闻不一,天无二日同协。第二件,圣上果殉社稷,尚有太子监国,为何明弃储君,翻寻枝叶旁牒。第三件,这中兴之主,原不必拘定伦次的。分别,中兴定霸如光武,要访取出群英杰。第四件,怕强藩乘机保立。第五件,又恐小人呵,将拥戴功挟。”
对福王的三大罪和“无不可立”,其实就是侯方域的一篇檄文,直接指向崇祯之后的皇宫乱象,这是侯方域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在这之后,他更是奉了史可法之名监军防河,知道高杰性气乖张恐挑起事端,便来劝谏,不想高杰不听谏言,被许定国遣人刺死,侯方域只得买舟黄河顺流东下,看见大路之上纷纷乱跑的都是败兵,这一次和处来南京时一样,都是国败之惨状,但是和最初作为旁观者不同,经历了太多、目睹了太多的侯方域已经成为了一个亲历者;之后和复社人员在一起被阮大铖投入监狱,身在囹圄,侯方域却将此当成是自我磨练的场所,“闲消自遣,莫说文章贱。从来豪杰,都向此中磨炼。”在遇见柳敬亭得知李香君的经历之后,侯方域拿出桃花扇,思念李香君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而在栖霞山被收留之后,侯方域再次拿出桃花扇,“天老地荒,此情无尽穷”的感慨既是对李香君的想念,也是对于国家无望的怅然。
就是从“却奁”开始,他们的婚姻埋下了被拆解的伏笔,阮大铖因为被拒而开始报复,侯方域只能暂避史府,从此两人各不相见,只有桃花扇在彼此之间传送折射出他们曲折的命运。爱情被解构,婚姻被拆解,政治化的现实便是让他们感受到了国破家亡的悲剧,无论是“一腔热血挥洒”的左良玉,还是“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的史可法,还是在四镇作反中的黄得功,其实都在这兴亡传奇里,用实践回答“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这个问题,也用自己的热血染红了南朝这一政治桃花扇——左良玉最后拔剑自刎,史可法则跳江战死,都表现了一种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而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最后未能挽救这个国家,更在于那些权奸者的败国之举,“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也”的马世英,“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的阮大铖,以及田仰,还有福王自立的为弘光帝,最后国败时,“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忠臣和佞臣的对比,似乎都在侯方域的视野之中,由此也和桃花扇一样,成为南朝兴亡的见证。
这是爱情政治化的表达,而关于最后“入道”的出路问题,孔尚任也早有预设,在“桃花扇纲领”中,他指出:“色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而两部之锱铢不爽。气者,兴亡之数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以奇偶计之,而两部之毫发无差。”色是离合之情,气是兴亡之感,两者其实最后都归于一种道,而对于这个道,他通过两个人表达出来,一个是张瑶星,作为方外之人,“总结兴亡之案”,另一个是老赞礼,作为无名氏,“细参离合之场”,两个人物一个是见证者,一个是旁观者,“明如鉴,平如衡,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张瑶星本是锦衣卫堂官,在《闰二十齣·闲话》中出场,当时在南京城遇见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山人蓝瑛,是西湖画士,另一个则是贾客蔡益所世代南京书客,他们一起看见了南京的惨状,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帝后乘舆而来,于是张瑶星跪迎,而得到的指点是明年七月十五在南京建水陆道场,脱度一切冤魂。张瑶星曾任北京锦衣卫仪正之职,正是避乱南来看见了权奸当道,于是最后在指点之下脱离凡尘,投闲归老。
而张瑶星并不是“舍了那顶破纱帽”为自己投闲归老,而是担负着使命,那就是“总结兴亡之案”,在白云庵里,他发出感慨,“念尔无数国殇,有名敌忾,或战畿辅,或战中州,或战湖南,或战陕右;死于水,死于火,死于刃,死于镞,死于跌扑踏践,死于疠疫饥寒。咸望滚榛莽之髑髅,飞风烟之燐火,远投法座,遥赴宝山。吸一滴之甘泉,津含万劫;吞盈掬之玉粒,腹果千春。”为三位为国捐躯的死难之臣册封,让马世英、阮大铖得到因果报应,连同侯方域和李香君的花月情根,也一并割断——爱情从政治化又走向宗教化,在已无国已无家已无君已无父的情况下,“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
而另一方面,作为无名氏的老赞礼更是“细参离合之场”,在“试一齣·先声”中他登场,九十七岁的他已经阅历了太多兴亡,一出《桃花扇》他便是观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而在传奇落幕之时,“续四十齣·余韵”中再度出场,他和柳敬亭、苏昆生以文艺的方式对兴亡旧事发出感慨,于是在老赞礼“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中,柳敬亭新编了弹词《秣陵秋》:“建帝飘零烈帝惨,英宗困顿武宗荒;那知还有福王一,临去秋波泪数行。”苏昆生则编成北曲《哀江南》:“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
当“美人血痕扇面桃花”的传奇落幕,离合之情,都付流水,兴亡之感,云自卷舒,一切只不过是“突如而来,倏然而去”的境界,“江山江山,一忙一闲,谁赢谁输,两鬓皆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