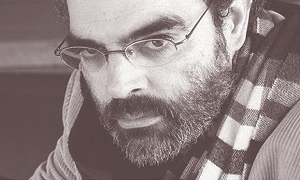|
编号:C38·2211108·1791 |
| 作者: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9.00元当当29.50元 | |
| ISBN:9787020165759 | |
| 页数:212页 |
“瓦莱里先生渐渐意识到,如果高个儿们也不停地跳跃,他是无法在垂直线上超越他们的。想到这儿,瓦莱里忽然泄了气。但疲倦感盖过了失落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瓦莱里先生放弃了跳跃,彻彻底底的。”这是对“四先生”之一瓦莱里的相关描述。《四先生》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创作的“街坊系列”中的四篇,分别讲述了四个街坊人物的日常趣事,而又将人物冠以著作诗人和作家的身份:瓦莱里先生、亨利先生、布莱希特先生、卡尔维诺先生;每篇又分成许多简短篇幅来叙述,有时甚至就一句话。正是这样奇特的碎片式的叙述形式,使他的创作难以归类为现有的文学形式,然而读来却饶有兴味。若泽·萨拉马戈评价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带着彻底原创的想象力闯入葡萄牙文坛,打破了所有传统的想象边界”。本书由塔瓦雷斯的妻子瑞秋·卡亚诺插画。瑞秋·卡亚诺是艺术家及插画师,为多部作品画过插图,曾荣获年轻设计师奖。
《四先生》: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
卡尔维诺先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再也无法前行了)。在那儿,他终于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无穷无尽。他把地址记录在了笔记本上。而最后,卡尔维诺先生终于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卡尔维诺先生》
卡尔维诺先生在漫步,他是不会停下来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讨厌等待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不会改变线路的卡尔维诺先生。从白天,到夜晚,卡尔维诺先生漫步在一条狭窄的路中间,位于两条平行线之间,他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因为“正巧在两条线中间”,“他走啊走,他走啊走,两条平行的直线非常完美,而他走在中间。”但是,走着走着,那条狭窄的路开始出现了变化,走着走着,两条平行线交汇在一起,走着走着,他再也无法前行了。
两条平行线,两条直线,以及中间狭窄的路,三条线应该是不会相交的,永远不会,但是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端点,一个阻止卡尔维诺前进的点,当平行线交汇在一起,前方便不再有路。这是目标的消失?这是方向的抹除,这是行动的取消?但是,在这样一种平行线交汇而成为点的“谬误”中,卡尔维诺先生却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无穷无尽。于是他把地址记录在笔记本上,于是,他抵达了乐格兰特路——曾经有人向卡尔维诺先生打听这条路的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并不知道有这条路,这是一种未知的状态,但是正是从未知开始,他在最后平行线相交的不可能中,在无穷无尽的可能里,真正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这是一个传说变成现实的故事?平行线发生变化,便是规则发生变化,抵达乐格兰特路,便是行动具有了结果,卡尔维诺先生的漫步无疑形成了规则的不可能和行动的可能的相异性存在,而这种相异性便是卡尔维诺不停下、讨厌等待和不改变线路的结果,便是他用不同的方法、喜欢走路、不再做计划的效果,闯入无穷无尽的世界,开辟未知的领域,抵达传说的世界,这是不是卡尔维诺先生行动的最大象征意义和卡尔维诺先生本身的最大符号体系?在他面前当然是一个规则的世界,杜尚帕先生就对他说过,“我们必须制定一下规则,这样才能知道谁赢了。如果我是裁判。”随后倒出了全套的玩具组件,这是游戏之前对规则的制定,但是规则是什么,如何制定?卡尔维诺先生也是这样问杜尚帕先生的,杜尚帕先生说:“你先开始,然后由我结束。”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反驳说:“你先开始,每个公式可以改变作为一个规则,那么我呢,制定最后一个。”
由杜尚帕开始制定规则,这是一个由他人开始的规则体系,从规则才能进入游戏,从游戏才能知道谁赢谁输。这是一个关于规则的规则,但是卡尔维诺先生把最初规则的制定权交给了杜尚帕,并不是取消了自己的制定权,重要的是,即使别人先制定了规则,因为自己是最后制定规则的人,那么最初的规则也可以被改变——被改变成为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将,他更具有决定权,或者说他把规则变成了和自己有关的存在,他人的规则只是一种游戏的初设,而自己的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从《三个梦》开始,卡尔维诺一直在改变他人规则的行动中,一直在自我规则的运行里:第一个梦里卡尔维诺先生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中抛掷而下,在抛掷的同时他忽然感觉到不对,于是冲下了窗口,一跃而下,试图去抓住皮鞋和领带——这是游戏的开始,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抛掷而下,受重力的作用将会很快到达地面,这就是被他人规则控制的结果,但是卡尔维诺先生自己一跃而下,他在空中系紧了鞋带,系好了领带,当领带的最后一个结在落地的瞬间完成,“时间恰到好处,一次完美的着陆。”最后的规则改变了结果,完美的着陆便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最后一个”的体现;第二个梦也是如此,蝴蝶慢慢靠近他的左耳,蝴蝶慢慢通过他的耳朵,在翅膀的煽动中,蝴蝶进入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而且,“蝴蝶在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里挥动着翅膀,小小的翅片一开一合,卡尔维诺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它的震动,他为之沉醉:仿佛从这刻起无需再考虑其他,仿佛世界一切终于被理解和接纳,无需再理会人类的纷扰。”蝴蝶闪动翅膀,蝴蝶靠近耳朵,按照规则来说,蝴蝶只是一个外物,甚至干扰了卡尔维诺先生,但是它却在梦中被改变了,进入耳朵,进入脑袋,进入心里,最后变成了美的化身,在不理会人类的纷扰中,让卡尔维诺先生感觉到了幸福;第三个梦,卡尔维诺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在关于事物利率的争论中,被一条鲸鱼吞食了,吞食便是死亡,这是规则具有的效力,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在鲸鱼的胃里,还在讨论关于石油和书籍的贸易,最终他决定43%的利率,在这个数字确定的时候,他早已经离开了合伙人,他是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说出了自己的数字。
卡尔维诺先生的三个梦,都是从他人已经制定的规则出发,然后发生了改变:在落地之前完成了系紧鞋带系好领带的事情,让蝴蝶在自己的身体里闪动翅膀,在鲸鱼的胃里确定了最终的利率,而卡尔维诺先生做出的改变成为了他自己规则的一部分:他体会到了完美的着陆,他感觉到不受人类烦扰的幸福,他结束了关于利率无休止的争吵。所以这是一个从他人规则到自我规则改变,并拥有完美和幸福的世界,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的象征意义:在《卡尔维诺先生的宠物》中,他养的宠物小猫“小诗”从二楼跌下摔死了,第二天卡尔维诺先生又领养了一只小猫,还同样取名叫“小诗”;在《假期中卡尔维诺先生的来信》中,卡尔维诺先生给安娜的信中说到了那片肥沃的土地,说到了年轻夫妇在田野中耕作,但是最后被改变了,“对于一个聋子来说,窗子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光泽。”在《太阳》中,卡尔维诺先生发现书架上的书籍因为太阳的照射,很多书页都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光线好像一只锯齿类动物,啃去了书本封面鲜艳的颜色。”这是太阳光带来的改变,这是书籍颜色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在卡尔维诺先生那里变成了太阳的阅读,“太阳也有它小小的愿望:它渴望打开书本。于是,它将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书籍的封面上,期望翻开书本,进入扉页,进行阅读,从那些句子起,渐渐地与诗歌心心相印。”所以在太阳对书的阅读中,卡尔维诺先生也开始了自己的阅读,他像太阳一样,他和太阳一起,“之后,一本接着一本,每天清晨,他都会重新翻过一页。”
从规则出发,然后发生改变,最后拥有幸福和完美,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到的启发,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出的规则:“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痴迷于方法学:我喜欢用多种方法来处理一件事情。有时候,他迷恋事物:我喜欢用一种方法来处理多种事情。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又对此重新洗牌:我喜欢在同一时间用多种方法处理不同的事情。”所以人的一生需要尝试而不是无用的计划,所以人需要不停地走路而不是停下来,所以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要等待,所以在平行线中间行走最后即使无法前行了也是无穷无尽的开始,从来不知道的乐格兰特路于是变成了自己脚下的路——这不是那个向他打听这条路的人想要寻找的乐格兰特路,而是属于最后制动规则改变了游戏的卡尔维诺先生的乐格兰特路。
这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笔下的“卡尔维诺先生”,和意大利著名作家同名的卡尔维诺先生,在塔瓦雷斯那里就是一个永远探寻方法、不会放弃、不想等待,甚至是制造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的人,他具有的最大意义是:改变。这种改变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是对已知世界的否定,是对游戏精神的阐述,当然最后的完美和幸福,就是回归于卡尔维诺先生的自我世界。无疑卡尔维诺先生是规则的胜利者,他的方法学重要的就是体现了实践主义。但是同样是自我世界的构筑,同样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塔瓦雷斯笔下的“瓦莱里先生”和“亨利先生”则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瓦莱里先生个子不高,他喜欢跳高,并且认为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和高个儿一样高,因为他自己站在凳子上。他还计算出凳子的高度,还画下了那只凳子,甚至还幻想在跳跃的一瞬间可以阻止重力,于是,“最后,瓦莱里先生决定想象自己的高度。”这是瓦莱里先生用想象的方式改变自己,和卡尔维诺先生一样制定了最后的规则,但是他并没有抵达属于自己的乐格兰特路,“自然而然地,为了保持高度,瓦莱里先生失去了朋友们。”在《帽子》中也一样,他一直以为自己戴着帽子上街,还作出了脱帽的动作,但是这一切只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于是他出尽了洋相,于是他被视为无力之人,于是他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平。
和卡尔维诺先生的实践主义不同,瓦莱里先生注重的是想象,他期望从想象的世界中发现完美,而想象在纯粹封闭的自我世界设计,便成了幻想,便失去了逻辑——在瓦莱里先生的幻想世界里,他总是建立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理论,在世界多元而幻想唯一的矛盾中,瓦莱里先生只能靠自圆其说的方式活在自我欺骗的“完美”中:他画了一个盒子让宠物进去,一个孔在上面一个孔在下面,他不为一个盒子而伤感,但是宠物本身也是自己画成的空无,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宠物;他用左手取左边的东西,右手取右边的东西,“世界有两边。左边和右边,就和身体一样。而错误的产生通常因为有人用左边的身体取世界右边的东西,反之亦然。”有人问他的是:当你的身体背对着它们,你如何判断哪边是左边哪边又是右边?被问住的瓦莱里先生粗鲁地回答:“我从来不会背对着它们。”他穿了一双鞋,右脚是黑皮鞋左脚是白皮鞋,回到家对换了皮鞋又重新走在大街上,于是左脚穿着黑皮鞋右脚穿着白皮鞋——如果按照左边永远是左边右边永远是右边的理论,那么瓦莱里先生是不会背向世界的,但是当两只脚的鞋被更换了,是不是黑和白对应的左脚和右脚也必然发生改变?对此瓦莱里先生抛弃了前一种规则,他认为自己没有穿反,“看上去是个谬论,但事实确凿。如果把双脚上的两只鞋进行对换,之后肯定又会重新再换一下,使之看上去是对的。”按照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他推翻的是常识,“一幅画的画面一定是对的,这样看起来另一幅画就是错的,因为这两幅画是反的。如果说,这两幅画都是错的,真正的原因是它们都是正确的。”
左手和右手各自取属于自己方向的东西的实名论,左脚和右脚变换了黑皮鞋和白皮鞋的原因论,称呼女人是X就是X,称呼她是Y便是Y的命名论,都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的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在自圆其说中变成了纯粹自我的逻辑学,于是常识不见了,于是真相没有了,于是原因被改变了——于是平衡变成了一种自设的存在,于是公正变成了自私的行为:瓦莱里先生说:“让真相幸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之倍增。如果真相是唯一的,而剩下的谎言却数以亿计,那么真相是很难被发现的,它成了一个奇妙的偶然;而谎言,却恰恰相反,充斥了每个角落。”瓦莱里先生说:“只有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赛才公平。但这不存在,你懂。如果条件都一样,怎么可能允许一个人在开赛前就位于另一人的前面?比赛的结果通常和开始一样。”
真相需要倍增才能击败谎言,在结果面前原因毫无价值,所有条件相同才是公平所以公平不存在……瓦莱里先生就是在一种自我的完美主义中,但是很明显,他所要反对和攻击的也是他人规则,也是控制论的逻辑,在《幻影梯子》中他转过身背对着给出恼人评论的人,说出的那句话是:“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但又对它评头论足。这就是人类。”攻击人类,指责人类,就在于人类既“请求我画下幻影”,又对它评头论足,所以对抗人类,就必须用幻影来解构幻影,用逻辑来反对逻辑,用真相来代替真相——制造幻影的人类,也制造着规则,正是在这一点的揭露和反抗中,瓦莱里先生和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着相似性意义。
|
|
| 塔瓦雷斯: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 |
和瓦莱里先生沉湎于幻想不同,“亨利先生”则完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苦艾哲学”,塔瓦雷斯给亨利先生的题辞引用的是亚历山大·奥尼尔的一句话:“文学品自苦艾/苦艾胜似红酒。”亨利把苦艾酒看成是一切,“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不过是有苦艾酒。”脑袋是苦艾酒,硬币是苦艾酒,常识是苦艾酒,“苦艾酒是我关于世界的理论学。我思考的体系叫苦艾酒。”苦艾酒喝下去,激发的是感性世界,它或者令人激动,或者使人兴奋,或者让人疯狂,而这种感性主义却变成了亨利先生的理论和体系,变成了一种理性主义,这是不是一种悖论?亨利先生总是在对他人说话,他站在人类世界的维度里,而且他念念叨叨的都是关于人类科技的进步:显微镜发明于一五九〇年的荷兰,第一台感应电动机于一八八五年问世,罗马尼亚人从一八五七年开始开采石油,十八世纪意大利人制造出了第一台钢琴……
科技进步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亨利先生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数学,“很久以前,存在两种数学,而现在,只有一种数学了。”当一种数学占据了世界,它其实是机械主义,其实是理性主义,所以亨利先生要在苦艾酒中找到思想的另一种力量,“酒精的好处在于它在体内自由行走,好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让离经叛道的想法更加蠢蠢欲动。”一切技术的进步都是为了让人类更自由,像苦艾酒一样,但是亨利先生的这种自由所要实现的是无政府主义,从而变成一种个人主义的身体哲学,“身体,鼻子和你们的脸蛋。比如我的脸蛋,你们仔细观察,有身体现象,有鼻子。但最重要的它是一台理性机器、一个会思考的动物和一座哲学工厂。”身体变成理性的机器,身体学会思考,身体构筑哲学体系,而身体便是世界的本质——当属于自我的身体承担起人类理性和哲学,成为世界的本质,那么很明显他人世界便也成了瓦莱里先生所说的“幻影”,于是亨利先生也攻击了人类的醉酒状态,“从今天起,我只会开口要更多的苦艾酒,剩下的谁也听不见了。因为,实质上,诸位阁下是醉汉的集合体。从今天起,只有本质。”
卡尔维诺让改变成为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瓦莱里先生在梦想世界里建立逻辑消除人类的幻影,亨利先生在苦艾酒中构筑无政府主义和身体哲学,他们都是站在人类规则的对面,而塔瓦雷斯笔下的“布莱希特先生”更是处在他人的包围中。布莱希特先生喜欢讲故事,而他的故事总是以“消失”为结局:《失业及儿子们》中的那个人失业了,听人说,如果同意切去一只手就可以提供工作,他同意了,一只手被切去,另一只手被切去,后来连砍头的要求都答应了;《会叫的猫》里,猫学会了老鼠的叫声,它很快就能抓到老鼠,但是那些猫也把它当成了老鼠,于是它被猫吃掉了;还有被子弹射中左翅、右翅、左脚、右脚的鸟儿,终于开始致力于歌唱;肥硕的女人为了减去重量要求医生切掉自己的一条腿……
被切去了手和头的失业者,学会老鼠叫声而被猫吃掉的猫,没有了四肢唱歌的鸟儿,为了减肥不要腿的女人,这都是用失去换来的拥有。更深一步来讲,人类就是活在这种悖论世界里:蜗牛几代人都在爬行为的是抵达百米线的终点,但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快要接近终点,“蜗牛们停下了。”彩虹是美的,彩虹消失而变成灰色的天空,人们也认为灰色是美的;这个国家伟大的诗人们写下的是监狱里带电电网上的诗句:“凡触碰者,即亡。”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在被解构,一切也都变成了无,但是这种消失的背后是人类的荒谬荒诞和荒唐,所以布莱希特先生讲述的故事带着对人类的嘲讽:在《人》中,某一个国家里出现了一个有两个脑袋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永远充满幸福感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哲学家的重要性》中,哲学家表示人类是唯一重要的,动物只能做无意义的事,最后他被一只老虎吞食了——反讽的是,人类的重要性仅仅为无意义的老虎提供事物。
一只母鸡发现了方法,用以解决城市里人类的问题,可以让人类安居乐业,它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最伟大的智者,最伟大的智者又将这个方法告诉了其他智者,于是七名智者在讨论后认为,“为了避免一切为时已晚,先把这只母鸡吃了。”这是布莱希特先生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当他讲述这个寓言,他想用那只母鸡讽刺人类的智者,但是最后他也变成了母鸡:在最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客厅里空无一人,但是在讲完那些故事之后,他发现客厅里坐满了人,他们是故事之外的他人?他们是故事里的母鸡?他们是有着生杀大权的智者?这是人类制造的幻影,这是人类的醉酒状态,这是人类制定用失去换来拥有的规则,“四先生”的布莱希特发出的最后问题是:“人因为太多而把门堵住了。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呢?”已经抵达了乐格兰特路的卡尔维诺先生没有回答,在黑与白上与下进与出左与右对立世界里瓦莱里先生没有回答,沉浸在苦艾酒哲学体系中的亨利先生没有回答,只有写作了《四先生》的塔瓦雷斯用212页的文本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