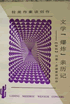 |
编号:E64·1951216·0225 |
| 作者:(智利)何塞·多诺索 | |
|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3.20元 | |
| 页数:210页 |
何塞·多诺索,一个带着悬念和鬼魂的作家,给拉丁美洲原先沉寂的文坛一个冲击,《污秽的野鸟》、《别墅》、《旁边的花园》,看看这些小说的题目,就能充分感受何塞·多诺索的个性。这位智利作家一直在追求着国际化的现代写作,就像他自己所言,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活和时间。“我愿意成为和我相反的人”,正因为如此,他鄙视拉丁美洲的权势,并且对一贯的现实主义有一种破坏的欲望,何塞·多诺索说:“只是一个样子的人使我厌倦。””
但是,我说,他们主要是继续分散,继续个性化,把“文学爆炸”甩到后头。
–《十年之后》
1982年的何塞·多诺索显然是以被唤醒的方式写下了《十年之后》这篇文章:在时间意义上,动笔于“十年”之后,无疑是回到了作为起点的1972年,正是在那一年里,何塞·多诺索写下了《“文学爆炸”亲历记》,当亲历的“文学爆炸”在十年之前发生,“十年之后”无非是一种夹杂着尾音的附录;而在1972年的文章里,何塞·多诺索就预言了“文学爆炸”“很快就会过时”,他甚至在那时就清晰地标注了这一运动的起始和终结:1965年,“始于在卡洛斯·富恩特斯家里那穿得珠光宝气裹着裘皮形象严肃的丽塔·马塞多主持的那个庆祝会”,而1970年除夕,在在路易斯·戈伊蒂索洛在巴塞罗那的家里,由玛丽亚·安东尼娅主持的盛会就标志着它真正的结束。
始于“珠光宝气裹着裘皮形象”的庆祝会,终于辞旧迎新的巴塞罗那圣会,当何塞·多诺索以这样的方式书写“文学爆炸”的履历,显然有些戏谑的味道,仿佛一场波及美洲、影响世界的文学运动只是一个沙龙式的讨论:既起始于文豪的讨论中,又消失于贵族的狂欢里。但是,何塞·多诺索却也不是心血来潮定义“文学爆炸”的时间,即使撇出和沙龙有关的定义,他也认为,当70年代所有人都想挤进“文学爆炸”队伍之中,都想为自己的创作贴上标签,都将其视为荣耀的象征时,一切就真的发生了质改变:“最后进入70年代一切都变了,变成一个大杂烩,很难弄清其价值,难以判断。”而即使在“十年之后”,何塞·多诺索被唤醒重新关注“文学爆炸”,他也依然认为,70年代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矛盾似乎在那里,何塞·多诺索为什么要写作《十年之后》,将目光再次聚焦“文学爆炸”?因为这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标记,无论对于美洲文学来讲,还是对于“文学爆炸”来说,“就像是给一个情节复杂且千头万绪的故事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何塞·多诺索这样说,而在十年之前,何塞·多诺索也有过预言,在他看来,《百年孤独》标志着“文学爆炸”进入了第三时期–第一时期的标志人物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认为,“他是第一个与欧美大作家建立友谊的人–第一个被美国评论家视为第一流小说家,他第一个察觉他那一代的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并且第一个慷慨而又文明地让人们知道这一点。”而第二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个当时年仅24岁的作家的作品获得了巴塞罗那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的“小丛书”奖。
“以我的眼光来看,第三时期–也许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爆炸’作为’爆炸’的决定性时刻–是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发表到来的。”《百年孤独》的发表标志着“文学爆炸”进入了决定性时刻,《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故事走向了“圆满的结局”,其实完全契合何塞·多诺索对“文学爆炸”一贯的主张和判断,圆满即结束,决定性时刻即退出舞台的时刻,当他在1982年再次回望“文学爆炸”,其实对于这一运动的想法还是清晰的,在他看来,这个已经达到鼎盛的文学将会“不时兴”了,甚至《百年孤独》在文本以外也推动了“文学爆炸”的终结:“所有这一切:诺贝尔文学奖,中学和大学需要这本书,出书有利可图,很能说明近十年来那个曾经是有争议、并且被诅咒的’文学爆炸’的际遇。”
“十年之后”无非是何塞·多诺索的一种坚持,在他看来,“文学爆炸”有过红火,甚至产生了排山倒海的气势,甚至小说一时取代了诗歌在拉美文学的垄断地位,但是在70那个除夕之后,“文学爆炸”就走上了末路–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够在十年之后还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因为他和科塔萨尔等人一样忠于某种革命事业,而更多的人“凑热闹地摇摇摆摆而已”。这里的一个认识是:当“文学标签”成为一种集体的标签,是走向整体性的文学标志?还是为它本身带来了危机?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是,一位住在巴黎的巴拉圭作家,当他获得了一项“美洲作家”的奖项之后,郑重宣布,凭借获奖的作品,自己已经跻身于“文学爆炸”行列了,对于这样一种沽名钓誉的人,何塞·多诺索用嘲讽的口吻说:“真是个傻瓜……太天真了。这就像相信有圣诞老人一样。”
让自己贴上标签而成为“文学爆炸”作家,这是“十年之后”很多人的功利目的,这是“文学爆炸”利益化、商业化的可悲。但是撇除这些沽名钓誉者,其实何塞·多诺索认为“文学爆炸”会过时,更在于他对曾经坚持着创新和革命的作家的担忧,本来“文学爆炸”就是不是以整体性观念和纲领统领的一个流派和运动,分散性是它的主要特点,但是当人们以“个性化”为借口从事创作活动,当“文学爆炸”失去了秩序和准绳,其实在创作主体上自行解构了“文学爆炸”本身:很多人搬了家,换了妻子,儿女长大,不断出书,“他们走到全世界的大街上都有人认出他们,请他们签名。”最后的“文学爆炸”真的变成了一个只是贴着标签、低价的包裹。
十年之后认为“文学爆炸”必被甩到后头,十年之前认为“文学爆炸”处于危机中,这一切都是源于何塞·多诺索的忧患意识,而当他真正亲历了“文学爆炸”的时候,其实对这一切是充满了希望–时间仿佛很规律地划分出三个时间点: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爆炸”走向圆满的结局;时间往前推10年,1972年写作《“文学爆炸”亲历记》时,他已经预判了危机将会出现;时间再往前推10年,正是1962年,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当何塞·多诺索得知富恩斯特将参加大会时,他打听了飞机到达的终点,像一个崇拜者一样,胳膊底下夹着富恩斯特的《最明净的地区》,希望他能给自己签名–“我有点失去了我为人有点矜持的本性”,这对于何塞·多诺索来说,是多么富有激情的举动,是多么珍贵的个人回忆。
而这种激情和珍贵,似乎也说明那时的何塞·多诺索对新时代的文学充满了期望,富恩斯特以及他的作品何以让何塞·多诺索丢掉了矜持,甚至有些疯狂地只求得一个签名?对于作家和作品来说,何塞·多诺索是赋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富恩斯特“给予我一种新的眼光”,这种眼光使自己获得力量,“使我感到有必要将此观念化为已有,运用于纯粹文学的范围,也运用于最世俗的各个领域。”而那部《最明净的地区》,在他看来是属于拉丁美洲特色非常突出的书籍,这种书籍具有一种使命:“挖掘我们的城市和我们国家的深层,以揭示实质和灵魂。墨西哥人、利马人、阿根廷人的实质是什么?当今的作家很少有人劳神去探究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实质是什么。”所以到机场等候、签名,对于何塞·阿多诺来说,更具有一种追随的意义,那就是像富恩斯特一样,拒绝表面虚伪的东西,“他采取的态度,不是像束缚着我的范围之内的小说那样是一种文献式的,而是质询式的;是指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
|
何塞·多诺索:我想损坏,碾碎,摧毁那东西 |
挖掘深层次的东西,触及实质和灵魂,以质询的方式指出问题,这一切在何塞·多诺索看来,就是代表着文学的希望,而这个文学,就是基于这块大陆生长、突围和创新的“西班牙美洲小说”。将这块大陆的文学命名为“西班牙美洲小说”,其实是一种对于地域的突围,而“文学爆炸”的真正意义就是寻找和实践一种国际化的思维,“我觉得最近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最有意义的变化总是与国际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要走向国际化,就必须超越地域限制,就必须扩大范围,就必须有开放性视角,而这些对于“西班牙美洲小说”来说的使命,正是源于60年代的美洲文学处在一种自我封闭、各自割裂,甚至臣服在权力之下。
克里奥约主义作家、地方主义作家、风俗主义作家和社会现实主义作家,在何塞·多诺索看来,都是60年代横亘在美洲文坛上的路障,他们的共同标准就是写作“我们的事物”:“他为自己’教区’写作,写自己的’教区’里的事情,用他那’教区’里的语言,面向他’教区’提供给他的读者–读者的数量和质量大不相同,巴拉圭的不同于阿根廷的,墨西哥的不同于厄瓜多尔的–除此之外,不能有更多的奢望。”这便是现实,关于社会问题,关于种族,关于风景,都成为衡量文学质量的尺度。无疑,“我们的”、“教区”都反映的是地方性事物,也就是他们以贫乏、短浅甚至闭塞的视角来写作;另外一方面,从何塞·多诺索自我经历来看,真正的小说创作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当时的命运就是自费出版,就是顶风冒雨去卖书,“在智利这个环境中我感到窒息”。
正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作家的定义是:“为自己驱魔的人。”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美洲迎来了一种开放,欧美外国文学影响了这片大陆,“这些新作家一方面使我们眼花瞭乱,另一方面又渐渐造就了我们。”
他们是萨特和加缪,我们刚刚挣脱他们的影响;还有君特·格拉斯、莫拉维亚、兰佩杜萨;不管是好是坏,还有达雷尔、罗伯-格里耶以及他所有的追随着,塞林格、凯鲁亚克、米勒、弗里施、戈尔丁和卡波特,以帕韦泽为首的意大利作家,以“愤怒的青年”为首的英国作家,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我们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这一切都是至少是在虔诚地生吞下并消化了“经典作家”如:乔伊斯、布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福克纳的作品之后。
无疑这正是美洲文学的契机,而对于何塞·多诺索来说,是找到了自己“文学上的父辈”。也正是在这一机遇的造就下,1962年在康塞普西翁举行了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虽然在大会上一些讨论的创造性建议并没有完全被采纳,但是何塞·多诺索认为,它的最大意义是国际主义思维,“说到’我们的’这个提法,已不光是指智利的事物了,而是指我和智利能够实现的,也必然会让成千上万组成讲卡斯蒂利亚语世界的读者感兴趣的事物,从而打破那些划得如此分明的国界,创造一种更广泛、更国际化的语言。”“我们的”不再只是“教区”,不再只是智利,甚至不再只是美洲,而是世界;不仅是地域意义的世界,也是人与人敞开的世界–何塞·多诺索对于富恩斯特近乎崇拜的表现其实真正的意义在于:“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鼓舞。”
打破地域限制,创新创作手法,更具世界目光,这种革新意义其实不光是指思维习惯,1962年的大会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古巴革命事业,而当时参加大会的作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古巴革命事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在何塞·多诺索看来,也构成了“文学爆炸”统一性的一个方面–现实层面的革命事业,一样被归为文学的一种实际行动,而作家们之后集体式的“流亡”生活,则成为他们不竭的创作源泉,这种“流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逃离“我们的”封闭世界,以一种自由、开放甚至牺牲的方式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所以何塞·多索诺总结出“文学爆炸”真正的同一性特点便是:流亡、世界主义、国际化,“所有这些或多或少有联系的因素,构成了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相当重要一部分。”
1962年的大会在何塞·多诺索看来,才真正标志着“文学爆炸”的开始,从富恩斯特到略萨再到马尔克斯,当“文学爆炸”经历了三个时期,辉煌也就意味着结束,“文学爆炸”如此昙花一现,当然更多是何塞·多诺索自身对于这一运动的考量,在他看来,帕迪利亚事件产生的幻灭使得古巴革命的激情消失,从而使得“文学爆炸”失去了外在的革命热情;“文学爆炸”本身缺乏统一的理论和立场,分散化的状态没有使之具有完整的总体性;缺乏秩序和准绳则使得“文学爆炸”成为了一种标签,在利益化、商业化的驱使下慢慢失去了创新意义;而流亡的作家在政治性为中已经不能回家,它使得“西班牙美洲小说”真的变成了一种没有归宿的流亡文学。
何塞·多诺索是忧患的,也是悲观的,而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的这种忧患意识和悲观心情也是站在自己作品立场上,对整个时代做出的判断,从自费出版到街头卖书,再到从富恩斯特等前辈身上吸取经验,打开世界的目光,何塞·多诺索就是为了打破困囿于自身的一切限制,在和莉莉·乌尔迪诺拉会见时,他指出智利令他感到忧虑,其中的士气、混乱、谎言和公众的不信任感,使自己感到压抑,“在智利,无法与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交往……”希望作家是人民的一部人深入到人民中去,最后却只能在隔阂中,所以何塞·多诺索把内心的希望寄托在小说创作中,在谈及《污秽的夜鸟》时,何塞·多诺索就说,“我想损坏,碾碎,摧毁那东西,并且弄明白它究竟是什么,并且达到什么程度,弄得我的生活荆棘丛生,把我也变得有如魔鬼。可以这么说吧,这反映了我自己变得像魔鬼。”所以他对“伪装”感兴趣,所以对人造的东西寄予厚望,所以会创造对称,这一切都是对现实的解构,都是想用“文学爆炸”来摧毁一切。
在“文学爆炸”的亲历中,何塞·多诺索无疑感觉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都在自我意义上实现了“爆炸”,这是对“我们的”狭隘目光的超越,这是对“教区”的贫乏世界的突围,这是对国际主义的构建,所以,在康塞普西翁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十年之后,在《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之前,何塞·多诺索说:“我觉得,自己与60年代的小说的国际化的进程是如此密切相关,因此当我写自己关于国际化进程的亲身见闻时,写着写着,就觉得是在写自己的一段自传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