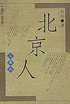 |
编号:X26·01960501·0282 |
| 作者:曹禺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5.05元 | |
| 页数:187页 |
1941年的曹禺,已经度过他彷徨的时期,“在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曹禺远离了《雷雨》中的呻吟,而看到了自己可以前进的方向。在这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戏剧作品中,以大汉“北京人”来反衬曾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腐朽与新生之间的较量。在该剧中,曾瑞贞的出走显然是作者对政治生活的一类幻想式的图解,而缺少更具体的铺垫。
“北京人” (徐徐举起拳头,出入意外,一字一字,粗重而有力地)我——们——打——开!
——第三幕
这是1941年彷徨之后的剧本,这是1996年被蒙尘的图书,当这本187页的书重新从书橱的角落里翻将出来,重新置于案桌之上,重新从第一页开始看起,仿佛听到的是那一声粗重而有力的喊声“我——们——打——开!”打开的是一部剧本,打开的是一个故事,打开的是一种声音——北京人就是以现实和象征的方式打破了某一种固有的秩序,如重生一般进入到“现在时”。
而对于这一个发生在遥远时代的故事来说,当北京人用拳头重重地打开一扇没有钥匙锁着的门,也具有了双重的含义,北京人是居住在背景的曾氏一家,北京人也是被视作哑巴的原始人,北京人是老朽时代封建专制的门第产物,北京人也是冲破束缚渴望自由的现代激情,北京人是见证辉煌却又走向衰微的家族,北京人也是不说话却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当在引号里、具有隐喻意义的“北京人”打开这一家北京人的大门,是一种象征破坏另一种象征的力量,是一个生命引领另一个生命的重生。
北京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是对于一个逝去时代的缅怀,曾氏家族曾经煊赫,曾经辉煌,曾经盛极,作为一个大家门第,当现实无情地摧毁了这一切,当时代残酷地埋葬所有,他们只能走向衰微走向落寞走向死亡,花园里的草木已经荒芜,屋内的柱梁已经褪色,墙壁的灰砌已经剥蚀,甚至隔窗也只是用纸糊起来。冷寂,空洞,奄奄一息,而在里面的那些人,似乎也和这衰微的大家门第一样,走向时代的边缘。
但是这房屋里却还有最后一座堡垒,那就是老太爷曾皓,六十三岁的曾皓见证了祖上的荣耀,见证了家族的辉煌,当走进这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他自然采取的是固守历史的方式,在他看来,祖宗留下来的繁文缛节必须遵守,必不可少的家教必须保持,家长的威严必须加强,所以对于这一个日渐衰微的家族,他却说:“这房子是先人的产业,一草一木都是祖上敬德公惨淡经营留下的心血,我们食于斯,居于斯,自小到大都是倚赖祖宗留下来这点福气,吃住不生问题。”
生活在祖宗的世界里,当他自己成为最后的长辈时,自然要延续这种权威,而这无疑是想象的一种辉煌,中秋节让晚辈败节是一种仪式,而守护着自己那口棺材更是一种仪式,存放了十五年的棺材,上了一百多道油漆的棺材,这是他死亡的符号,但是在曾皓看来,却是彰显权威的另一种象征。六十三岁的老人是最后一座堡垒,还在支撑着的房子是最后一座堡垒,连存放死亡的棺材也是最后一座堡垒。而在这个最后堡垒里,曾皓更像是一个活死人,他吝啬、他自私、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怜悯着自己,但是当自己放大了时代给他造成的不幸之时,一种可怜的权威维持,又让他看不到别人的痛苦。
其实,当生活在这座最后的堡垒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朽败的象征世界里感受到痛苦,每个人都像一个活死人。处于虚幻权力最高处的是曾皓,而在实际权力中心的则是他的媳妇曾思懿,一个贪财若命、笑里藏刀的人,在人前她微笑,说着动听的话,而身后则是自私虚伪的代表:对于曾皓,她似乎是言听计从,以一个听话的媳妇示人,但是却把已经变坏的人参给他吃,希望老头早早死掉;对于奶妈,她笑脸相迎,没有主人的架子,但是在背后却骂奶妈嘴巴臭气熏天;对待儿子曾霆、曾瑞贞也是和蔼可亲,却总是算计,对于照顾曾皓的姨侄女,表面上也是给予照顾和同情,暗地里却因为和丈夫暧昧关系而心生仇恨……实际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权力代表,她是这个北京人家族的中心,甚至是她主宰着个人的命运。
 |
| 曹禺:在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 |
北京人这个家族组成的权力体系,自上而下都透着腐烂的味道,曾皓的棺材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象征,而对于第二代的曾文清和曾文采来说,则是权力变异中的自我放逐,曾文清是曾思懿的丈夫,他儿时有“神童”的美誉,但是这之不过也是一种虚幻的历史,当被母亲溺爱而长大,当门当户对而结婚,其实对于曾文清来说,自己的一生早已经被宿命所注解,这种宿命一方面是家族权力影响下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找不到出路之后的自暴自弃,他身体孱弱,他精神恍惚,他敏感而沉郁,他悲哀而无力,一种病态的身体和病态的精神,使得曾文清“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最后只能依靠鸦片才获得一种活着的动力。而对于曾文采来说,似乎也沾染上了懦弱的毛病,不仅在身体上体弱,而且优柔寡断,所有的事情都在崇拜丈夫江泰的过程中失去了控制力,反而“甘心受着她丈夫最近几年的轻蔑和欺凌”。
所以在第二代北京人懦弱、沉郁、悲哀,甚至自暴自弃的现实里,他们自然变成了被欺凌的对象,也使得一种权力体系走向崩溃的边缘,曾思懿和江泰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种取代对于这个家族形成的垂直、男权统治体系来说,自然是一种解构。曾思懿是权力崇拜的典型,她的贪财和自私为自己构建了一种堡垒,而江泰作为一个老留学生,有着西方的经营头脑,却沉溺于欲望世界,回到北京,他和那些公子哥儿一样,贪图享受,而经商的失败又让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皓,他想要这个曾经煊赫的家族为自己提供资金,甚至当看到落寞的现实的时候,他甚至想把房子卖了作为盈利的资本。
而曾家的第三代曾霆和妻子曾瑞贞,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合拍的时代气息,只有十六七岁的他们早早地组建了家庭,早早地失去了少年自由选择的权力,婚姻是门当户对的,而这这不过是继续了曾文清和曾思懿的老路,他们在热闹的锣鼓鞭炮中走向婚姻殿堂,却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住在冰冷的新房里,他们是“一双临刑的肥羔羊”,而所谓的婚姻本身就成了桎梏,“曾霆和他的妻就一直是形同路人,十天半月说不上一句话,喑哑一般的捱着痛苦的日子,活像一对遭人虐待的牲畜。”
这是三代北京人的世界,而在这个自上而下形成的朽败的结构中,还有另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愫方,她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家族里,但是这种生活对于她来说,却如死了一般,她是以照顾者的身份生活在曾皓的身边,每天为他煮参汤,每晚为他捶腿,“在老太爷日渐衰颓的暮年里,愫方是他眼前必不可少的慰藉,而愫方的将来,则渺茫如天际的白云,在悠忽的岁月中,很少人为她恳切地想了一想。”就是在这种牺牲了青春、牺牲了爱情的死寂生活里,愫方为这个朽败衰微的家族添加了一种悲剧气息。
这是一种北京人的现实,曾皓、曾文清、曾霆三代组成的体系就是把生命放在棺材里,放在鸦片中,放在冰冷的婚姻里,就如江泰那次喝多了酒所说:“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这是整天垂头丧气的生活,这是垂死挣扎的现实,这是希望泯灭的时代,这最后的堡垒和外面有推着北平独有单轮水车的人,和挑担子的剃头师傅,和磨刀剪的人一样,也是生活在崩溃和死亡的边缘。
但是在这个朽败的家族中,却始终潜伏着有一种生命最原始的力量,对于曾文清来说,他对于愫方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陷于伦理之困不敢表白,只能通过那些画作交流,另一方面在曾思懿的蛮恨和欺压下,他却需要一个倾听者,愫方也一样,她似乎在曾皓的服侍中看不到未来,但是在曾文清身上她唯一可以感觉自己的存在;曾霆是一个对鲜鲜食物有自己兴趣的少年,在袁圆的影响下,“他开始爱风,爱日光,爱小动物,爱看人爬树打枣,甚至爱独自走到护城河畔放风筝。尤其因为最近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类学者的女儿,她居然引动他陪着做起各种顽皮的嬉戏。”对于他来说,这是生命中出现的亮色,那一些游戏也仿佛是对于他从童年一下子跨入成年造成断裂的弥补,而曾瑞贞虽然和曾霆形同陌路,但是她和愫方有着共同的语言,而且在外面也接触到了一些革命思想,这让她慢慢成长为旧时代的破坏者。
虽然他们内心有着自己的欲望,虽然他们渴望逃离这样的秩序,甚至他们也有了行动,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强大的权力体系和对于新时代的不适应,使得他们总是畏手畏脚,使得他们无法彻底大秩序,使得他们又被宿命拉回到现实里。曾文清又一次毅然决然地离别,他想要离开这个家,离开自己的妻子,离开所有的秩序,也离开深爱着却永远无法在一起的愫方,消失,但最后他却又回来了,这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回归,反而是懦弱的另一种爆发。曾文清的离开,对于愫方来说,反而可以无虑地放弃一切的想法,安心在这个家族里走向生命的终点,因为在她看来,曾文清的离开就是为了让她取代他的位置,就是把一种爱传递给了她,“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他!”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她误把这一切当成是爱的最高境界。
一种内心的欲望被压制,一种积极的行动被阻止,对于曾文清和愫方来说,他们也只能成为有限的出走者,宿命又把他们推向一个悖论:出走是离开爱人,是追求自由,而走投无路的结果不如把自己囚禁在没有自由的爱里。不管是曾皓,还是曾文清、曾思懿,还是曾霆、曾瑞贞,其实在三代矛盾迭起的关系里,在即将解构的系统中,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破坏,需要另一种力量的重生,而“北京人”作为一种象征出现在这个家族里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开那扇真正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北京人似乎只属于象征意义,这一个由房子的租住者、考古学家袁任敢带来的怪物,本身就是一个闯入者,当中秋夜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是一个“猩猩似的野东西”:“他整个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满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都似在这个人身内藏蓄着。”巨大而散发着野性,当然是和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秩序背道而驰的,“四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倒是这样:要杀就杀,要打就打,喝鲜血,吃生肉,不像现在的北京人这么文明。”所以当他以黑影的方式投影到这个已经熄灭了灯的家族的时候,就是一种象征性符号的闯入:“在那雪白而宽大的纸幕上由后面蓦地现出一个体巨如山的猿人的黑影,蹲伏在人的眼前,把屋里的人显得渺小而萎缩。”
他是“北京人”,是人类的祖先,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所以北京人是自然的代表,是自由的代表,在他身上有着和腐朽的家族不一样的生命气息。
但是北京人是曾经的机器工匠,是一个哑巴,失语对于这个符号来说,则象征着那些渴望自由的人缺少一种真正的表达,如愫方,如曾瑞贞,所以要让闯入者变成破坏者,就必须赋予他另一种力量,那就是在那个曾家最黑暗的夜晚,北京人终于举起拳头,对着这个时代说出了“我——们——打——开!”那时曾家隔壁的杜家已经把漆了上百道漆的棺材当做债务抵押品抬了出去,曾皓失去了权威最后的象征;那时候,逃离了桎梏的曾文清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了家,愫方所有对于爱的美好构想都一下子坍塌了;那时,一心想要发财的江泰,因为顺手牵羊被警察抓去落得了耻辱的名声;那时,曾霆和曾瑞贞悄悄签好了离婚协议,向那一种冰冷的仪式最后告别……矛盾在激发,而新生的力量也在破坏之中成长,就如愫方那句预言:要我离开的那一天,就是“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
回来的曾文清让她失去了自我牺牲的爱,而当那堵墙最后坍塌,当哑巴的北京人说出“我——们——打——开”的时候,预言毫无意外地变成了下一步的行动,那把锁被打破,那扇门被打开,那些懦弱的人在死去,那些看见希望的人走出最后的堡垒——对于举起拳头,对于打破束缚,对于开口说话让预言成真的“北京人”来说,他不仅是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代表,也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只有英雄会引领他们走向另一条路,只有英雄才可以真正打开那扇门,“跟——我——来”是最后的态度,是最后的呐喊,是最后行动,而真正悲哀的是,敢于冲出这封建重围的却只是愫方、曾瑞贞一样的女性,那些延续北京人家族传统的男人们,自然在这个男权社会的坍塌中,成为了最后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