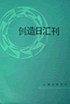 |
编号:H76·2011029·0599 |
| 作者: | |
| 出版:上海书店 | |
| 版本:1983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6.00元 | |
| 页数:508页 |
《创造日》是创造社前期为上海《中华新报》编得文艺副刊,1923年创刊,同年11月2日停刊,共出101期,本书是它的汇刊本,据光华书局1927年版印行。
这是立秋的晚上。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业者。
——郁达夫《立秋之夜》
一个穿着洋服,一个着着长衫,一个从访同乡处归来,一个则要送别赴美国的朋友,不同的打扮,不同的朋友,似乎是两个方向的行走者,似乎在面对不同朋友的境遇,但是他们殊途同归:一样是在立秋的晚上,一样是迎着风沙,一样站在三岔路口,偶遇的他们更具有相同的身份:失业者。
当郁达夫在《立秋之夜》这篇小说中描述了两个殊途同归的失业者,不管是三叉路口,还是狂猛的风,都构筑了现实的困境,他们其中一个没有坐电车回家,一个不从叉路回去,也都展现了他们的迷惘。这是无法走出的现实,这是无从抉择的生活,“二人默默前去”似乎把他们重又拉回到同一的世界里,而所谓的“同乡”和“赴美国的同志”也便成为一种隐喻:在被现实困住的立秋之夜,回到故乡或者远赴他国都不是最终的出路,“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者在那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向内回到故乡和向外走出国门的选择。
郁达夫描写立秋之夜是中国当时的普遍的现实图景,群体如邓均吾在《面包》一诗中所描写的劳工:“黄尘雨汗的劳工们,/你们最大的希望不过面包,/假如面包也有灵魂,/他会为你们同情而悲悼!”劳工和面包之间呈现的希望和失望在个体意义上更是涂抹上了悲情色彩:“现在我又听到这种尖锐的汽笛声,我正等侯我的运命来实现我的失望。我卧在这个如坟墓的床上,我的思潮杂在窗外的雨声里飘着,我满帐中都酝酿着幻想了。”沈松泉在《汽笛声》分明听见了将希望拉回来的“汽笛声”,它是运命,它是幻想,它最后是一张“如墓的床”;而如郁达夫小说中的“同乡”,全平的《故乡之游》里则让回去的故乡变成了死亡的渊薮:“这故乡,正是我理想中故乡:路上铺着正义,路上砌着真理,流着汗,流着血的小孩子,正立在路上猛力攻打那兀立的残败的古旧城墙。”当旧有的记忆和旧墙一起最后轰的一声坍塌,他发出的疑问是:“理想中的故乡,终不过是一个甜美的梦么?”
倪贻德《寒士》中的“我”,也是沉浸在这样一个梦中,只不过和梦见理想中的故乡不同,“我”梦见的是让文艺找到理想的都市生活。和朋友辩论中“我”总是认为都市才是文艺应该存在的地方,他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文艺要表现近代生活,而近代生态或显著表现在大都会里,所以艺术家就应该到大都会里去观察去描写;第二,中国古代文艺偏向于山林田野,这是一种偏离,必须进行补救;第三,都市生辉情调丰富,是简陋乡村无法达到的,所以,“南京路是常欢喜去跑的了,市内电车上是常有我的踪迹的了,夜深更静的时候,是常要踏进小酒店小面馆里去吃喝的了……”这是一种理论式的构想,而当“我”用实际行动开始进入都市的时候,起先是看不起乘坐开往南京火车上的旅客的,因为他们带着土特产,穿着贫民的衣服,而当自己真正来到南京这个理想中的大都市,才发现一切都只是梦想,现实击碎了这个文艺梦:“什么是王气金陵?什么是龙蟠虎踞?都不过是些骗人的话!在我的眼光里看来,不过只有些清冷的长街,低陋的平房,和灰色的空气的集合体罢了。”
这是一种失落,因为失落才要反过来审视理想,倪颐德的另一部短篇《江边》更是思考着青年的出路问题,亚白咒骂的是社会,“这都是受了经济的压迫,可恨的金钱哟!万恶的金钱哟!我们这许多有为的青年,都被他压制得不得动了!”而充满了失望的N更是嘲讽着自己,“我在学生时代,常冷眼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怜虫,哎!如今我自己也变了一个可怜虫了!”他终于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希望,那就是去镇江CW公学求职,坐上轮渡,带着希望而去,但是在公学里却遭遇了不公,希望破灭了,N像是被人又推向了万丈深坑,于是冰冷麻痹的他对自己说:“此地那里是我的安身处,还是回到家乡去渡孤独的生活罢。啊!我还是归去……”从失望到希望,从奔波到麻痹,N代表着一代人的困顿,当他带着醉意来到大江边,向着世界发出了呐喊:“啊啊!我若能从此地,乘风而西,过九江,泊乎洞庭,去访访屈贾行唁之地,听听潇湘夜雨之声………啊!我的屈原!我的贾生!我崇拜你们的孤高!我崇拜你们的节操!我…我……”
郁郁不得志,是现代版屈原的再现,是另一篇《离骚》的问世,敬隐渔在《破晓》中呼唤着:“我的爱,你快把门儿打开!”楼建南在《龙山顶上放歌》中代表着一代人不愿昏睡的呐喊:“我纵在这么的嘶声高歌,/黑越越的人寰还在贪着睡眠!”要告别脏脏的世界,要离开梦境,就要站在最高处,迎接照满人间的鲜红朝阳,“醒来吧!快醒来吧!”但是如何醒来?面对现实的困境,倪贻德是在怒骂,在自省,敬隐渔在呼唤,在期盼,楼建南在攀爬,在呐喊,但是也有另一种态度,张友鸾《随感录·服从》则表达了另一种“服从”的心态,在他看来,服从不是耻辱,反抗引起的争斗才是耻辱,“有能吃人的人,我们便让他吃,总比兽吃我们好些罢?兽想吃我们如果是热忱哩,我们也可让他吃,总比让‘面上不吃我,肚子里想吃我’的动物吃去好些罢?”由此他认为,服从的你我构成了永远和平的世界,而不服从的你我则制造了斗争的世界——服从选择的不是动物,不是野兽,而是人,期望用服从的原则得到和平,其实是一种卑劣的人生观,是一种奴役心态——诵邺《猎狗庸奴》给出了这种人生观的下场,当老狗最终失势,他得到的是讥讽和冷笑,是良心的呵责:“都是我底罪恶呵!一切都是我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呵!我现在觉悟了!我现在忏悔了!赦了我罢,如果你们肯宽恕我;裂了我底肢体罢,食了我底肉罢,如果你们要寻我报仇,都可以!一切我都很愿意!因为我已经觉悟了!因为我已经忏悔了!”最后等待的是被审判。
不管是面对现实而理想破灭,还是咒骂社会的不公,不管是山顶上放歌而排遣苦闷,还是以服从的媚态来换取和平,其实都是那个时代面对迷惘现实的一种态度,都是遭遇困境时想要寻找出路,而这种出路观似乎又回到了郁达夫的两个方向论:穿长衫还是穿洋服?回故乡还是去美国?东方和西方是一条岔路口,有人选择向外,王珏在《日落江上行》中问道:“西方有乐土,/友们哟!是否由这儿寻去?”敬隐渔在《罗曼罗朗》中发现了西方另一个文学世界,“如今看若望克利司多夫小孩子时代的生活倒比我自已经过的事情看得明白多了,更觉得有意思,方才知道了一点人与生命底观念。”而郁达夫则盛赞已经接受西方思想的日本在翻译上取得的成就,由此看到了中日之间文化的差异,“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西方世界已经打开了国门,但是对于西方文明还存在着矛盾心态,或者是在观望,或者是盲目接受,全平的《他的忏悔》则以“忏悔”为关键词写出了一代人的迷失。青年受到了现代思想的教育,对于父母安排好的传统婚姻存有质疑,在没有采取抗争的行动中,他希望能感化他们,“这已是定局的了。我不能违拗尊长;取社会的责怪。并且不美观可以修饰补救的,放足,读书,便渐渐的会使旧式变成新式了。”新式在他看来就是让旧式女子放足、读书,“否则不娶。”但是回家之后,这种理想主义似乎覆灭了,他还是结婚了,看着妻子的小脚,他心生诅咒:“旧式而顽固的讨嫌女人!”他以西方的平等观对照妻子,“这原不能怪她,因为旧式的女子,被家庭礼教所束缚,仅能晓得服侍她丈夫是应当的,而不晓得有所谓爱情,比服侍还要紧,她仅晓得待我好;我生病的时候,她也很关切的照料我,当心我,甚至坐在床边啜泣,但总没有爱情的举动现出来:我烦闷发怒的时候,她也会用很和慰的言语来劝解我,但总不会用甜蜜的爱情来安慰我。我所以很失望!我或者能原谅她,然绝不会爱她,虽然她是我的妻!”终于在六年之后他和妻子离婚了。“离婚”作为一个新式词语和生活方式,让他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他爱上了一个新妇女领袖,而且也成为了他的良伴,在四个月的甜蜜生活之后,他忽然发现,“他像一枚荔枝,清香的果肉,被满长棘刺的壳在外面包着。又像一粒桃核,外面的甜肉吃完了,中心藏着一粒很苦的仁。”于是他又和夫人离婚了,这次离婚是新式妻子表达了不满:“他的名誉和地位,不足以增高我社交上的声望,并且他不贡献真诚的爱情,使我的身心愉快。并且……”
他成为了独居的人,他在忏悔中感觉到了自己的谬误,“懊恨怨悔的回忆,把他的良心,从偏执的胸中现出来了。无形的责罪,使他在昏暗而阴沉的空气中,起了全身的战栗。”起先是小脚的旧式女人,后来是新妇女的领袖,但一样是离婚的命运,就像郁达夫的《立秋之夜》,不同的穿着,不同的方向,“殊途同归”的两个人都有着失业者这一相同的身份,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式和旧式,都是在同一个叉口找不到归途的人,而小说中的青年从迷惘而追求,从追求而忏悔,更是对于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一代人的讽刺,“思想是谬误的,正和美丽的她待他的差误一样。”但是这谬误和讽刺中,是需要回到旧式生活中去吗?抱着“服从”态度的张友鸾在《随感录》中再一次提出了“骸骨的迷恋”这一种被鲁迅批评的守旧思想,在他看来,西方夹面包的工具“偏是筷子一双”,“但我却不相信,西洋终会化我,而我终会永远改化而同于西洋!”所以否定要吃面包肯定只吃饭的张友鸾发出了自己的宣言:“今朝开始,我读古书!”
这是一种绝对的态度,“骸骨的迷恋”是回到故纸堆,是坚持保守派,针对这样一种对西方全盘否定的观点,洪为法在《我谈“国风”》中提出了批评,“……我们如今读国风,我以为与其费时费日去读那汗牛充栋的诠释国风的著作,不如先以自家的心灵吟味他……因为这时读者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已经感印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韩,我怕只有损失杜韩的真价值,国风(诗经全部其实都是的)之难研究,正因注家太多,我们研究时没有先跳出万千注家以外。……”《读卷耳集》更是表达了对“整理国故”的批判,“研究诗经!研究诗经!这种呼声,我得听得也好多时了。其成绩表现的在那里呢?唉!还不是旧解之迷恋—一骸骨之迷恋!谈到能摆脱一切,另觅‘诗’的真生命,在历来诗经研究上辟一个新纪元,那不得不推沫若的卷耳集。”他把郭沫若的《卷耳集》看成是“整理国故”正确主张的范本:
国风之价值之可贵,就在于它是一班活活泼泼自自由由的男女性在欢愉或悲戚的时候吐出的心声,所成就的作品,是真挚的,是自然的,是不加雕琢,我们读到它,谁不懂憬于那时作者优美可恋的世界?所惜历来解诗者多斤斤于字句,翼翼于惩劝,把一部诗经几乎变成一部“说文解字”或是一部“太上感应篇”,沫若这个小小的跃试,便是还它本来面目一个抽刀斩乱丝的办法。
正如郭沫若在《卷耳集》自跋中所说:“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说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不迷恋于古文古字,不执著于注解,而在于对其中真生命的挖掘,才是“整理国故”该有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洪为法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去从来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在翟秀峰看来则体现在成仿吾的作品中,由此他认为,“他的爱慕之情比人强,他的憎恶之心比人大,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良心,他便是良心的战士,他是对于时代的虚伪与罪孽用猛烈的炮火者。他是真善的战士,彷彿是美的传道者。”
要革“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要做“真善的战士”和“美的传道者”,郭沫若和成仿吾成为领军者,而作为《创造社》主将的他们,自然也在实践着创造的意义,而这也是“创造日刊”一直以来体现的时代意义。革命就是为了创造,战士就是在创造,郭沫若在《怆恼的葡萄》中发出了呼喊:“矛盾万端的自然,/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人间世的难疗的怆恼,/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宗在《啊我要创造个新的》中开始了自我的革新:“啊我的身躯!/啊我的身躯!/你这不可改造的物体!/我今誓将你弃去。/我要创造个新的,/如此青春之树所象征。/啊,我要创造个新的!”郑伯奇在《A与B“对话”》中探讨了创造的意义:“我只想永久活动。我只听生命活泼泼地发挥。为忠于生命,我要破除一切羁绊,打破一切藩篱。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同时我要永生!”刹那刹那地生着便是循环不灭的永生。郁达夫在《苏州烟雨记》中从目睹行旅中那些“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的迷失而发出了创造的宣言:“你们若欲上空旷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气,一则可以醒醒你们醉生梦死的头脑,二则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谢的青枝绿叶,豫藏一个来春再见之机,那么请你们跟了我来,Und ice。Ch Sohnucre Den Sack and wandere,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吃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
生命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自由,这便是创造的宗旨——1923年7月21日,由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的《创造日》创刊,这个为上海《中华新报》编的文艺副刊处处体现了创造精神,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说:“现在我们的创造工程开始了。我们打算接受些与天帝一样的新创造者,来继续我们的工作。”这创造的工作需要的是“纯粹的学理”,是“严正的言论”,是“唯真唯美”的精神,从政治经济到文学文艺,无不需要创造——“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属言的。”创造远离时局,远离政治,是因为创造只属于纯粹的批评和唯美的文学,“我们这一株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
但是正如站在三叉路口的中国一样,穿长衫和穿洋服,回归故乡和外出接受新学,都是殊途同归的,创造要远离时局远离政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乌托邦,所以和中国现实的矛盾一样,出刊101期、存在100天的“创造日”终于走向了它的“终刊”——11月2日正式停刊,郭沫若在停刊前两日的《创造日停刊布告》中认为,“创造日”是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但我们深恨没有力量可以使荒漠成为良田,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使他独立以至于永远;我们只好忍心,我们只好听他在荒漠中萎谢。”与郭沫若将停刊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力量局限不同,成仿吾在终刊当日发表的《终刊感言》中分析了终刊的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力量太弱了”,而是“不辨黑白的群众对我们的诬枉倒使我们每期作呕三日了”,一边是自身的不足,一边则是读者的原因——读者为什么会不辨黑白,又为什么会诬枉他们?成仿吾没有细细分析,但是从创造日的停刊来看,它似乎也没有走出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迷局,就像当时的民众,就像当时的文艺,就像当时的政治,但是“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的永生观让“创造”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一种不竭的动力:
我们的“创造日”虽只道一百余日的生涯,但我们相信在我们小部分的关系者心中,在我们小部分的爱读者心中,他如像种子中含的胎芽一样,他是依然活存,而且必有一日迸出地层,奋发参天的时侯。朋友哟!我们请暂抑着悲哀,同声唱他的薤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