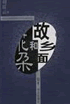 |
编号:C28·2050821·0723 |
| 作者:刘震云 | |
| 出版:华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8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118.00元 | |
| 页数:2183页 |
刘震云的长篇《故乡面和花朵》创作时间历八年之久,长达二百万言,他试图走一条新路,即注意开掘“深藏的和隐藏的现实”,用主要精力去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灵并进行深入开掘的现代精神长篇的新路。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型或板块组合的叙事结构,它的结构方法也不限于时空交错和线型,而似立体交叉等等,它建立在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的基础上,把传统和现代揉合在一起,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把故乡延津的“老庄”与整个世界的大舞台融合起来,采用某种物景描述,插进书信、电传、附录以及歌谣、俚曲等各种可以调动的叙述形式,组成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然而又井然有序的新的结构形式。
当卷一卷二是前言卷三是结局到了卷四才觉得要有一个正文为大家的回忆录作共同序言的时候,我还真是一诺干金,真的没有提成年之后的事只是拿着自己的11岁和1969年作为座标和风信鸟说了一下。
——《卷一·第一章 丽晶时代广场》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以及第四卷,整齐地摆放在自上而下的序列里,如果以一种阅读的方式被打开,一定存在着前和后的关系,最上面的第一卷,之后的第二卷,之后的第三卷,乃至最后的第四卷。可是,为什么第四卷的时间会被埋没在最底层?为什么前言和结局之后的附录是回到最前的1969年?那么,和页码和卷序相关的仅仅只是数字?但是时间也是数字,数字里出生,数字里成长,数字里变化,数字里死去,“但1969年和1967年之间的空白,到底靠什么来填补的呢?”同一个年份里还有什么样的空白?那个空白可以用骑行三十里的自行车弥补?可以用我和牛顺祥童年的过家家游戏覆盖?可以用11岁的变声和所有的革命、口号更替?
数字是标记,却早已经在自己设定的空白里消解了时间,所以第一卷第二卷可能不是前言,第三卷可能不是结局,而第四卷的回忆录却正是一个时间的起点——如果将最下面的第四卷抽出来,然后依次拿过第三卷、第二卷和第一卷,在反向的阅读中进入到一个顺序的时间里,那种“1969年和1969年的空白”就完全变成了一种虚构,变成了一种呓语,变成了可以颠覆时代的寓言。这无非是一个关于故乡的想象式叙述,回忆里的现实只有在身后的时间寓言里,或者才有启示,才是坐标。
从第一卷到第四卷的数字序列是一种关系,从第四卷到第一卷的时间寓言也是一种关系,关系的定义启示早在序言里就已经标明了:关系是名词或者是动词,关系分为正当关系和不正当关系,关系是可以改变的现实,关系是历史中佛、刘邦、阿斗和孔孟有关人的说法,关系是书籍里记载的传说,关系是“随处可见的成年朋友的朋友”,是“永不再来的童年朋友的游戏”,词语的关系、现实的关系、历史的关系、书本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构成了种种的可能,所以当同性关系、异性关系、灵生关系和生灵关系,在一个充满时间寓言的故事里出现的时候,它只代表着可能,空白里可能的填补,时间里可能的割裂,以及故乡里可能的颠覆。
不如直接跨入到现实之外、时间之外、空白之外的22世纪,那时候骑小毛驴变成了时髦,那时候露天Party里名流和闲杂没有区别,那时候“一头鸡毛”的发型在世界风行开来,而那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解放同性关系者,给他们提供家园。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无疑是一个矛盾关系的结合体,礼仪与廉耻,是为了维护一种秩序,而“孬”字指向的是道德缺陷,以及名模你孬妗、影帝瞎鹿,都在一种道德意义上被命名,所以那个丽晶时代广场也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讽刺,“战斗已经打响,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该你为难的时候到了。这段警句是这样的:身绣荷花的人,去接受身处粪坑人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场上的战斗,变成一种关系改变的宣言,这里没有“研究研究”,只有人生大问题,没有拖延不绝的历史和过去,只有革命性意义的现实,“同性关系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生难题,它牵涉到你是拒绝世界上一半人还是接纳这一半人的大事,你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怎么能说一句’研究研究‘就像解决世界上其它问题一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
| 刘震云:在第四卷里摸到历史和故乡 |
没有研究,只有决定,没有讨论,只有实施,没有历史,只有现实,所以即使表面的清高、表面的先锋,表面的现代,表面对世界和现实的不屑一顾,但是当时间变成了一个人的暮年,“你们不都以自己已经过期的先锋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了吗?”解构先锋,是为了返回现实,解构清高,是为了回归人性,“这是同性关系,是家园,是涉及到世界和人的根本问题”,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政治,也没有所谓的伦理,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对人类、男女的蔑视和不屑,通过一个环境布置,通过一个小小的专机,就对世界发出了宣言和提出了挑战。我为什么要搞同性关系呢?就是因为对你们的蔑视和不屑。那些还残存在这个世界和专机上的,黑暗和旮旯之中的异性关系,在我的摆设面前,一下就显出了他们的肤浅和可笑。”
可是这种被重新定义的关系里面,那种已经存在的关系,已经存在的家园又会向何处去?孬舅的宣言和行动指向人性,但是为什么自己却在另一种关系里?为什么自己和三国时代一样离政治很近?为什么自己要娶冯·大美眼?这是一地鸡毛的现实?还是革故鼎新的现实?离开旧有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对故乡的抛弃?那么在新型关系里,故乡又在何处,故乡到底何谓?“故乡是他家棚子里隔年的蜘蛛网,上边扯着几只干化的苍蝇、蚊子和蠓虫;网子是固定和陈年不变的,苍蝇、蚊子和蠓虫是偶尔撞上去的;棚子是不变的,人就像网上的苍蝇、蚊子和蠓虫一样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罢了;遗忘和忽略是大部分的,留在心中和历史上的记忆是偶然的——谁是当年结下这干网的大蜘蛛呢?……”白蚂蚁定义的故乡和昆虫式的生存有关,“故乡是什么?故乡就是我的母牛;母牛没有了,我哪里还有故乡呢?故乡是什么?故乡竟成了梦中的温柔富贵,所以我要背井离乡。”郭老三定义的故乡和动物有关,那么那些人呢?那些异性关系的人呢?他们在故乡的哪个地方?
故乡何谓,或者是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难题,而在故乡的变迁和定义的更改中,故乡早已经逃逸在时间之外了,也就是说,故乡被架空了,当故乡被架空的时候,历史也被架空了。为什么曹丞相曹成和袁主公袁哨从几千年前的三国以来,就成为了英雄?“正是因为当时不能搞同性关系,所有的男女都无事事,大家就要当英雄,就因为关系压抑相互在别的方面掐了起来,就打仗,就争分天下,就分崩离析,就一刀一枪,获得个封妻荫子。”性压抑,性关系不解放,所以产生了养猪业一样的政治,所以造就了争分天下的英雄,所以当时代被重新定义的时候,当关系被颠覆的时候,“故乡该重新安排秩序了。旧世界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兔死狐悲的声音,已经在原野上悲悲切切地响起了。”
旧世界是时间的一部分,新时代也是时间的一部分,千年之前的三国是时间的一部分,丽晶广场的露天Party上的解放宣言也变成时间的一部分,或者时间就是在英雄和英雄之间,同性和同性之间被重新书写的,英雄属于历史,鬼魂属于历史,在牛屋理论研讨会上,除了时间意义上的不同代表,还有空间意义的不同代表,从欧洲而来的呵丝·温布林、卡尔·莫勒丽、牛蝇·随人、横行·无道,从南美而来的巴尔·巴巴、基挺·米恩,都带着异域的特色,他们作为同性的代表,其实也是对于故乡的一次解构,“延津离我们越来越远,旧金山倒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就这么把他乡当成了故乡。同性关系者回到了故乡,我们却成了局外人。”是的,在故乡,同性大军像洪水一样涌到了我们家乡,在这种即将被解构的关系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孬舅的密令中,谋杀异己分子,重新保卫故乡,重新维护自己的权力。
“当然是谋杀。活不见血,死不见尸。”打卖场,这个最具故乡意义的地理标志,变成了一个屠杀的地方,“故乡从此就开始又一轮的混浊和混沌的循环。”历史是我们的历史,而“他们”和“她们”却不再是我们村里的人,“什么同性关系,什么回故乡,什么标准,这不是到了我们家门口了吗?到口的肉,不吃就是罪过。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抢粥吃是为了满足食欲,强暴欧洲的同性女人是为了另一种欲望,用欲望重新找到故乡情结,是一次捍卫,却也是一种破坏。墓挺·米恩和袁哨、瞎鹿和巴尔·巴巴、莫勒丽和女兔唇,正是这种对立式的关系,让故乡重新回到了序列体系里,而这种斗争是一种特权,也是对于人性关系的另一种颠覆,仿佛是回归历史,“当历史真的要坍塌下来的时候又靠谁呢?我不说话,让他们说,那是我相信,历史终于会给我一个说话和澄清历史的机会。”也仿佛是回归故乡,“一到这种时候,我们就真的回到故乡了。原来以为故乡只是一个地点,现在我们才知道,更重要的还是时间呀。一个地点对于你的吸引力,还是不如你永远难以忘怀的时间段呀。”
故乡的时间,在历史中经历过谜语时代,经历过披头士时代,谜语是一种迷惘,披头士是一种结合,“本来故乡已经是一盘散沙和各自为政了,现在一场披头士革命,又把大家万众一心地集合到了一起。”可是谜语和披头士也是一种虚幻,可是真实的故乡在哪里?当小刘儿的姥娘去世的时候,真实的故乡便在真实的时间里变得可怕:那是1995年3月24日8时25分,具体到分的时间,是一个人的死亡,而翻过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历史,就是一个魂灵,所以从同性关系到异性关系,最后却回到了和灵生关系:和生命有关,和死亡有关,和收割的季节有关,和成熟的麦子有关,和麦花、枣花和啤酒花的香味有关。当历史突然凸显在时间的意义上的时候,那早已经到来的22世纪是不是就是一次丽晶广场上的虚构?
1995年3月24是一个“结局”,掠过了已经走过去的历史,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场胡宁之役战场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敌人,所以也从历史的叙述中脱离出来,没有任何的文字,它只是一个背景。灵生关系开创的是一个理性时代,可以检视生命,可以理解死亡,可以看见故乡,所以就在1995年的故乡,历史是被一刀割断的,而现实走到了学术时代——象征着理性,“到底到了一个以学术和理性统治我们故乡的新时代了。”理性是什么,是灵生的关系,是真实的时间,是看见的自我:“直到临死我们才知道,我们经过异性关系、同性关系、生灵关系或是灵生关系的阶段,到达了学术和文明的新时代——原来这竟是一个自我的时代。我们从异性出发,现在以自我和上吊结束。”自己的生,自己的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头颅,“过去的情感时代我们把一切都贡献给了别人,只有到了学术和理性的时代,我们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而在这种自己照顾自己的时代,没有了同性,没有了异性,自己和自己结成的关系就变成了合体人,小刘儿、小小刘儿和小刘儿他爹,三个刘家的爷们儿和后代停留在单体的异性或同性,生灵或灵生,自我或骷髅的时代,小小刘儿叫爹爹,小刘儿的骷髅就高兴,小刘儿让他别怕,却仿佛是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异化自己。这是在故乡生存的理想?这是时间从历史走来真实的现实?无非也是一种虚构,“你们虽然表面上成了合体其实你们才是单体我们表面看是单体其实我们内心才是合体呢。你们用你们的合体也就是单体向我们接近,我们用我们的单体也就是合体来拒绝、限制和磨搓你们。”合体的历史,单体的现实,其实是分叉在两种不同的时间里,而在对小刘儿的营救中,这种所谓的合体无非是一个讽刺:小刘儿只是把门的五十多岁老头,而被营救的小刘儿不过是邻居而已。
包含着现实的历史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包含着死亡的生灵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包含着单体的合体看上去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一个虚构,就是一种幻觉,就是不存在的关系。而被说成整体的现实其实就是一种成人化的构想,而在经历了同性关系、异性关系、灵生关系和圣灵关系之后,经历了谜语时代、披头士时代、学术时代之后,故乡回到了1969年的童年,回到了1969年的11岁,回到了大家的回忆录。距离1995年的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三国的历史还有千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11岁的起点,在这个11岁的坐标里,故乡是不是就是存在的,就是真实的?
1969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可以接煤车,可以单独远行,可以到三十里坡;1969年,我看见了吕桂花,硕长的腰身、丰满的臀部、细长的腿,以及冬天的红棉袄、月蓝的裤子、女性的香味,都让我产生了震撼的觉醒;1969年,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1969年是墙壁上的口号,1969年是自由而又矛盾的面瓜投河而死;1969年是镇上捎回来的一块肉;1969年,老胖的三个妹妹因为贫穷被卖掉……1969年是11岁的我慢慢成长慢慢变声的年代,1969年是看见了女人觉醒了情欲的年代,1969年也是革命和口号取代一切的年代,1969年更是贫穷和死亡的年代。可是它一定要出现,一定会进入现实,一定会变成历史,即使荒谬,即使残酷,即使错误。
所以对于故乡来说,那个违背的诺言终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16岁的牛顺香出嫁,憨厚的牛文海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在你出嫁的时候,请记着戴上避孕环。”出嫁是一种仪式,却也是对于父权的解构,蠢蠢欲动的欲望会成长起来,会生娃,会延续后代,会改变秩序,所以那场违背诺言的集体行动直接变成了械斗:“成千上万的人,手里拿着日常劳动的工具——棍、棒、锹、权、铲、锨、铡、斧、犁、耧……”农具成为武器,村人成为战士,还有什么是对于1969年最真实的描述?避孕环是一个阴谋,取消了生育能力,取消了夫妻关系:“这时你将避孕环就不单单是放到你女儿身上了,而是放到了我们全体和我们村庄身上。”
械斗是为了利益,却破坏了关系,而最后的“换亲”,又以颠覆伦理的方式变成故乡新的传奇,“你开创了故乡一个新时代呢。”在这个时代里,女人的身体里藏着避孕环,故乡的庄稼被踏平,和谐的关系被“换亲”代替,而唯有11岁时的那个假扮夫妻的游戏里还有叫做故乡的归宿、叫做米面的食物、叫做花朵的欲望,“但1969年和1967年之间的空白,到底靠什么来填补的呢?”11岁会走向成年,11岁会完全变声,11岁会看见“村庄血流遍地的纪念日”。
从前言到结局,从第一卷到第四卷,从历史到现实,从数字到时间,也从22世纪到1969年,那段空白的插页里写着一个个传说:《水浒》第一章里是“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白石头的便是”,《三国演义》最后一章里,是“朕闻石头在边境与敌人相通,今果然矣!”而那《琵琶引》的诗歌里,是白石头又名白居易的对于历史不幸遭遇的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