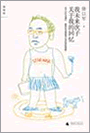 |
编号:C28·2120822·0906 |
| 作者:[台]骆以军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4月 | |
| 定价:36.00元 亚马逊25.90元 | |
| ISBN:9787549509331 | |
| 页数:265页 |
《西夏旅馆》之后,现在之后,骆以军以一个被虚构的父亲的名义出现:“父亲晚年的作品里,常出现一个像鬼魂一般挥之不去的人物形象:一个身体羸弱的少年。曾遭到背叛、伤害而变得多疑、残忍的主人翁们,在不同的情节场景和这个少年对话。”父亲是相对于少年而存在的,这是时间的序列,只不过提前到了回忆般的小说中,封面那个抽着烟、戴着眼镜、被小狗围着的简笔画人物是谁?一种意象?一个符号?“是完全未曾存在过的故事,还是另一种生活之可能?”关于回忆。关于遗忘,也关于追寻。父亲的次子,小说家的次子,是不是还有一个“我”的次子?在35篇未来时光的预言书中,故事只不过是时间序列中的一个点,一个被延伸出来的有关自己的错乱身世:“我信赖的时间术,在小说之外的,包括宽恕、透过第三者放话的真相对质、另一种翻转的生命视景,或经由无辜纯洁的下一代重新学习的爱的能力……这一切原本交给继续流动的时间。”副标题写着:关于记忆与遗忘、家族史与青春考古学的探险旅程。”
《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去年在马伦巴
在我的故事里,发生过一次的事便不会再一次发生。所以我把所有的虚构视为祝福,而非预言。
我以为骆以军是抽烟的,喜欢养狗,还戴一副眼镜,经常休闲式的打扮,T恤上还醒目地写着“STAR WAR”——不是WARS,没有复数,当然不是1977年的那部电影。从一个单词出发,从单数对于“历史记忆”的那个复数形式的否定,一切的否定便连锁反应般开始了:抽的是香烟吗?那只狗在吠叫却原来是玩具狗?或者这个戴着眼镜望着不远处的人是骆以军吗?认识论问题上已经无可挽回地偏向了一种误区,《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是“我”的故事?我就是那个叫“骆以军”的作者?或者说我有次子而且一定会有“关于我的回忆”?疑问接着疑问,否定连着否定,像是在“铺天盖地的他父亲的虚构迷宫里”触到了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我”一定是次子的父亲,这是一个权利谱系的最基本关系,未来、次子、回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结构,父亲在另一边,次子在这一边,如果一定要从关于“我”的归属出发,可以用一种仰视和观望的方式来描述,但和骆以军无关,和文本的作者无关。“我父亲继续写作,一天吸两包烟”,这是一个段落,写作、吸烟,继而是“得了忧郁症”,这样打开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我”的特性,但还不够生动性,还不够肉体性,架空一般的描述背后,可能也只是一个寓言,所谓“父亲”只是父权而已。所以在这本“关于记忆与遗忘、家族史与青春考古学的探秘旅程”完全剥离了对于父亲家族序列的历史考察,而充满了假定性,充满了不在现场的遥远感。父亲是谁?“往好处想你可以说父亲是个充满创意、冒险性格与行动爆发力的大男人”,而或者真正被定义的却可能是那个“无厘头而固执”人,而“我”作为父亲,真正打开具体而微的不是封面那抽着烟、带着小狗,用“STAR WAR”否定复数存在历史的那个人,而是那张作为书签、标准七寸素描相片里的那个窥见了秘密的“眼镜男”。
相片里的两个小孩,和两个大人,我、哥哥、父亲、母亲,前面的孩子睁着大大的眼睛,一半的好奇一般的木然,左侧的脸已经占据了大半,是我,而右侧是大哥,大哥的后面是“笑靥如花”的母亲,而父亲呢?在左侧的后面,大半的脸被“我”遮挡,只露出一双戴着眼镜的眼睛:“只有我的大头如梦如雾地遮据了照片左半边几乎全部的画面,父亲的脸只剩下被遮住大半剩下的一对眼睛,如此凶厉如此愤怒。”被遮挡的父亲其实看不出凶厉和愤怒,局部的表情或许是一次预谋的计划,因为“那时我太小了”,或者是在用这样具体的相片反而可以解构真实,解构父系的一种权威,故意呈现着真实、具体的影像,而其实这只是关于家族回忆中“模糊的记忆”:“那是大瘟疫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模糊记忆,那张相片我至今还收存着。”
固定在真实的相片里,放大的“我”和被遮据的父亲,如此细究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否定权威?否定既有的秩序?或者否定历史的“真实先例”?那篇意大利小说家《砍头》的小说,对于权威完全是一种形而上的扼杀:“所谓权威就是其人拥有在不久将来把你送上断头台的权利。”命运早已经被决定,只是在一种形式意义上具备了“权力之位置”,而实际上只是一个游戏,一个对于“大刺杀”时期选举仪式的彻底否定,而这种被称为“假刺杀”的仪式最后一定是为了伪造一个历史上的“真实先例”,告诉你,早就在那里发生了,但是“必然会发生”和“真正发生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它虚构了历史图景,假设了历史事件,说到底是相信“永劫回归”或“文学起源论”的笨蛋而已,“那个人”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假设。
父亲呢?被遮据的相片里是不是也是一种对于“真实先例”的否定,具体而微,却不返回现实,就像母亲曾经说过的那个“我不解其意的咒语”:“像《去年在马伦巴》。”《去年在马伦巴》,一部电影,关于记忆和谎言,关于确认和否定,关于爱的虚无,关于不存在的存在感,一年前,或者更远的时间里,其实都是为了获得“真实先例”,但即使在谎言中,你也会找到那些证据找到存在的理由。一部电影的寓意,一段咒语,母亲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却使我“不解其意”?“去年在马伦巴”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父亲的不存在的存在感,其结果是创造一个走向另一世界的“任意门”:
任意门,我突然领悟我疑惑之处在哪,就是那成千上万扇集中簇挤在一工厂景观,而打开门后可以任意通往那个被全球化城市印象简约成一幅一幅风景明信片的“世界各地”的,任意门。
这是父亲旧稿里的一段话,是问题也是答案,是原因也是结果,每一扇门都在打开,却通向不同的地方,只有这一边的门,“它们被集中并置在同一个空间”。通向那边通向陌生的世界,任意门是去年的“马伦巴”,来过又不在那里,而在“我”的父亲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通往过去,通往未来,通往现在的入口,当“时光迢迢地成为一种象征”,父亲就成为一个制造任意门的最大原因,他一定存在“我”的记忆中,却开始变形,开始隐匿,开始用“真实先例”来返回现实,任意门被打开,父亲在这头,眼镜后面“如此凶厉如此愤怒”的表情终于变成了一本虚构的书。
虚构而为虚幻,作为一种任意门的进入方式,贯穿在“我”作为次子的成长过程中,那个钞票“加倍”的魔术最终变成了“我”的出生事件,“母亲说,他们那趟旅行结束回国后不久,她便怀上了我。”我的出生带上了明显的虚构色彩,仿佛是一次灵验的幻术,把一个生命按进了肉体里,“所以它活着……不仅如此,它蜕化成成虫了……”这是蜻蜓的出生过程,不经意地生命孕育。但这毕竟只是一个魔术般的开始和结局,面对魔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被取消,“其实包括我在内,你们,和我这一代的,都是无经验之人。”被取消意义,就会是一个“无经验之人”,无经验也就没有历史,没有存在,是“去年在马伦巴”的脆弱证据,而父亲遭遇到这种魔术般的结局,已经成为一个“经验匮乏者”,所以他的虚构就是在书写“经验匮乏者的笔记”,“次子”当然是被创造出来被书写和虚构,也成为弥补“无经验”的那扇“任意门”。
“次子”,完全变成了一种臆造,那漂亮女人说:“因为我憎恶人类的小孩。”没有活的生灵是不是也是一种“经验匮乏者”,而父亲对于次子的创造越来越接近虚妄,“我记忆里曾经载存下的画面,原来我父亲在许久以前便在他的小说里描述过了。”小说里的一种存在,一扇任意门,打开,便是关于不存在未来的回忆,那篇论文里考据出的东西也都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小说中所有属于‘我’这个人的记忆,全是我父亲编织拟造的。”所以作为一种可怕的结局是,我是不存在的,周遭所有的人,都用“他曾这么说过”、“这是他告诉过我的”或“像这类的事他肯定是这样认为”这样的叙述方式来描述他的世界,”我发现父亲并不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一个父权序列的”去年在去年在马伦巴“?而我在”次子“这个属性外,到底以什么方式呈现?是“陆沉的亚特兰提斯”?还是“佛罗伦萨之境”?又或者只是“一个人独自站在城市高楼顶端的故事了”?那个在父亲万年作品中出现的“身体羸弱的少年”是我,还是父亲自己?或者只是不存在的“真实先例”,记忆也不存在了,就只剩下了虚妄的未来:“那个男孩,跑到了未来的时空,也就是二〇四六年的未来城市。”
“我”在另一个任意门,看到“父亲如何像一栋瞬间变作烟尘、轮廓尽失,将自己炸毁的大楼”。所以父亲也变成了一种虚构,一种不存在的存在,同样被“去年在马伦巴”的咒语里活着,刻意埋下的重组线索其实就是一次对于记忆和遗忘的试验,所以从反过来看,是我成全了父亲,是我创造了一个父亲的符号,“可能是我拟造了我父亲,而非他拟造了我。”拟造的背后是一个家族般的痛苦,是死而复生的生活,其实,在”父亲“这个沉重的字眼后面,承载着更多有关“人类”、“文明”、“历史”、“未来”这些像空荡荡的巨大教堂的词,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家族有关的“神秘符”。但是它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不管是“我“拟造了父亲,还是他拟造了“我”都变成了返回文明的一种考古探险,而结局并不是有所收获的,甚至那个所建造的虚构世界,只是一个被简约的世界,一个不存在的“马伦巴”:“也许作为父亲所说‘文明之隳坏’最精准之隐喻,不是那座如今已不存在的机场,而是拿在我和大哥手中,那罐无法穿透时间延续意志的,一个异乡死者的精液。”
所以在这个小说的版本里读不到那些肮脏、龌龊以及色情的叙述,“铺天盖地的他父亲的虚构迷宫”早在骆以军的《西夏旅馆》里就不断地出现,那个叫做“外省”的地方一直存在,无法认同的陌生感已经将“父亲”逼近了“一个最隐秘、色情、变态但高度文明的乌托邦”,那也是关于父亲的寓言,进入了真正的“内心底层”,“就是在那儿,我父亲将我遗弃了。”那个图尼克其实也是遥远的“我”,未来次子,不是那只“迦陵频伽鸟”,也不是恐惧身体一部分的“人面疮”,而如果一切取消了父亲的意义,取消了家族史,取消了记忆和遗忘,那么无父之人就会在没有未来的地方出现:“因为无父才得以让创造力任意窜走颠倒梦境。因为无父才得以随意下载各种盗版他人之梦境以拼装自自己之身世。因为无父才能自由进出道德承受极限边界外的禁区。”
而实际上,无父之人亦是“无经验之人”,外省之人,是在那间“西夏旅馆”里开始“探险旅程”的他者,而在未来次子的回忆里,“西夏旅馆”就是那通向另一世界的“任意门”:“他离开我们前的那整整十年,他埋首苦研西夏史,他从头学起那些活像汉字洒了生发水的西夏文字,然后用那些无人能识的西夏字进行他那部传说中两百万的西夏王朝魔幻小说:《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
如烟消逝的帝国,也是一个家族的全部历史,“是一趟漫长的车程”,坐在上面的是写作、吸烟、患有抑郁症的父亲,是内八瘸子、练软骨功、穿着“飞天鞋”的次子,而那些内心里的有关家族的乌托邦最终也只是一个“羞耻的倔强”,是一个“眼瞎目盲之强光的家族仪式”,最终敌不过一个平凡人物的真实叙述:“不干活体内细胞因肥胖、烟瘾、酒精或年轻时荒唐行径之摧残而早在四十岁以前便老化焦枯,内脏囊袋中浸满了腐蚀性毒汁酸液,所以他一张嘴便让入昏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