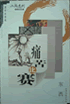|
编号:C28·2110116·0793 |
| 作者:东西 | |
| 出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 |
| 版本:2005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253页 |
应该是很久远的事了,2003年的小说,2004年变成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我都没有看过,我想我是忘掉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那里的世界又被我遗忘的地方,而当我在一个新年初临的时候注视的时候,是方力钧的光头和烟,是“Voices in the Light”,是“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简介上说:《耳光响亮》以一个普通平民家庭的故事,写出了六十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仪式,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启蒙过程进行了真实再现。从某程度上讲,它就是这一代人的心灵史。本书聚汇了那些破碎的、不健全的心灵,他们既被别人伤害,同时又伤害着别人,甚至还不时地相互伤害。一切既定的传统伦理关系在这里都受到了巨大的怀疑和肢解。书的第一句:“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
当当网上7.5折优惠,对于东西的作品,或者并不能用这样的价格指数来衡量,但毕竟是有些久远的东西,2003年就出版了《耳光响亮》,当年还拍摄了电视剧,只是拙劣而娱乐地改成了《响亮》,但对于我来说,东西的作品还是陌生的,这位广西作家似乎越来越走向制度化生存,但在无限接近中却总是擦肩而过,《耳光响亮》成为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响亮》中的蒋勤勤因出演牛红梅而获得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入围,或者提名,都在走近体制,“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在目光“愈拉愈长”的体制内成长中,似乎我们听到了那记响亮的耳光。我是因为看到封面上方力钧的绘画才买下的,男人和女人,橘红色的欲望在升腾,却被他们陌生的目光所阻挡,光头,烟夹在手上,仿佛世界就这样凝固了,那种“最向往的生活”已经不能随目光“愈拉愈长”,东西说:“他的画我很喜欢,画中夸张、荒诞、泪水之后的微笑,苦难却又不失理想,其中蕴藏的复杂性与我作品的精神气质相似。”但那眼神不像是被扇过响亮耳光的眼神,冷漠,麻木,没有方向,很多认都在问,这样一个一代人的悲欢故事中,到底谁扇了耳光,或者说,谁被扇了耳光。
父亲牛卫国、母亲何碧雪、姐姐牛红梅、哥哥牛青松、以及叙述者“我”牛柏翠,一家五口,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张开,扇将下去,一个时代便出现了红色的手印。或者这样的简单的数字化寓言正是东西在作品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隐喻,一代人的成长仪式,一代人的心灵史,里面有着时代给我们留下的记忆碎片,但是对于我们所要批判的或许不仅仅是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在一系列荒诞中我们其实在寻找黑色幽默背后的那记响亮耳光。其实,那耳光就从叙述者档案开始,最喜欢的书:《毛泽东选集》;最喜欢的歌:《红旗下的蛋》。
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这两种文本阅读会让我们毫无悬念的进入那个颠倒的历史现实,“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个“普鲁斯特”回忆录式的开头方式,就是为了表明一个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而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个体陷落在巨大的陷阱中,讽刺也好,警世也好,生命的时光无法逃脱,1976年的记忆,毛泽东逝世,这样的回忆直接把小说带向寓言的起点,那就是父权的丧失,作为那个时代政治信仰和民众记忆最强烈的记忆,毛泽东的辞世就是把一个父权社会带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权威丧失了,没有了方向,也就没有了信仰。
我睡在20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人的蝙蝠,在蚊帐顶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朦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飞出来。
把这个故事设置成这样一个起点,后面的个体荒诞便顺理成章,空空荡荡的世界突然出现在面前,于是父亲牛正国毫无预兆的失踪了,只留下一封遗书,又一个父权消失了。国家父权和家庭父权的双重消失,让这个家庭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中,所有的秩序似乎都在瓦解,也都在像一种真实状态靠拢。在追悼毛主席的现场,出现了一个一丝不挂,精神分裂的杨美,杨美用作为国家舆论工具的报纸遮住了脸,她的这一举动似乎在消解时代的权威,而她被拒绝进入,小孩们则围住杨美喊:聋子、哑巴、坏蛋、神经病。而在这样一个丧失最起码尊重的时刻,“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他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开追悼会。”在别人看来,她没有尊严,更没有任何话语权,但是即使在一个被界定为神经病的病人身上,也有着不能消除的对父权的盲目崇拜。
当父权瓦解的时候,正像杨美一样,是需要寻找另一种父权带代替丧失的父权,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对父权的寻找逐渐成为变本加厉的行为,一个是牛红梅,她和初恋情人冯奇才约会被发现,然后被流氓宁门牙糟蹋,怀孕。但是对牛红梅来说,这是一个计划外的怀孕,宁门牙不可能成为孩子的父亲,父权的丧失又一次出现,牛红梅为了给孩子找一个爸爸,不惜向长相丑陋的邮递员曹辉求婚,竟然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她做了手术。在认识杨春光之后又怀孕,但是在杨春光背叛的计划面前,牛红梅再一次流产,最后在刘小奇按摩店里,再次被强奸,但是昏睡过去的牛红梅一无所知,直到自己被检查出再次怀孕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牛红梅三次怀孕,却三次在孩子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被推向一个悲剧的高潮,这样的隐喻对于作品来说,无非是用残酷的手段表现没有父权下的无奈和痛苦。
另一个是金大印。和母亲何碧雪好上之后,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对自己成为一个爸爸的强烈渴望让他的人生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举动,金大印“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真心诚意地叫他一声爸爸。”于是他在抓小偷时,用小偷偷生的欲望满足他做父亲的渴望,他把那些叫他爸爸的小偷放掉,然后,内心充满着“如果是放了小偷,他会格外兴奋和自豪,会不停地笑着说他叫我爸爸,哈哈,他叫我爸爸了。”在这样扭曲的人性需求下,金大印似乎一直在人生的边缘,他希望用父权来树立自己的地位,但是遭领导非议等一系列不公之后,他却用一种英雄的存世方式来挽救自己的道德信仰,他按照记者马艳三个信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照顾邢大娘,救一名儿童,直至成为新闻人物,到处作报告演讲,金大印不是真正的英雄,他在虚拟的英雄光辉下寻找自己的父权地位,而这一切在那个时代只能是一场闹剧。
更啼笑皆非的闹剧还不止这些,当最后“我”需要30万元作为拍电视剧的资金时,金大印答应出资,但是条件是和牛红梅结婚,目的也只有一个,生孩子。当最后和牛红梅签订结婚合同书的时候,那种荒诞的文本后面,其实是一个乱伦生活的开始,而倡议者竟然是金大印的相好,“我”和牛红梅的母亲,在这里,仿佛人性中那种扭曲的东西被放大到极致,而他们的出发点无非是为了换回失去的父权。最讽刺意味的是,在数次流产、堕胎中,牛红梅其实已经丧失了生育功能,在一纸合同中,所谓建立父权秩序的努力变成一个十足的讽刺。而更为讽刺的是,最后父亲牛正国在越南芒果街被找到,而此时,父亲已经没有了记忆,从失踪的父亲变成失忆的父亲,他的存在只是父权社会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
从毛的逝世作为起点,从牛红梅的“不知谁是父亲”的质疑到金大印“他们叫我爸爸”的虚荣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父权社会的人性悲歌,从信仰膜拜到道德困境,一代人并不能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撑,在分崩离析的现实面前,这些所谓的追求显得可笑可叹,我们仿佛听到那岔开手指突袭而来的耳光,沉闷地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