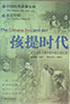 |
编号:W71·2021220·0656 |
| 作者:(美)何德兰、布朗士 | |
| 出版:群言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8.00元 | |
| 页数:322页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和英国传教士坎贝尔·布朗士在中国生活期间,目睹了那个时代中国特殊的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儿童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其实,在这两个传教士眼中,中国儿童的孩提时代仍然有他们的快乐,有他们爱玩的游戏,但是这样的生活到底有多少历史的真实?
如果我的工作能让天涯相隔的人们从中看到亲切、博爱和友善,那么,这本小书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中国的男孩与女孩·自序》
天涯相隔,便是东方和西方的距离,1909年,当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在《中国的男孩与女孩》的自序中写下这句话,他其实在这中国生活了21年,1888年来华,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对于何德兰来说,通向古老东方大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只不过曾经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大门是不是真的能为西方人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提供一种可兹了解的样本?
“在中国紧闭的国门被打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为西方人所了解之前,中国儿童的生活不可能在西方得到全面的研究。”这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当全面了解和研究无法达到,却也可以从一个小窗口管窥,比如孩子们嬉戏玩乐的大街,就是何德兰观察的一个立足点,比如从会讲童话故事、会唱儿歌的“鹅妈妈”那里听到一些儿歌、故事和游戏,也会丰富对中国儿童生活的了解,即使是片段的,偶然的,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通道,而何德兰把介绍中国儿童的生活看成是自己的“工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隐藏了自己传教士的身份。
其实,他于1909年写成的《中国的男孩与女孩》一书,就是隐去了自己的身份,而专注于细心观察儿童生活,为的是让美国人甚至欧洲人能够看到“亲切、博爱和友善”的中国孩子形象。从这一点来说,何德兰的记述具有客观性,也为真实展现中国人的特殊群体生活提供了一份资料——在书中有很多当时中国人的历史镜头,何德兰就是用西方的“洋机器”将他们拍摄下来,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合影,还是孩子们荡秋千玩游戏,都保留了百年前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图像的保存是一个方面,而何德兰更注重文字世界的记叙,一方面他不仅仅是一个对于所见所谓进行记录的被动者,而是以“工作”的姿态直面儿童生活,主动出击,特别是在收集儿歌、游戏、玩具上,非常用心。为了得到保姆口中的那些儿歌,他答应给“殷太太”每首歌500个铜钱,像《小老鼠,上灯台》这种耳熟能详的歌都收录进来,“我不在乎歌的好坏,只求越多越好。”另外,他从赶驴人那里得到一些儿歌,从史密斯博士一本里得到山东地区的300多首儿歌,自己的朋友切尔芬也送给他一些儿歌。如此,从多个渠道得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儿歌,最后整理出版了《中国儿歌集》,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儿歌。
收集并整理,其实是两步,对于何德兰来说,其中既有一个选择问题,他认为,采集到的儿歌“不至于引起人们的反感”,也有一个翻译问题,“如何把这些儿歌翻译得既有韵律,又富于节奏,同时还朗朗上口。”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整理,最后集结出版的儿歌集代表了中国儿歌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其中“饱含着对儿童诚挚而温柔的情感”,以及一些教育意义,比如那首“七岁我就没了娘,就像失水的花儿枯又黄。爹爹娶后娘,生了小弟把我忘。小弟吃肉我吃糠,叫声“亲娘”好心伤”,何德兰就认为:“这样的儿歌欠确实会培养起孩子们的怜饲心和同情心,使他们体贴和善待苦难中的人们。”
此外,在记录“男孩子们的游戏”时,他有意去寻找熟悉各种游戏的孩子,那个叫祁的男孩就告诉了他“跑马城”“盲人”“转肉轮”“掷石锁”“剥蛇皮”等游戏,并且和其他孩子一起在何德兰面前玩起了游戏,也正是在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游玩中,何德兰认真记录下来并拍摄了照片,而且还从游戏的组织、实施和趣味性上认识了中国游戏,他认为,“中国孩子们的游戏尤其有趣,这是一座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宝藏。”同时,通过他依然认为祁这个孩子具有一种“领导地位”,从而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小孩是“真正的民主派”,“中国人从孩童时代起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为大众服务的真正的民主理念。”
这似乎有点片面甚至偏颇,就像他从儿童玩具里观察认为,“亚洲没有产生任何科学,更没有达到任何程度的完善。”这似乎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优越感,因为,他看到很多玩具只是贫苦的家庭妇女制造的,而且都是简单、粗糙的手工玩具,但是他也对此抱有宽容态度,提醒欧美人不能自高自大,不能嘲笑亚洲人。从何德兰对于儿童生活的“工作”态度来说,他的确是十分用心的,男孩的游戏让祁来介绍,女孩的游戏则由一个“街头的小流浪儿”来演示,所以光在北京,他就收集到了75种不同的游戏。而在儿童玩具上,他从“辛先生”那里知道了布娃娃、泥人、拨浪鼓、陀螺等游戏,而一名中国官员则将《十五个魔块》这本书带给了何德兰,正是在这本书里他了解到类似七巧板的智力游戏,而且这些拼图和中国古诗歌结合起来,“囊萤”的故事、李白捞月、张骞考察黄河源头、陶渊明采菊等,从一个侧面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另外,少儿的娱乐表演,他则是从工匠尹实那里了解了木偶,也知道了周穆王的故事,并和欧美的“潘趣和朱迪”相比较,也提出了为什么这两个木偶表演会如此相似,“甚至连操纵木偶者的声调都没多大区别”,没有相关成文的记载,《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没有任何提及,所以他认为这可能隐含着一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口头史”:“我们可以想见,即使没有成文的东西,也至少会有口头的交流,使他和其他意利商人或旅行家把木偶戏传到欧洲去。”
或者是一种假设,或者是一种猜想,但是从何德兰对于儿歌、玩具、游戏、故事的关注程度,对于各种传说的疑问,以及“工作”的主动性和认真态度,的确为百年前的中国儿童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就像儿童本身一样,他的叙述笔法让人感到亲切、友善和博爱,中西方之间隔阂已久,他就是想通过这一份独特的工作展示中国的家庭生活,并使得西方人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消除隔阂感,“细心观察各种情形,就会发现中国儿童游戏和娱乐的方式是很多的,并且同其他国家的儿童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玩的许多玩具与西方的儿童玩具惊人地相似。”
当然,另一位传教士坎贝尔·布朗士来到中国,写下《中国儿童》一书,其目的也是让西方了解中国,在1909年作的序言中,他以写给西方孩子的口吻说:“在很远很远的中国,在那儿的群山中,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叫‘孩儿谷’。要是我有飞毯的话,我一定带你们去探访这个奇妙的地方。”中国孩子生活在“孩儿谷”,具有神秘的童话特色,也反衬出和成人生活不同,孩子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天真有趣充满活力的,“就像你走在这条小道上,满目都是荒山秃冷,突然间却发现了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长者对孩子们无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爱,就像这迷人的花园里盛开的鲜花。”所以,布朗士就是为了打开那个仙境之门,让自己扮演“山神”的角色,让他们编织飞毯,然后“带你们到要遥远的中国”,进入这个迷人的“孩儿谷”。
所以布朗士的初期目的更多是“揭秘”,就像那些讲给中国孩子听的故事一样,里面有着一种不为人知的“中国模式”:中国人从西方穿过中亚,然后定居在陕西省;最初在蛮族的包围中,是个幼小的王国;后来不是通过武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扩大领土,最后成为了中华帝国……其中有很多对历史的无知,有很多对于中国的误解,而这也使得对于中国的探究变得越来越强烈,也正是这个原因,布朗士想要揭开那个“看不见的顶”,让中国显露出来。
中国儿童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像何德兰一样,他对中国儿童的相关礼俗、游戏生活、儿歌故事等方面力图展现中国儿童的生活,但是和何德兰原生态的记录不同,布朗士似乎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角度,从家庭、教育、宗教、忠诚和贫困生活等方面记述了中国儿童的现状,也得出了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在中国,男孩子和女孩子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他发现,“中国人把孩子念书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觉得,“忠诚是我们敬仰的另一种优良品质,也是中国人经常教育孩子的内容。”他也观察到,“赤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饥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孩子们往往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必须开始工作了。”可以说,布朗士更多关注于中国儿童的群体现实和命运,那些儿歌、游戏和故事,似乎只是为他揭秘中国的一种辅助说明。
而其实,向西方儿童介绍遥远东方的儿童生活,只是他写作此书的一个目的,作为传教士,他不像何德兰一样将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反而时刻凸显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每一章节中,他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接近上帝、信仰基督的作用,也就是说,他的落脚点是为了传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儿童》更像是一本职业著作。比如,他从“中国婴儿”出生给家里带来乐趣,他更认为当孩子大了知道了“主”基督然后孩子告诉父母,那么,“家里就会增添新的快乐。”比如,他说中国城里的家庭有很多约束和规矩,但是只要信了《福音书》,那么不论男女,不论这家那家,都是平等的,而且信奉上帝之后,“无论别人怎么白眼相向、恶语相辱,都不能动摇这些新皈依者的信仰。”比如,他认为孩子在学校里接受《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等经典之外,还应该学习“福音”,“传教士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建起学校。许多孩子由此知道了上帝之道,并爱上了‘主’。”
有一些说教,有一些夸大,甚至有些杜撰,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信仰天主教的家庭毕竟不多,但是他却在书中说:“中国的孩子们平常也读一些圣经故事,例如约瑟、撒母耳、约拿单和施洗者约翰等人的事迹。”实际上,布朗士行文中有非常强烈的传道色彩,为了能更大范围传播基督教,他甚至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放大,比如他列举了很多的封建迷信,而其中有很多是风俗,他把所有的都归结为“迷信”,目的只有一个:“中国人对看不见的世界的恒常感受,对冒犯不可见的神灵的畏惧,应该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做到经常把看不见的神记在心中,并且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冒犯我们敬爱的、无所不察的在天之父,就像中国人不去冒犯神灵一样呢?”而在“宗教”一节中,他介绍了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但是他很直接指出,儒教和佛教有致命的错误,因为它们都没有引导和教育中国人去认识一个有人格的神,一个唯一的真神,“佛教让人们自己苦苦挣扎,没有向他们指出,谁能拯救他们于罪孽之中。”相反,有人信了天主教,于是,“在侍奉神的过程中获得了安宁和愉悦。”
为了传道,布朗士不惜将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视为对立面的存在,有些符合当时的国情,比如中国人吸食鸦片导致痛苦,有些可怜的女孩卖身为奴,所以他用“孩子们的哭”来证明诡异主的种种好处,一个叫凤子的姑娘,父亲有抽鸦片的恶心,为此遭遇了不少罪,有一次她看到了朋友手上的福音书,拿来一读,便发现了另一个光明世界,“在这之前,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掉入泥沼的人,渐往下沉,泥就要盖过我的脖子了。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人及时赶来救了我,奋力把我拉了出来。我梦想着又重新回到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念书写字。我隐隐觉得朋友们的这次到来预示着一切有了转机,上帝即将为我打开幸福之门。事实证明我想得没有错,‘主’的力量果然神奇无边。”同样是不幸遭遇的是耀儿和乌妹,耀儿的父亲总是赌博,为此他也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当他在学校里学习了福音书知道了耶稣之后,发生了巨大转变;乌妹则遭遇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死了乌妹也病了,但是她看到了福音书,于是在众人的祈祷中,她也向上帝表达自己的皈依之心,““谢谢你,上帝,你把独生子赐给了世人。我这个有罪之人,我相信你,希望你会让我获得永生。”最后耀儿和乌妹虽然都去世了,但是他们都去了乐土,去了“爱与永生之乡”,而从此之后,耀儿的父亲得到启示,开始帮助那些病人,并成为了教堂的长老,向更多人传道。
他们都是“布道的孩子”,而在这个意义上,布朗士描写的“中国儿童”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从中得到启示,成为“布道的孩子”,从而让中国充满希望,“后来,我们的主耶稣来了,中国开始苏醒了。”中国像那些生病的孩子一样,笼罩在魔咒中,偶像崇拜,拜金主义和恶习使人们远离了天国和主,所以,要让中国苏醒,就必须让爱传播出去,而在布朗士看来,主就是“孩子王”:“中国的孩子们学会了爱耶稣,这就是耶稣是孩子王的明证,他亲吻他们,把他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如果你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耀儿和乌妹的故事,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召唤他们回家时,他们愿意追随他。”
孩子的身上有亲切、博爱和友善的特点,所以自然和上帝之爱契合,所以他们都是“布道的孩子”,所以他们都可以走向“孩子王”——当布朗士的《中国儿童》变成一本启示录,一本传道书,那个神秘的“孩儿谷”其实也无非是通往天国的一条路,所以在如此强烈的目的论框架下,20世纪初的中国孩子生活或者也变成了布朗士的一种臆想,而他似乎也没有悬念地成为山神,打开了属于自己的仙境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