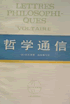|
编号:B36·2220121·1811 |
| 作者:【法】伏尔泰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91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68.00元当当29.90元 | |
| ISBN:9787100008204 | |
| 页数:745页 |
《哲学辞典》于1764年匿名出版,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代表作之一。原书贯穿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理性主义信条,对当时法国政治、社会和宗教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批判,因而遭到专制当局的查禁。中译本选译了主要条目100条,反映了作者的自然神论和经验论的哲学思想,并突出了作者对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的揭露和批判。 本书主要特点有二:首先是突出地反对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反对宗教狂热带来的愚昧迷信与迫害无辜;其次是强调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认为只有这种一切从合理的理性出发的思想意识才能为人类带来一线曙光。阅读这本书,从作者伏尔泰的思考问题时注意从合理的理性出发,不囿于一切固有的成见、探索真理、敢于面对现实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中吸取教益,对于我们认识现实,寻求真得,采取合理行动是有裨益的。
《哲学辞典》:我没有参与上帝的事务
我不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人类却又把人类淹死,而又用一个更坏的人类来替换。
——《世界洪水》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旧约·创世纪》里这样说。这是上帝毁灭人类的记载,这是人类之恶的后果,但是这个在希伯来圣书里叙述过的洪水泛滥真的能让人相信吗?或者它真的发生过吗?词条“世界洪水”中,伏尔泰把这一叙说看成是“一桩奇迹”,而且是“双重奇迹”,它所显示的是“各个星球主宰权能的最大奇迹”。
奇迹之发生,奇迹之创造,是因为有人类的主宰存在,是因为人类的主宰具有控制的权能,所以奇迹的第一层含义指向了上帝,是上帝宣布使用洪水,把作恶的人类包括一切有血肉有气息的生物毁灭;但是上帝制造这一奇迹之前已经有了更早的奇迹,那就是那些人类,那些作恶的人类,甚至有血肉有气息的人类,也都是上帝亲手创造的,这种造物的过程就是奇迹发生的过程:上帝创造人类是第一个奇迹,上帝淹死人类是第二个奇迹,所以伏尔泰把这两个奇迹看成是一种矛盾,他用讽刺的口气说:“我不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人类却又把人类淹死,而又用一个更坏的人类来替换。”
实际上对于所谓奇迹的定义,伏尔泰并不只是站在末世论的怀疑中,一方面上帝用洪水淹死人类的确是“上帝愿在圣书里过问的一切事无往不是奇迹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上帝创造的这个奇迹完全在物理常识之外的奇迹:海洋未必能搞出最高山巅十五吋或二十吋而不露出海底来,而且还不违反液体重量和平衡规律,“这显然就需要有一桩奇迹了。”另外,即使海面可以升高到书中提到的高度,根据物理规律,诺亚方舟也未能能够容纳得下世界种种动物和它们想要吃很长时间的那么多饲料,这不就是再一桩奇迹?展开来说,一次洪水泛滥淹没世界也是自然规律办不到的,伏尔泰证明如下:各大海洋覆盖了地球的一半,按照从海岸起到远离海岸的大洋深处计算,平均深度有五百尺;仅仅为了能够覆盖这五百尺的深度,不仅需要有五百尺深度的海洋可以“居住”在陆地上,而且还需要有另一个海洋能够覆盖现在的海洋,“否则重力规律和液体规律就会使地球负载的这一片五百尺深的新水泄下去了”;退一步讲,即使有高两万尺的大山,也需要五百尺深的海洋四十个彼此重叠起来,而每一重上层的海洋包括其下各重海洋,最上面一重的海洋的圆周面积就包括下面第一重海洋圆周面积的四十倍,所以要形成这样一层厚的水,唯一的奇迹就是:“就必得无中生有。”
这种无中生有的奇迹,伏尔泰在“洪水”词条中再次进行了阐释:海水可能陆续把陆地一块接一块地淹没,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按照历史上的计算,“海水在五百年间从埃格·莫尔特、弗莱儒、腊万纳这些大港口后退,留出约有两古里宽的旱地来。”这样的进度,需要二百二十五万年才能绕地球一周,接近地球轴心竖立起来与赤道吻合所需要的年月,而地球轴心的这种运动,也有人计算过,“这一运动要经过两百三十多万年这么一段长时间才能完成。”由此,伏尔泰明确指出,“这在物流学上说是不可能的事。”从《圣经》传说,到宗教故事,再到物理推理,伏尔泰无疑提供了关于洪水泛滥的不同视角,而物理学当然是对上帝奇迹的怀疑和否定。姑且不论伏尔泰在所谓的物理学推论是不是严谨,但就上帝制造的双重奇迹来说,的确是一个自我创造又自我毁灭的悖论,在这种悖论中,末世以及诺亚方舟这种最奇妙的事就变成了荒谬的事,甚至当上帝在双重奇迹中只是让更坏的人类来替换,洪水的故事其实和巴比伦塔的建造,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水变成血读过红海之类的故事一样,看起来说上帝施慧于他的子民,实际上变成了“人类心灵所无力探索的深渊”。
“这类奥秘是出于信仰而相信的,而信仰又在于相信理性所不相信的东西:这又是另一奇迹了。”无疑在伏尔泰编辑的《哲学辞典》里,“洪水泛滥”就是一个信仰和理性之间矛盾的体现,理性使得这一故事、这一奇迹不可能发生,信仰似乎站在理性的更高层次要使其变成可以相信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奇迹”——在运用奇迹这个词的时候,伏尔泰语气里是含有多么嘲笑的味道,嘲笑是怀疑,更是否定,那么对于启蒙运动主将的伏尔泰来说,发现这一奇迹的意义何在?身为自然神论者和崇尚自然法的哲学家来说,他又想在《哲学辞典》里建立怎样一种体系?坚守理性主义的伏尔泰在对信仰世界的悖论揭示中,主张的是怎样一种哲学思想?
以词条的方式编纂《哲学辞典》,伏尔泰当然不是以纯客观主义的立场进行关键词的注释,而是在注解中阐述其宗教信仰、理性哲学、善的伦理和自然法。伏尔泰的阐述明显体现了两种文风,一种是在对奇迹的揭示中的讽刺,另一种则是在对真理的探寻中透露的自信。从第一个词条《阿贝》的注释中就明显具有这双重的行文风格,阿贝,Abbe,法语是修道院院长,拉丁语和希腊语作Abbas,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作Abb,它们的词源来自希伯来语ab,而ab的意思就是“父亲”——当修道院长成为了“父亲”,一种人为的关于权威的书写就已经形成,于是伏尔泰说:“您可知道阿贝的原意就是父亲吗?您若是作了阿贝,可就为国效劳了;那一定能做出一个男子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儿来;国家又从您这儿多添一个会思维的生灵。这件事倒还有点儿神圣的意思在内哩。”这是一种讽刺;沿着这种命名学,当国王滥用职权,教会愤愤不平,“那些无衣无食真正贫苦的人都在阿贝先生门前向天呼冤。”穷人把修道院院长当成“父亲”,他们喊冤的背后是不是“父亲”的无为和欺骗?所以伏尔泰带着强烈的谴责口气说到:“先生们,你们有理,侵占世界吧;世界是属于霸占它的强者或能手的;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和愚昧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遗产,践踏我们,用我们的血汗来自肥。理性到来的日子,你们就发抖吧。”
修道院院长是“父亲”,穷人们还在他的面前喊冤,这是愚昧的表现,这当然也是理性的缺失。所以一方面伏尔泰在很多词条里注解了和宗教有关的内容,揭示了“父亲”权威体系中的荒谬,提出了对信仰甚至宗教狂热的质疑,嘲笑了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另一方面则是建立科学、理性、自然论和善的理念。在《亚伯拉罕》这一词条中,伏尔泰根据神迹的事迹,发出的疑问是:亚伯拉罕有一百三十五岁,怎么又只有七十五岁?亚伯拉罕的妻子为什么又是他的妹子?关于亚伯拉罕出生的年代为什么在注释家那里就有四十二种意见?“原文和注释使我们困惑不决,最好的办法就是信奉而不争论。”信奉而不争论的态度并不是伏尔泰对神迹的相信,而是因为圣灵本不在纪年学里,也和物理学、逻辑学无关,“我们既然什么也无从理解,也就只好唯命是听了。”唯命是从也不是一种盲目,而是因为在“视旧约为新约的蓝本”的所谓信仰世界里,“微弱的理性,也就可以缄默了。”
因为理性还没有到来,所以阿贝成为了喊冤的穷人们救赎的“父亲”,因为理性微弱而且缄默,所以只能信奉而不争论,只好唯命是听,就像亚伯拉罕故事本身,他服从上帝的命令,就是把上帝赐给他的孩子做牺牲献给上帝,“这是比喻人应该服从最高的主。”唯听是从的服从,就是一种父权体系,所以关于人类原罪的“亚当”故事在犹太的作品中找不到了,而且犹太教禁止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阅读《创世纪》第一章;所以最古老的天使学说在灵魂不朽的信仰中成为一种想象力和偏爱,“我们不大明确天使在哪里存身,是在空气里呢,在空中呢,还是在星球里?上帝却无意让我们知道。”所以注释“启示录”的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只为“找到符合各自利益的东西”;所以所谓的天赋人权,在很多国家成为法律杀人的证明,“这都是由于暴政、狂热信仰,甚至是由于差错和软弱而利用司法生杀予夺之权来犯下的案件。”
在这个父亲体系中,有“父亲”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权力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穷人,还有喊冤的穷人,还有在父亲面前喊冤的穷人,只有这些穷人会服从最高的主,会唯命是从,会让理性缄默——这是不是就会变成狂热信仰?有一个词条就是“宗教狂热”,伏尔泰明确指出,这是“一种错误意识构成的结果”,这种错误意识“使宗教为变幻莫测的想象和紊乱失常的情欲所奴役”,他分析说,宗教狂热是由于创立戒律的人的眼光过于狭窄,或者是人们逾越了所规定的的限度,所谓的律条只是未少数经过选择的人物制定,改变了它的初衷,所以最后宗教狂热变成了一种“宗教疯狂”,变成了可以传染的心灵疾病,“宗教狂热之于迷信,犹如狂暴之于感情激动,暴跳如雷之于愤怒。”在“疯狂”这一词条中,伏尔泰更是将其与理性对立起来,“疯狂就是思想和行为错综凌乱没有条理。”
从迷信到狂热再到疯狂,理智和理性当然不断被弱化直到最后缄默,以致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疾病,最终导致的是群体性的危害。那么无神论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狂热?无神论不承认上帝存在,这是在颠覆上帝颠覆权威颠覆“父亲”,无神论是怀疑论者,他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哲学观点,“无神论与狂热的信仰原是一对能够吞噬和分裂社会的怪物”,但是,伏尔泰认为,“无神论者在错误中还保持着理性使他不致胡作非为,而狂热的信仰却无休止地疯狂下去,这就更使他会为非作歹。”在这个方面无神论至少还保持着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在怀疑论中,迷失了方向,“他们不善于推理,不能理解创造、恶的根源和其他的难题,便求助于万物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假说。”所以伏尔泰并不主张无神论,而是需要一种上帝的存在,而这个上帝是自然论中的上帝,是宽容和爱的上帝,是不被狂热支配的上帝,“一个否认神的社会又怎么显得是不可能的呢?原来有人以为人类不受管束就永远不能在一块儿生活;以为法律对于秘密犯罪是无能为力的;以为需要一个上帝在这个世界或另外一个世界惩罚那些逍遥法外的坏蛋。”
这一观点在“偶像、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词条中得到了阐述,偶像一词从希腊语而来,意思是“图像”,是“侍奉”,是“崇拜”,“总之,通常是指行最高敬礼而言。总是含混不清。”当崇拜于一种偶像,就是把偶像当做神来供奉,就是命令人视之为神。进香上供,或者谈论灵迹,神变成了神像,变成了物,偶像崇拜其实远离了神,“我们既无神像又无庙宇之时,曾经大骂过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而自从我们以绘画和雕塑来荣耀我们那些真理就像他们以之荣耀他们的错误以来,我们仍旧坚持我们这种不公正之举。”所以伏尔泰在“上帝,诸神”中说:“我唯一的理性为我证实有那么一个匠人,他安排了世上的物质;但是我的理性却没有能力为我证实这位匠人创造了这个物质,为我证实他是从无中生有的。”在“性格”中说,“宗教、道德钳制着天性的力量,却不能把天性毁灭。酒徒在一所隐修院里,把每餐的苹果酒减到四两,便不会再醉了,但是他却老是爱酒。”
在对宗教的怀疑中,在对哲学的讽刺中,在对偶像崇拜的批评中,自然在何处,天性在何处,理性在何处,善在何处?在“灵魂”这一词条中,伏尔泰的论述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性主义下的灵魂论。他认为灵魂本来就是一个含义不清的名词,相当于拉丁文的“嘘气”,嘘气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常态,所以这是一种天性的证明。但是灵魂在哲学世界里变成了一种争论:它是物质还是精神?是不是在我们出生前就创造出来了?出生是灵魂是不是出自虚无?当我们死后灵魂是不是永生不灭?在伏尔泰看来,这些问题就像是盲人提出“光线是什么”一样的问题——在一些哲学家看来,灵魂是形而上的存在,但是这个形而上存在却在宗教之下,也就是在上帝之下,“天启必定胜过一切哲学”,但是在哲学家争论灵魂的时候,这个来源于“生命的本原”的嘘气却在自然中行动着——这就形成了三种体系,上帝在上面,它用天启带来了灵魂;自然在别处,它在灵魂的自我世界里创造着万物,而哲学意义的灵魂,为灵魂进行的争论,还有什么样的意义?伏尔泰说:“我既不了解创造,也不了解虚无,因为我没有参与上帝的事务,因为我完全不懂万物的本原。”
没有参与上帝的事物,是因为对于灵魂没有任何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对于无理性的哲学家进行了批评,“哲学什么也不报复;它心平气和地笑你们徒劳无益;它循循善诱地启发人们,你们却要使人愚钝无知,跟你们一样。”不参与上帝的事务,但参与了理性,参与了启蒙,参与了善,所以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就是不参与之后的参与,“你用脚走,用胃消化,用全身感觉,用脑袋思想。看看你唯一的理性是否给你足够的光辉,让你不必求助于超自然而得出结论认为你有一个灵魂呢?”在科学和理性的启蒙中,“古人的天”在伏尔泰看来,是人类外壳的绒毛,“我们现在还用天这个名词来称呼水蒸气,称呼地球跟月亮之间的空间;我们说升天,就像我们说太阳旋转一样,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太阳并不转;我们这儿对于月亮上的居民说来或许就是天,每个星球把它邻近的星球都看成是天。”所以在狂热信徒和哲学家对话的“物质”中,物质就是延展的,有体积的,坚实的,有引力的,可分的,可动的,“上帝可能给它整千种其他性能,是我不知道的。”
排除了奇迹,排除了天启,排除了迷信,一切在人类的天性和自然的本性中建立属于自己的自然法:友谊是什么?“在希腊,友谊本是宗教和立法的一部分。”自尊是什么,“自尊心根本不是一项大罪,这是人皆有之的一种自然情感;在虚荣与罪恶之间,它比较更近于虚荣。”德行是什么,“德行不是一种善,而是一种义务;它是另外类的品德,是高一级的。德行跟痛苦或快感毫不相干。”在这个理性主义、自然论和善的世界里,伏尔泰的质疑、反讽和否定,当然不是一种无神论,而是要去除偶像崇拜,要抹杀宗教狂热,一种基于科学的证明,是在“目的因”里,否定了自然界的目的,“大自然赋给我们的那些工具不能总是在运动中的目的因,而这种目的因必有其结果。”眼睛并不一定时刻睁着,感官有休息的时刻,修道院的女孩被关进大门,目的因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有意图,就会有目的因,“我觉得主张在自然中没有任何意图,便等于把视觉和悟性全都堵塞住;如若有意图,便有一个有智慧的原因,便有上帝。”上帝成为目的因,不是因为他是创造了世间一切奇迹的上帝,不是因为他是让人崇拜的上帝,不是因为他是毁灭了天性的上帝,而是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他支配了一切的永恒规律,他创造了万物——他是把理性赋予人类的上帝,他是把真理灌入人类耳朵的上帝,他是启蒙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