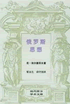|
编号:H47·1970702·0383 |
| 作者:(俄)什克洛夫斯基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89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7.50元 | |
| 页数:371页 |
宣称文学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的俄国形式主义对20世纪以后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对传统的文学“摹仿”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对文学作品的结构以及意义表达提供了多种可能。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灵感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从而彻底延长了文学自身传达时的意义,特别是诗歌。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莫斯科语言学会”的托马舍夫斯基、“诗歌语言研究学会”的什克洛夫斯基等。本文论选录了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埃亨巴尔姆、梯尼亚诺夫、托马舍夫斯基、日尔蒙斯基等五人的文论14篇。
诗的材料不是形象,也不是激情,而是词。诗便是用词的艺术,诗歌史便是语文史。
—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
从否定开始,到肯定结束,从解构开始,到建构结束,当日尔蒙斯基把诗歌史称作“语文史”的时候,就开始把诗学的任务建立在材料学之上,而把词作为材料的唯一,并非是回到科学语的规则之上,只是关键的问题是,当激情和形象从诗的材料范畴中剔除,仅仅在词的世界里,一首诗如何表达感情?如何形成审美?如何在读者中引起共鸣?
而这个被提出的关键问题或者也是日尔蒙斯基所要驳斥的一种诗学观。表达情感、形成审美、引起共鸣,是不是诗学所要研究的目的?当一首诗以体验和感受作为其写作的原因,它实际上提出的是一种内容构建问题,而传统的诗学就是以二分法把一首诗分成形式部分和内容部分:这部作品表达了什么,这是内容意义上的探寻,这种东西是如何表达的,它用了什么手段作用于我们,使我们对其发生感知,这是对于形式问题的疑问。
其实不光是诗歌,任何艺术作品都以这样一种流行的方式寻找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在日尔蒙斯基看来,这种将“怎么”和“什么”约定对立的二分法看起来是对统一的审美对象进行实质分析的不同方式,但是很明显,把艺术作品区分为形式和内容是一种人为的割裂,至少也是含混不清的,“这就导致把形式理解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外表装饰,同时也导致把内容当作美感以外的现实性去研究”,也就是说,如何表达的形式问题是为表达什么的内容服务的,当形式退居到次要地位,就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外表装饰”,从而忽略了形式具有的意义。
这也是日尔蒙斯基所要否定的一个方面,而这种否定的一个实质意义是取消分类,取消割裂,在他看来,“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已是新内容的发掘”,形式发生变化,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它在本质上形成了新的内容,当我们说“任何一件物体都下落”的时候,我们似乎透过形式看到了具体的内容,但是当我们又说“下落乃一切物体的共同属性”的时候,句子的逻辑内容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是很明显,内容发生了改变,而这种内容的改变并不是内容自身的添加和删减,而仅仅是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甚至在这种词的变化中,“思想的心理流程随词的重新选择与组配而发生变化”。
内容发生改变,思想的心理流程发生变化,而这一切仅仅是词的选择和组配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形式上的改变变成了新内容的挖掘,“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所以回到诗学的母题上,日尔蒙斯基认为,诗歌的材料就是词,诗是用词的艺术,诗歌史便是变化着的语文史。在这个基础之上,日尔蒙斯基对于诗学的定义是:“诗学是把诗当作艺术来进行研究的科学。”诗学是一门科学,科学需要的客观,“我们在建构诗学时的任务是,从绝无争议的材料出发,不受有关艺术体验的本质问题的牵制,去研究审美对象的结构,具体到本文就是研究艺术语言作品的结构。”
审美对象就是诗歌作品,就是本文,这是一种本体论的阐述,当诗歌回到词语,当词语体现变化,便是消除了内容和形式约定对立的流行观点,便是融合了审美对象的科学研究中发现意义,也从而构建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诗作中的主题不是脱离语言表达而抽象存在的,而是通过词来实现,并服从于象诗歌词汇所具有的那种艺术结构的规律。”而这个从否定开始的观点,也是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所提出的观点。
“艺术就是用形象来思维”,这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波捷博尼亚也说,“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包括诗歌。”这个普遍的观点被提出来,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诗歌是思维的一种特殊方式,当用形象来思维的时候,可以轻松建立审美感,因为“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智力、节约感知力,使你‘感到(思考)过程相对而言是轻松的’,也就是说,形象思维的重要任务“是它们可以通过对各种各样的对象和活动,分组归类,并通过已知来说明未知”,形象化的目的可以使形象接近我们的理解,闪电比作聋哑的魔鬼,天空比作上帝的衣装,都是这样的思维产物。但是什克罗夫斯基却认为,这种把诗歌称作形象思维的艺术创作活动却是无意识的、机械的活动,“形象几乎是停滞不动的;它们从一个世纪向另一个世纪、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流转,毫无变化。形象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上帝’。”甚至是一种代数式的思维方法,它会吞没生活,使生活成为虚无的东西。
什克洛夫斯基对形象思维的否定,其实就是为了构建艺术的本体,而这也正是俄国形式主义最重要的观点: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决心以对待事实的客观的科学方法,来反对象征主义的主观主义美学原理。由此产生了形式主义者所特有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新热情;哲学和美学的臆想被抛弃了。”深受日内瓦语言学派、胡塞尔现象学、象征主义、未来派、立体主义等等的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一九一四年开始扬起了属于自己的大旗,他们所反对的就是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我们决心以对待事实的客观的科学方法,来反对象征主义的主观主义美学原理。由此产生了形式主义者所特有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新热情;哲学和美学的臆想被抛弃了。”而这种反对实际上就是要保持文学作为科学的一种独立性,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独立于政治,独立于作者,文学作品就是审美对象,只有从作品本身来分析和阐释,才能发挥其文学的特色,才能构建属于文学的本体。
否定形象思维,是这种否定的第一步,而否定当然是为了建构,如何发现文学的客观属性,如何界定艺术的科学本质?当什克洛夫斯基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那么,石头如何真正成为石头?当诗歌要成为其自身,那就必须从诗歌的材料中寻找这种属性,而这便为“形式”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和实践双重的可能。回到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当诗的材料回归到词本身,它需要的就是,从词这一材料出发,以艺术体验的问题为切入点,去研究审美对象的结构,去研究艺术作品语言的结构。关于词的结构变化就是一种形式的变化,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在《诗学的定义》中,也认为,“所有成功地找到最简单形式的、能被牢记和不断重复的表达就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较大规模的结构,它是不依赖于日常生活的偶然说话条件,但是它具有本文的固定不变性,“文学是具有自我价值并被记录下来的言语。”在他看来,形式具有某种固定化的意义,这是形式的一个特点,“在大多数句子中,词之间联结得十分牢固,并相互制约着,因而有可能从句中抽取出个别词而不使句子丧失原义。”
但是当托马舍夫斯基把文学结构解释为一种固定不变性的时候,并非是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种静止状态,而是强调其形式的整体意义,但是当作为基本材料的词在本文中存在的时候,它却是在改变中注入了新的内容,这是形式主义所强调的“变化论”,托马舍夫斯基说:“上下文使它们获得词义。”尤里·梯尼亚诺夫说:“词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它是变色龙,其中每一次所产生的不仅是不同的意味,而且有时是不同的色泽。”引用保罗的那句话就是:“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文学的。”无论是托马舍夫斯基所说的词的转喻,还是尤里·梯尼亚诺夫说分出的意义的基本特征还是次要特征,其核心逻辑是词这一形式在本文中的变化,而正是这种形式意义上的变化,才赋予文学作品真正的文学性。
所以,形式主义的核心不是词的材料说,而是产生文学性意义的词语“变化论”,尤里·梯尼亚诺夫认为:“‘词’的抽象体就象一只杯子,每次都重新按照它所纳入的词汇结构以及每种言语的自发力量所具有的功能而被装满。”托马舍夫斯基对词义的变化进行了综合考察,而日尔蒙斯基提出了理论诗学和历史诗学,在他看来,理论诗学是“解释这些诗歌程序的艺术意义,解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和本质的审美功能”,而历史诗学是澄清各种诗歌程序在诗歌的时代风格上的起源,阐明它们与诗歌发展史的不同时期的关系。扩大到艺术领域,这样的“变化论”其实就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反常化”手法,也就是陌生化理论。
要使石头成为石头,不是让石头这一形式成为永远不变的物,它需要的是另一种命名,“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也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形式,通过这个材料,“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石头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反常化”手法,就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使它变得陌生,而艺术就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推而广之,他认为,“凡是有形象的地方,几乎都存在反常化手法。”所以他把诗歌定义为“受阻的、扭曲的言语”,就是在陌生化的世界里,在变化的形式中,“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
在《故事和小说的结构》中,什克洛夫斯基对于小说创作,也提出了“反作用”的手法,“构成一部小说不仅需要作用,而且需要反作用,即某种不一致的东西。”这种反作用是虚假结尾,是否定结尾,是阶梯结构,是穿连程序。而鲍里斯·埃亨巴乌姆在《论悲剧和悲剧性》中,对悲剧创作手法提出了“应当用怜悯激发享受”的观点,“如果主人公的死仅仅由于个人的过错,那么他的死便成了罪有应得,这样一来便使得怜悯和享受都削弱了:‘残忍的’观众要求(并且他是对的)无辜的牺牲。”悲剧重要的不是形式的体验,不是形式的激情,而是形式的直观,只有当观众宁静地坐在沙发上,“并用望远镜观看,享受着怜悯的情感”,艺术才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的艺术就是实践了“形式消灭了内容”的作用,“它取自心灵,又显现给观众,观众则透过它去观察艺术组合内的迷宫。”尤里·梯尼亚诺夫则在《论电影的原理》中对电影艺术的形式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电影还是诗,有一点很重要,即不去表现注意力所关注的那一物体而表现与其有联想关系的另一物体。”它不是为了“可见之人”和“可见之物”,而是为了“新人”和“新物”,只有在镜头这一形式的处理中,才能建立“自己的时间”——无论是特写、镜头重复,还是各种蒙太奇,形式建立的是一种变化关系,是一种节奏,是一种运动,“电影中的可见世界,并不是本来的世界,而是意义相互关联的世界”。
变化论在日尔蒙斯基那里甚至变成了建立形式的程序,他在《论“形式化方法”问题》中提出,形式化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也是一种世界观,“形式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艺术中的一切都仅仅是艺术程序,在艺术中除了程序的总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别的东西。”程序包括韵律学结构、词的风格、情节分布结构,主题的自我选择等等,在他看来,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反常化”手法和复杂化形式的程序只是为了满足“较落后的读者的意识中的进步”,也就是说,它们是形式主义派生的特征,要摆脱死板的艺术公式,必须建立一整套的艺术程序,只有艺术程序才是艺术发展的唯一因素,而艺术程序建立的唯一标准就是康德所提出的美学公式:“美是那种不依赖于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
文学艺术要从内容和形式的二元论中脱离出来,要从形象思维的怪论中解脱出来,要从象征主义的主观中心中突围出来,要从政治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而最终不管是“诗便是用词的艺术”,还是“凡是有形象的地方,几乎都存在反常化手法”,不管是“形式消灭了内容”,还是镜头建立了自己的时间,当一切的形式主义都回到“美是那种不依赖于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这个终极公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中回到了文学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