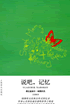 |
编号:E54·2100109·0770 |
|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09-4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393页 |
尽管纳博科夫在自传《说吧,记忆》中坚持认为“什么都不曾失去”,然而在1919年4月的一个夜晚,他在俄罗斯留下并无感伤的最后一瞥,踏上了永远的流亡之旅。当时他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一切确实都已失去:故乡、家园、财富甚至包括自己的母语。“我在思想上回到了过去——思想令人绝望地渐行渐淡——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通道,结果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1966年,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前言里这样写道。在这篇与正文一样写满了人生经历与创作记忆的前言里,他将自己的一生比喻为“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
“这部作品是有系统的、相关的个人回忆录汇集起来,地域上,从圣彼得堡到圣纳泽尔,时间跨度是三十七年,从一九〇三年八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只有几次进入了后来的时空。”我一直无法理解”进入了后来的时空“到底是指什么,那时,纳博科夫已经结束了20年的流流亡生涯,成为一个美国作家,那时他已经开始放弃俄语写作,那时离他最有争议的小说《洛丽塔》问世还有15年的时间,所以看起来时间在纳博科夫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两种可割裂开来的记忆,任凭自己像“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旋转出命题弧、反题弧、合题弧,和历史一样,在记忆中刻下各自的轨迹,“螺旋在实质意义上是一个圆”,而那些经历最后变成生活最大的财富,而对于纳博科夫来说,一九四〇年以前的记忆是与某种母性有关,是与俄罗斯祖国和民族有关,与“强烈和单纯的虔诚”的母亲有关,与“归于寂静时”第一首献诗给塔玛拉有关,与流着犹太血统的妻子薇拉有关。
已经一年多了,它一直压在待阅图书的最底层,而我开始阅读之后,也总在一种很游离的状态下进行,一是关于纳博科夫,关于《洛丽塔》,我已经快要遗忘了,那种发生在我大学时代的阅读记忆早就破碎了,相反,作为《洛丽塔》DVD版的《一树梨花压海棠》却留下些深刻印象,这名字的暧昧很有中国古典的艳丽色彩,可是这个故事在道德的危桥上是容易被落入小水的,洛丽塔毕竟无法在所有人中完成这样的颠覆性的革命:“人性中的道德感是一种义务,而我们则必须赋予灵魂以美感。”所以对我来说,《洛丽塔》只是一部小说,和美国文学有关,和纳博科夫有关,10多年了,它当然会逐渐老去,当然会被淹没在记忆中。二来,是对这本书的体例,《说吧,记忆:自传追述》这是书的全名,首先是一种自传,其实才是关于记忆的追述,所以这体例大体是和散文有关,而我很难就一册散文作品发表很多阅读感受,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快餐色彩浓郁的文学消费样式面前,我基本上是解读不出什么形而上意义的,或者说,我很不喜欢用散文的架构来追忆自己的生活记忆,尤其是在纳博科夫这样逐渐淡出视野的作家身上。
综合以上两点,大致可以看出,我对这册图书的购买显然是在计划之外的,甚至在阅读中间还有一些无奈,说实话,在挑选图书的时候,我是不了解里面的内容的,我甚至以为是一部虚构小说,纳博科夫的语言必须是在虚构的文学中才能驾轻就熟,而自传回忆对他来说只是某一种树碑立传式的媚俗做法——很凑巧的是,今年的4月23日是纳博科夫诞辰112周年的日子,离我阅读完《说吧,记忆》还有20天的时间,距离如此靠近,我仿佛闻到了20世纪初的那种俄罗斯作家身上散发出的技巧性和冒险性的游戏特质。于是硬着头皮,从3月末到4月初,把记忆坦露在这个初春的日子里,把纳博科夫的往事用一目十行的游戏心态去解读,是的,那里有风花雪月,也有凄苦和无奈。
纳博科夫实在是一个天才,也从来都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追求,在他的孩提时代,我们看见了纳博科夫对于数学的天才敏感性和理解力,超过了正常人,他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里度过的,记忆的幻灯片所聚焦的,是那些庄园小径,童年玩具,捕蝶经历,棋题设计,色彩的涂抹,初恋的心悸,叶的卷曲,字母表的彩虹,海滩上的碎瓷片。这些都在母亲的影响下,因为作为一个母性强大的人来说,母亲遵循的简单规则就是“全心全意喜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是一种彻底的融入,在纳博科夫看来,这颠覆了那场俄日战争的记忆,颠覆了父亲的政治生活对他的诱惑,“我在大自然中发现了自己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实用主义的喜悦。”于是那些蝴蝶,那些童年里的记忆都成为喜悦的源头,讨厌约束,讨厌规则,也成为一个孩子最基本的反抗,“从七岁开始,一切我感到和框在长方形范围内的阳光有联系的东西,都受到唯一的一种激情的支配。”在激情的支配下,他们和家庭教师进行着反抗式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规则都是可以改变和颠覆的,他们只想在自己的家园里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
但这些理想主义的想法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遭到解构,而对于纳博科夫而言,他的解构就是寻找心理的那种寄托,回归母性。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友,他都希望“全心全意地喜爱”,而由于特殊的关系,纳博科夫走上了一条流亡的不归路,而这次的打击更大,几乎把他赶出了俄罗斯这片土地。对于这样做一种结局,他也只能默默承受,纳博科夫的个人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抗争史。纳博科夫1899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十五岁时已继承有百万家财,良田万顷,庄园一处。然而十月革命爆发,举家逃亡,走上漫漫流亡路,一生永不返乡。几度流离,从俄国世袭的财产,只余一只质地精良的旅行包而已。在欧洲,父亲遇刺,他不得不自谋生路,教授法语、网球、拳击和英语为生。二战爆发,他携妻逃至法国,又因为其妻薇拉的犹太血统,不得不再次踏上流亡之途。期间母亲贫病交加,客死异乡,其弟死于纳粹集中营。在美国,他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作家,不得不放弃自己一流的俄语,而使用二手的英语写作,这对任何一个作家,尤其彼时年逾不惑的他都是一种“个人的悲剧”。
这其实就是沉重,他必须告别祖国,必须踏上异乡之路,必须改变自己的语言,无论如何,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充满着颠沛流离的味道,“流亡生活的忧伤和辉煌”,到最后也是随着时间而消逝,而成为作者心中最后的痛。对于祖国,对于流亡,纳博科夫心中有种无奈,“失去祖国对我来说就是失去我的爱。”大爱就是小爱,就是突破的框,就是非实用主义的喜悦,就是归于沉寂后的诗。
颠沛人生,远离政治,风云中继续拈花微笑,这也许是《说吧,记忆》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那些失眠与爱,那些孤僻与自由,那些离别与游戏,个体的记忆也都是民族的记忆,1918年塔玛拉致纳博科夫说:“下雨时我们为何感到如此快乐?” 这或许就是一种记忆中最弥久的信仰,和生命有关,和自由有关,和大自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