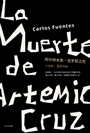 |
编号:C57·2120320·0870 |
|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9月 | |
| 定价:38.00元亚马逊25.80元 | |
| ISBN:9787020086573 | |
| 页数:402页 |
他在病床上看着死亡向自己走来,在或清晰或迷糊、或明或暗的思绪中,这个骄傲的新贵族追忆自己绮丽而又残酷的一生:革命时如何英勇作战,如何失去最爱的人,如何逃避被处死的厄运;革命后如何与总统之女卡塔琳娜结婚,幸运地得到总统的青睐,却被妻子憎恨;他的财产如何成倍地增加,如何获得显赫的地位和万贯家产……这部被“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使卡洛斯·富恩特斯享誉世界文坛,书中的革命、死亡、独裁,或许就是拉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小说“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优美和惊心动魄的力量”,第一句是这样的:雷希娜长长的眼睛半开半闭,在发亮,好像是块黑色而闪亮的伤痕。他深深呼吸了一下。雷希娜的双手合到他的后脑勺上,两个人的轮廓又在一起了。”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
你就是这个走向大地,发现大地,从自己的出发点走出来,发现自己归宿的孩子,而事至如今,死亡已经使出发点和归宿合二为一,不顾一切地在两者之间插进了自由的锋刃。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个纪年的最末端,接下去就是全新的一九五六年,那时距离他“终于进入人生”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已经67年了,而距离飞机降落还“镇静自若的”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还有最后的4年,所以这既不是他的生,也不是他的死,是变成老头靠近死亡的时间,或许也没有了爱情,而只有身体的回望,那些女人不在身边或者在身边,但都是“自由的锋刃”所不能插入的,她们起先是爱情,是肉欲之外的那种生死之恋,但是最后当身体死去,爱情死去,肉体成为女人唯一的注解,“这些该死的女人……他们懂得这么多的小聪明,有那么喜欢忸忸怩怩……把开始阶段的拖得老长……先是不肯,然后是犹豫,最后是等待,然后是勾引,哎,应有尽有!”犹豫、等待、勾引,当时间最后摧残了一个时代的欲望,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甚至想象中的记忆,雷希娜、卡特琳娜、劳拉,以及最后的莉莉亚,尽管有“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成为一种摆设,“不但没有挑起他的欲望,反而使他充满了克制,一种恶意的禁欲。”
女人的时间,贯穿在一个男人的生活中,他已经变成了老头,在一九五五年即将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寻找自己应有的归宿,只是被模糊的不只是爱情和肉欲,还有革命,还有战争,还有财富,还有大地。所以,发现自己的归宿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而到最后看到了死亡,归宿便成为虚无,可贵变成了可怕,大地会在哪里?
这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疑问,“谁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次像你那样既体现了善,也体现了恶,同时受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这是大彻大悟的开始?如果把一部分的时间抽取,那么这个开始就是回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回到“克罗—福,我相信字母d是不发音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三十万元的股本的股东,在五月五日大街寻找那些大地,财富成为一生的荣耀,“我赢了许多人。我赢了一切人。”而在财富的陷阱之外,必定是要看到那些善和恶,那些超脱出来的生死,或许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没有完全看见,或许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抵御身体的痛,“我很快会痊愈”,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原谅他们”,让敌人在那一天消失,也让女人们在某一种身体腐烂之前,暴露她们最可怜的欲望:“到了最后时,棺材落到了那个洞穴里,一大批女人在我的坟墓上会不会一面哭哭啼啼,一面又给自己的鼻梁上抹粉?”
但是一个身体里会长出多少这样的狂放,傲视一切的无耻和无聊,而剩下的真实却是“多么无用的抚摸”:“我想摆脱它的接触,但我没有力气”,卡特琳娜的手变成了发现那个编年史人生的罪恶之手,让身体提前在死亡之前死去,对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太过残忍,所以在他看见的那种善与恶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下,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返回到我们一直抚摩的封面,它刺激我,成为我购买并阅读的全部理由,仅仅在于黑和白构成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黑色的背景像是我们面对死亡肃穆的颜色,庄重、压抑,而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和Carlos Fuentes,人物和作者的西班牙文呈现骇人的白,有些错乱地分布着,将黑色压在下面,没有反抗。而在那右侧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题目,与套在外面的封面呈现的白色不一样,这里是红色的中文,从西班牙语变成汉语,完成了一种颜色的变化,没有原因,或者只是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就可以为阅读之后的标题寻找到改变的充足理由。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作为卡洛斯·富恩特斯1962年的那本书的标题,已经活过了60年的时间,它比阿尔特米奥·克罗斯71岁的生命略短,所以很可能看不见那条善与恶的线索,只是那么拗口地占据着拉丁美洲文学的位置,那么当60年后的阅读变成某种破解的努力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就是一个拆除围拢在里面的符号的过程,书名号死了,也就是60年圈定在那里的历史死了,重新被阅读,就是重新被书写,重新寻找故事。在死之后,便是“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它是历史,它是文学,它是生命,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它完全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反对政权的一次反抗:它就是“他妈的”,粗俗,却是力量,这个字眼是一切反动的根源,是一切力量的化身:“诅咒,目的,喧嚣,生活的计划,所属的关系,回忆,绝望挣扎者的呼声,穷人的解放,有权有势者的命令,打架和工作的号召,纪念爱情的铭文,出生的记号,威胁和嘲笑,作见证的圣徒,吃喝玩乐的酒友,象征勇敢的利剑,代表权势的宝座,象征奸狡的犬齿,家族的族徽,山穷水尽的救生圈,历史的概括:墨西哥的标志:你的字眼。”
其实,“他妈的”远没有结束,作为墨西哥的标志,一定是革命与历史有关,一定和身体与死亡有关,所以“它叫喊,它消失,它生活在每张床上,它贯穿着友谊,仇恨和权力的编年史”,它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字眼,它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标志,它是墨西哥文学的风暴,它是抵达汉语之岸的阅读方舟,那么当完成这一系列的仪式,我们就可以平安地进入故事的核心,寻找关于死亡的线索,寻找关于革命的历史,寻找关于身体和欲望的不同呈现,以及领袖、爱情、罪恶、自由等一切的存在,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甚至是他,是我,是你,人称的单数里是每一个不同的世界,它一定活在文本之内,在翻阅到每一页的时候,“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就会打破迷宫,打破沉默,在最后的生命荣光里发现所有的归宿意义,就像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顿悟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一样,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时,会看见那些不曾走远的日子:“有的则历历在目——邂逅与拒斥,昙花一现的爱情,自由,怨仇,失败,意志。
那些词组排列在一起,在死亡到来的时刻一定是洞察到了死亡之中的自由和自由之中的死亡,”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这是蒙田《散文》里的话,在题辞里作了注解,而其实相同的意思来自于劳拉,“预先想好死亡,也就预先想好了自由。”在死亡和自由之间,死亡一定是前提,或者说不死亡才是自由的前提,所以对于死亡最终实现的身体来说,是一次万劫不复的存在,“如果死掉,你就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了,你就不是七十一岁了,你的体重就不是七十九公斤了,你的身高就不是一米八二了,你就不戴假牙了,你就不抽黑色烟丝了,你就不穿意大利丝绸的衬衫了,你就不收藏马具了……”“如果……不”的句型背后是一个身体不想毁灭来换取更多自由的向往,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从最后一部分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出生,到第一部分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的死亡,翻转过来,本身就是在颠覆这种秩序,所以对于最后的归宿,身体在人生中不断地更替,不断地呈现新的自由,身体之变也直接折射着肉体的爱欲。首先是雷希娜,她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完全是爱,是生与死中结下的爱,崇高而无二致,或者一生都沉溺在这爱的世界里,而革命事业让他们分道扬镳,追击敌军导致了分离,“他朝着南方,朝着首都;她就回到北方,回到辛纳洛阿的海边,也就是她结识了他并委身于他的地方。”错开的爱情,也是身体的分离,她死了,在革命中死去,只有那裙子在风中飘扬,那一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中尉,这一场爱情的死亡也让他的身体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裂变;而当革命事业继续前进时,他结识了卡特琳娜,这是一个让他的身体开始第二次替换的女人,却完全是事业或者革命的牺牲品,因为她只是为了探寻哥哥致死的原因,委身于他或者只是一次交易,“双眼、双唇、结实而柔软的胸脯,既是哀恻而又幽怨。”肉体带来的并不是欲望,而是恪守在那些背后的那些线索,她成为他的贱女人,“报杀兄之仇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抱这个人,拥抱他而又拒绝把他企图在她身上找到的爱情献给他要把他拖死,把自己的苦水一一挤出来,变成毒汁,把他毒死。”身体变成了交易,变成了相互报复,那场政治的“逼婚”完全变成了可耻的来源,“我让他给玷污了……我却得到了快感。多么可耻啊。”在享乐和羞愧之间摇摆的时候,身体也处在某种爱欲与政治的摇摆之中;当然,还有劳拉,自由和死亡看透的劳拉,还有莉莉亚,仅仅作为一个陪他度过假期的女人,这女人的更替,是身体的向下滑行,而最后,甚至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没有了任何兴趣,这也就是身体在更替中最后必然要走向的死亡。
而身体并不仅仅是身体,它不独立于时间之外,在身体的不断更替这样的命题下,必须有一个时间的更替,而在时间的更替中,表现为革命政权和领袖的更替。从被遗弃的命运开始,到投入联邦军反对独裁,再到墨西哥革命的身先士卒,再到最后成为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发迹发财,人生在一系列的变革中被改写,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入死,也见证了无数的溃败和死亡,对他来说,甚至生命也是一次阴差阳错的选择,比如深夜逃命而被人鄙视为“卖友求荣者”,当卡特琳娜的哥哥死去,所有人都在怀疑,“回到普埃布拉的竟是他,而不是被枪毙了的贝尔纳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一次化装舞会,是一次冒名顶替,是一次可以郑重其事地开的玩笑。”就像身体的更替这一命题一样,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是一次替代的过程,而这种替代也直接给了他走向政治“自由”之路的捷径,那就是不断地见风使舵,不断地阿谀奉承,不断更替心中的领袖:“他择主而事一直都选择得很对,总是选择最有出息的,选择新兴的领袖,反对穷途末路的领袖。”对于他来说,政治斗争就是“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大悲剧”,只有当自己成长为领袖,告别侏儒,“自己才能爬上去”,所以他会选择卡特琳娜的“羞耻”来成全自己的政治资本,继而积累财富,当报纸、地产、不动产投资、硫磺矿、矿山、采伐区以及短期高利贷、收购地皮成为所操作的事物,他的帝国也就建立了,但是而当身体走向死亡的时候,那些政治资本和财富却变成了一种不自由的束缚,变成了对物的占有而湮没的“快感”,“做生意是做生意,宗教是宗教”的结果只能使自己丧失最后的信仰,而当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弥留在床上,两毫克吗啡或许可以缓解肾炎肠绞痛等身体的疼痛,但是“碧绿的眼睛,细瘦的胳膊和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头发”却也只属于那个曾经对自由向往的身体,也只有在最后的死亡阶段,才会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鼻子……我就是这副颧骨”,这里面透出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无奈,“我请求把我的脸和身体归还给我”这最后的期盼是对于荣誉和生命的期盼,但是死亡如此迅捷,当一切死亡完成最后的仪式的时候,他、我和你都将变成人称一种,变成更替的叙事者,而最终退出身体编织的人生舞台。
你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把你带在我当中,你死我也死……咱们三个……都死……你……死……你已经死了……我也死了。
最后一句话,却在”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的出生日开始,这是一个寓言,这是进入迷宫的入口,却放在了最后一页,“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不是病了。不是的。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不是的。”如果死亡全部是可以变成否定句,从而离开身体离开叙事或者离开时间离开”编年史“,那么“在过去的第一个里程碑和未来的最后一个里程碑之间”,让我们做一次关于身体和自由的实验,像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时那样,没有痛苦,没有抱负,也没有女人,只是“沿着河水放下去,让蝴蝶一路照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