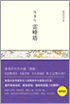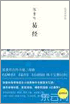 |
编号:C28·2110721·0815 |
|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 |
|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32.00元 | |
| 页数:376页 |
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划得余韵无穷!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角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20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易经》: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
“和楼上的世界两样”终于还是在琵琶面前打开了,“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这是一个少女走向向外道路的开始,告别了幽深的家族之痛,告别了弟弟陵死亡之痛,在她的面前完全呈现了不同的景观,后母不在了,为虎作伥的不在了,礼教也不在了,似乎那个新世界正在终结一切囚禁的噩梦,缓缓打开一扇真正的窗。
从《雷峰塔》到《易经》,从儿童到少女,这文本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这里已经没有了家族的哀怨,没有了挣脱的冲动,连琵琶自己都觉得自己小时候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伤感”,世界的口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城市,另一种人生。那就是香港。在母亲露看来,香港是出国的过度,而在琵琶看来,这里更多是一种宗教的庇护,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弥漫着宗教的关怀,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在一起,他们注册学习,他们仿佛要远离那个世界。香港在另一种语意上,其实是护佑,心理上的归宿,这就如寻找母体的努力一样,琵琶也在母亲露的照顾下接近自己的成人世界。
但这仅仅是表象,母亲和琵琶的关系完全从《雷峰塔》时代走了出来,那种依恋也慢慢解构掉,在琵琶看来,母亲已经的护佑是一次失败,在骨子里才是真正囚禁她的原因,历史老师布雷斯代给琵琶的八百块钱被怀疑是琵琶肉体换来的,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而露曾经的自由解放形象也不过是一种表象,在她心里还是恪守着传统的礼教和道德,甚至有些已经完全变成了猜疑,变成了压抑。“这些年来压抑住的嫌恶,以及为了做个贤妻与如母的长嫂所受的委屈,都在这时炸了,化为对琐屑小事的怨恨。”美德毕竟要付出代价,妇道也只不过是一种维系世界安稳的手段,而当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环境的时候,也就会慢慢被摧毁。这几乎成了女性的悲剧。
母亲露之外,琵琶找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姑姑,曾经以为“姑姑珊瑚和明哥哥:她还当他们是男女间柏拉图式恋情最完美的典范。”,但其实隐含着更多的乱伦味道,之后母亲口中所说的为钱而闹得不开心,二位一体的关系也迅速瓦解;另一个是表舅妈,围绕在汉奸表舅的身边,却无自己的生活,她的“七情六欲都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男人,毕生都坚定的、合法的、荒谬的爱着他。”直到表舅被蓝衣社的人杀害,表舅妈还无法从那样的秩序中走出来。在琵琶看来,“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这样就为女性的生存找到了一条欲破的方向,可是琵琶也是女人,也要面对爱情,面对家庭,面对每一次的成长。所以实际上和母亲的某种关系断绝也是女性走向自觉的一个标志,“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总会在某一代斩断。”
母亲哭了,战争爆发了,世界被颠覆了。《易经》将视角转向香港,转向更广阔的生活,这里已经有了家庭的破裂,有了战争的阴影,也有了少女的自觉意识,布雷斯代给她的八百块奖学金却“给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尊。”,而在战争面前,琵琶更多面对着生与死,面对国家,面对更多的迷茫,这里有宗教的,也有政治的,对于迷惘的琵琶来说,突围的方向更多是走向自省。对于宗教,她说“不能为了不想死了就完了,就去信什么宗教”,对于国家,则是一片厌弃之声,“我怕的不是轰炸,是到处都是政治,爱国精神,爱国口号,我最恨这些。”在女性被沉沦的礼教之后,琵琶又一次面对政治的斗争对人性的泯灭。比如“日本皇军是热爱文化的。”比如一提起“共产党”这三个字,“就会吹来一股鬼气森森的冷风”。甚至她用一种暗黑之心的来理解世界,“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她觉得真正的爱是没有出路的,不会有婚姻”,而在这样一个哀怨的世界里,“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圈禁疯子似的,唯有慈悲的松懈穿过,美丽动人,无法形容。”
但毕竟是要寻找归宿的,战争无非是让她这个愿望更迫切。琵琶对归宿的寻找其实就是在寻找生命的母体,当父亲变得专横,后母变得霸道,母亲变得压抑,及至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变得伤痕累累,像莲叶的故乡一样,中华文明变成荒漠之地,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母亲,能够包容她,能够安慰她,而那个充满孩童记忆的城市上海似乎已经成为她躲避的最后落脚点。“她的家人同住在上海的每一个人一样,那里是生活的基地。上海在政治上免疫,被动、娇媚、圆滑,永恒不灭的城市。”她需要归宿,需要在地理的回归中寻找到精神的领地,“被阳光包裹住”免于伤害的家。
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尽管香港发生的事已没有了实体,而是故事,她会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与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语言轰然的合唱,可是在她总是最无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她的囚禁是成长的代价,“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其实更多的是,琵琶在上海这样的记忆之城寻求精神的庇护,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她甚至不关心国家,不去想爱国,“这是她头一次以观光客的外人眼光来看中国。从比比那儿学的,她一辈子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住在中国。”她也不热衷于恋爱,在变化之中,她却是躲避着一切:“她想找《易经》……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再次回到书的题目,其实是一种双关,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隐喻,晦涩难懂或许就是对生活的极致追求,是人生的最后归宿。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自己的悲剧,她的上海早已倾覆,她的爱情早已哭泣,“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叫人伤感。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在《童女的路途》中说:
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