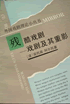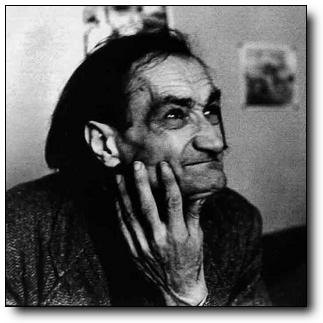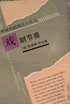 |
编号:X13·1951205·0218 |
| 作者:(美)凯瑟琳·乔治 | |
| 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4.10元 | |
| 页数:247页 |
凯瑟琳·乔治将节奏理解为“描述”一出戏剧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效果的力量。这其实就是戏剧的作用,戏剧打动观众的核心,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考虑场景、语言、风格等戏剧因素,“剧中人物相互之上的戏剧行动或变化”,以使戏剧的节奏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
弗劳拉 今天早上你注意到那朵忍冬了吗?
爱德华 那朵什么?
弗劳拉 那朵忍冬。
爱德华 忍冬?在哪儿?
弗劳拉 在后门口,爱德华。
—-品特独幕剧《微痛》
早上被注意的忍冬,后门口的忍冬,应该知道的忍冬,可是这些忍冬仿佛都是弗劳拉在重复,在她的台词里形成了一种连续性;但是对于爱德华来说,忍冬却像是一个陌生的词,陌生的花,他的疑问甚至看起来像是有意躲避,而这种躲避具有的重复也造成了“冷漠”的连续性。一种是制造问题带入情景而形成的连续性,一种是避开回答而具有的连续性,在关于忍冬的对话中具有了节奏的意义。但是节奏似乎是刚刚起来,当爱德华引入新的单词“牵牛花”的时候,连续性之后的变化就产生了。
而当牵牛花取代了忍冬,当变化代替了连续性,爱德华变成了主动带出节奏的人,他说到了“牵牛花也开了”,用的是一个否定式的疑问,“你刚才还说没开呢?”当弗劳拉纠正说,“我刚才说的是忍冬”的时候,爱德华又加深了否定,“说的是什么?”“那就是?”“我还以为那是日本山茶花呢。”当弗劳拉有点生气地说:“你完全知道你的花园里长的是什么。”爱德华的回答是:“正好相反。芮然我并不知道。”
连续之后的连续,变化之后的变化,停顿之后的停顿,以及否定之后的否定,他们的对话还在继续,他们的重复还在继续,但是很明显,这样的递进是单一线性发展的,而在这个发展变化里,凯瑟琳·乔治认为,“爱德华和弗劳拉的世界是风雨飘摇的”,之所以用重复,其目的就在于缓和某种“威胁性的氛围”,但是在“从进攻转为防御,从钟情转为厌恶,从邀请转为拒绝”的小小单元里,节奏似乎具有了某种情感上的共鸣,话题在继续向前,停顿在不断增加,甚至变得越来越频繁,而这样一种设置就起到了“引进新的内容来与冲突抗衡”,爱德华把话题从忍冬转向了牵牛花,是一种紧张,把牵牛花转向了日本山茶花,是一种紧张,又把话题从太阳转向了轻风,也是一种紧张。
“有节奏的重复把我们引向象征和冲突,这个事实是重要的。”不管是风雨飘摇的关系,还是威胁性的氛围,不管是走向某种梦魇的对话,还是蒙上阴暗色彩的喜剧,重复的意义在凯瑟琳·乔治看来,是为了让我们“吸引到接受和相信不可接受和不可相信的事物”。也就是说,通过重复而形成连续性的节奏,在观赏者那里具有了某种创造性启示,它带来的是重新构建“不可接受和不可相信的事物”——“它甚至明显到了立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并使我们怀疑我们刚刚进入的这出戏的世界简直模式化到了非写实的程度。”它和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怀疑,是模式化的重复,但是却是在不断重复的“忍冬”和停顿中产生的“牵牛花”、“日本山茶花”的单词意义上吸引了注意力。
重复和变化制造的效果,终于把我们带向了一种情景中,在爱德华·阿尔比的《微妙的平衡》中,整整三页的对话篇幅制造的是一个古怪的动态模式,“令人惊讶一相信一意外一相信一令人意外一相信一随风漂浮一随风漂浮一漂浮物一发疯一大茴香酒一漂浮一令人惊讶一揣测一发疯一大茴香酒一科涅克酒一揣测一揣测一完全发疯一丝带一科涅克酒-随风漂浮一科涅克酒一疯一丝带—惊讶一恐惧一恐惧一揣测一令人惊讶”组成的不仅是词语的重复和变化,也制造了节奏的含义;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里,胡言乱语和神态清醒的结合却具有了一种诗意的重复:“有一天,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不管是词语制造的古怪模式,还是育婴韵般的重复形成的诗意,它们都具有某种节奏,“节奏或动态的模式是理解涵义的线索。”爱德华·阿尔比需要是在台词的世界里建立内省的逃避,还要建立向外延伸的通道,而三页对话的篇幅对于我们制造的注意力就是一种外向的联系,而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里,那种超越时间的意象甚至把单词的涵义掏空了,但是却在荡然无存的程度上、在行动不可能而只剩下对话时,明显的节奏却被凸显出来,而这具有反讽意义的效果却正是节奏的涵义之一,文字本身变成了符号,因为对于节奏来说,“文字并不是用来代表什么;文字是用来代替什么。”
重复而停顿,连续而变化,甚至只剩下逃避,只剩下符号,在凯瑟琳·乔治看来,就是体现了节奏的动机,引用《哈姆雷特》里的那句话:“鬼魂在这儿。鬼魂在这儿。它消失了。”凯瑟琳·乔治说,“节奏之于我们,犹如哈姆莱特的鬼魂之于守夜的卫兵,常常令人费解,难以捉摸。我们寻觅它时,它不露面。谈别的事时,它却出现了—一但转瞬即逝。”出现却又转身即逝,寻觅却又难以捉摸,像是一种突然出现又消失的灵感,但是只要是出现,只要有了效果,节奏就是可以把握的。按照波列斯拉夫斯基《演技头六讲》中的解释,一件艺术品所包含的是不同要素的“有次序、可衡量的变化”,变化的过程是递进的,它的意义是刺激观赏者的注意力,而它最后的目的是“毫不偏离地引向艺术家的最终目标”。
凯瑟琳·乔治把这个定义引入到戏剧中,她认为节奏是艺术的实质,认为节奏是建立关系,认为节奏是体现变化,所以从波列斯拉夫斯基的定义出发,她发现节奏具有六个特点:首先,观赏者是头等重要的;其次,艺术家为观赏者制造一连串期待和这些期待的实现;第三,节奏涉及某种对立物之间的交替;第四,内容与节奏难以分离;第五,变化具有某种次序或模式;第六,一部作品有一个总体的节奏,一个总体的被模仿的姿态或行动。节奏是对立的统一,是变化的发展,是内容的有机,是总体的行动,而实际上在凯瑟琳·乔治看来,节奏最大的意义是在开放性场景中表现它的涵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小剧场里,如何能够体现体现它的开放性,如何制造它的冲突,如何在对话中提供跌宕的效果,如何在台词里形成可能性,“节奏这个东西如此微妙,任何速度上、变化点或变化幅度的变化,都会导致各个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新型关产生,因而都能改变风格、语调和涵义。”
凯瑟琳·乔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方法论的介绍来阐释她的节奏理论,在声音、单词和短语的重复中,制造一种动态的模式,这是一种反讽,正如品特所说:“有两种沉默。一种是无言的沉默。另一种也许是说了一大堆话。”一大堆废话最后带来的却是沉默,这是动态中产生的节奏涵义。而在讲话人在台词的长度变化和交替中,产生的是对话节奏;语言策略的重复中,重要的是“自言自语进入角色”的内心独白,它在重现、聚合产生的整体效果中制造了节奏,就如哈姆雷特,“他的内心变成了一座法庭,反复掂量着证据。”还有是“态度的模式化”,就是通过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表达行动,在行动中制造节奏,“重要的变化并不完全是沉默同声音的关系,而是进承同屈从、否定同肯定或拒绝同接受的关系。”
不管是单词重复、讲话人的交替、态度变化还是语言策略,所提供的的模式都是在完成一个动作,在叙述一件事情,它是单一的,而对于一出戏来说,保持节奏的最要一点是整体的连续性,这就是风格,易卜生的风格是“对感情的条理化或控制”,斯特林堡的风格是“提供了更多的对紧张的表达”,高尔基在《底层》中以客观的面目来讲话,契诃夫则以持续的、含蓄的反讽对我们讲话,“不论整个模式的一部分有多少,每个节奏的显示都是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而风格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保持整体连续性,它指向的是作者,也就是把我们“引向艺术家的最终目标”。
节奏也并非是外在的重复和变化,并非是明显的语言和风格,在凯瑟琳·乔治看来,节奏更重要的是反映它是视觉隐喻,它体现在场景和“象征性姿态”中。场景分为单一场景、多场景舞台、全景舞台和在场景之间“有限的递进”。场景提供了空间,作为一种存在,它本身就具有节奏性,“存在就有节奏。”在单一场景中,节奏更多表现为“重复自身的作用”——“这种重复赋予发生在它身上的各种变化以形式,通过那些变化的性质来显示涵义。”它以阴影、被重复的物体、台阶的线性形式等存在的节奏制造一种视觉性隐喻。而在多场景舞台和全景舞台上,通过场景的变化体现地点的变化,通过提点的变化递进一种主题,“重复对不同地点的运用、重复一个地点到一个地点的旅程、提供视觉性反讽(比如展示地点与地点之间的关系),以及强调递进。”但是很显然,这种递进是一种有序的变化,它带来的是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生机,更多的舒适,但是却要保持一种整体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带来了递进的逻辑性,提供了视觉性的线索。
而服装、道具等视觉性象征的姿态,对于节奏来说,也体现了着同样原则:“重复,变化和递进——也支配着它们的运用。”它包括人物的服装、人物的用品以及行动的地点、季节和时间,以及“外部意义上被加以模仿或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些视觉性领域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场景设置,受到舞台上人物的多少,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发生的行动有关,“谁对谁在什么情况下做了什么?”具有的意义把节奏带向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因为它不单纯涉及剧作家的创造,还涉及导演和演员的职能。也就是说,节奏不仅是和剧本有关,更涉及到现场,那么在现场意义上来说,除了导演的临场指挥,演员的临场表现之外,似乎还应该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观赏者。
在凯瑟琳·乔治对节奏做出的分析中,就强调过观赏者的重要意义,节奏的变化和递进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艺术家的要求,但是如何达到,那就是要在刺激观赏者的注意力中制造节奏效果,所以她认为,“观赏者是头等重要的”,而且,艺术家就是通过为观赏者制造节奏而实现他们的期待,甚至可以说,观赏者就是一种审美主体。但是很显然,凯瑟琳·乔治在阐述制造节奏的单词重复、讲话人的交替、态度变化、语言策略、场景隐喻等方面,并没有把观赏者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放在艺术家最终目标实现的可能意义上,只是简略地提及那个在剧外的“我们”。
声音、单词和短语的重复制造的是一种变化,凯瑟琳认为,“对话使我们对梦魇有所准备,同时又拉开了我们问它的距离,允许喜剧公然蒙上了阴暗的色彩。”在那些重复的忍冬和停顿之后产生的牵牛花、山茶花单词世界里,观赏者无非是“吸引到接受和相信不可接受和不可相信的事物”中,但是这种吸引只是局部的,甚至只是一种可能;通过讲话人的交替和词的长度制造的节奏,很像古希腊时代的歌队作用,凯瑟琳认为,歌队起到的意义是“间离观众”,是悲剧性结构的主要部分,也是对于舞台时间的填补,如何让观众产生间离效果而把舞台推向更广阔的场景,却并没有提及。在对风格的论述中,凯瑟琳·乔治认为,“只要观众或读者受到作为常数的风格的影响,风格在节奏方面就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作者正在有节奏跟我们讲话。”也仅仅是一种“讲话”,而且是单向性的讲话,即使是一种节奏,也完全是被影响的。单一场景具有的是视觉隐喻,当我们的目光追踪着那些阴影,那些台阶,那些重复的物体,在空间上注意到了节奏的潜能,并使我们充满了对于变化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甚至心理变化而具有的自由,也是被动的。
“存在就有节奏。”这是波列斯拉夫斯基的一句话,存在是舞台,是场景,是人物,是动作,是艺术家,当然也是观赏者,当他们接受,当他们阅读,当他们想象,甚至当他们拒绝和否定,在一种整体性的节奏中,他们就是我们,就是节奏的紧张和紧张的消逝,就是节奏有次序、可衡量的变化的主体,就是把节奏的递进引向正轨并最终达到艺术家的最终目标的体验者和创造者——即使偏离艺术家的目标,偏离期待,对于一种开放性剧场来说,这也是节奏可能性的真正意义,戏剧并非是文字、事件、行动、思想、人物的模式化,苏珊·朗格说,节奏的过程是一种命运,亚里斯多德说,这个过程是头,身和尾,它是活动的,它是开放的,它是多元的,“这种运动着并使我们随之而运动着的排列就是节奏。”而节奏的最终目的,是在运动之后形成停顿,形成变化,形成不是忍冬的牵牛花和山茶花,“剧作家的工作是要通过对特殊变化的精心地模式化和强调来吸引情愿的听众得出一个特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