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E22·2151117·1247 |
| 作者:方向东 注译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2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25.00元 现17.00元 | |
| ISBN:9787101088281 | |
| 页数:363页 |
《新书》又称《贾子》,是贾谊的政论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最初称《贾子新书》,《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今存10卷58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56篇。《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经济、教育、哲学思想,而政治思想最为突出。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宗首》、《藩强》、《权重》等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贾谊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感情充沛,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新书》:前车覆而后车戒
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过秦下》
年轻的贾谊站在汉初的时间节点上,看见的是过往,看见的是现实,对于“颇通诸家之书”的他来说,那历史的成败转换并非如过眼云烟,并非属于不变的时间段落,“观之上古”是一种眼界,“验之当世”是一种态度,不是遗忘,不是逃避,是要审察,是要变化,而对历史盛衰的考察意义是为了不蹈覆辙,是为了“旷日长久”,是为了社稷安定,是为了国富民安,是为了天下顺治。
否定而肯定,贾谊不是革命派,只是改良派,当他在《数宁》中写下理想的治国框架的时候,看起来是在俯视“当世”,为“旷日长久而社稷安”描绘一种蓝图:“臣窃以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亿,社稷久飨,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周得,后可以为万世法,以后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在这种至孝、至仁、至明的理想社会里,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匈奴四荒,乡风慕义,乐为臣子;天下富足,资财有余,民素朴顺而乐从令;官事甚约,狱讼盗贼鲜有;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万生遂茂。而其最重要的核心则是以仁义为经,以礼节为纬,以法为辅,使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而这样的理想范本并非是贾谊的一种创新主张,只是将儒家观点适应时代需要的一种体现,正如章太炎所认为的那样:“《数宁》一篇,是贾子以《春秋》为汉制作之本。”
理想是历史范本归纳而出的理想,所以现实也就成为“观之上古”而痛击出的现实。对于贾谊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离当世最近的无非是秦朝,所以秦朝的覆灭是最活生生的教材。为什么一个“宰割天下,分请山河,强国裂伏,弱国入朝”的国家,一个“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的朝代,会在“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美梦中迅即灭亡。而推翻秦王朝的仅仅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没有“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的地位,不是“抗九国之师”,没有“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的战术,但是却“成败异变,功业相反”。分析秦王朝的灭亡,贾谊提出的观点是:“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的反面是暴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逢为天下始。”不管是“怀贪鄙之心”,还是“行自奋之智”,不管是不信功臣,还是不亲士民,不管是“焚文书”,还是“酷刑法”,其根本就是“废王道而立私爱”,以暴力开创天下之业,而秦二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国家成为一个人的国家,没有了仁义,没有了君道,只有繁法严刑,不仅国家衰落,百姓怨恨,最终使得天下反之。
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自然规律,“故周王序得其道,干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这是对于周王以来道的背叛。但是贾谊在活生生的秦朝覆灭范本中看见了仁义不施的恶果,其实“察盛衰之理”对于他来说,也是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担忧。这是无为而治的时代,这是藩强而危的时代,这是礼乐而衰的时代,这是瑰政而行的时代,而这一切几乎都违背了贾谊心中的理想范本,都是社稷安定的一种潜在危险。而其实这种种的问题,就是缺少一种规范而持久的道。因为藩强,所以诸侯足可以专制,足可以行逆,后果便是“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专大权以逼天子”;因为礼乐之衰,所以“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最终的结果则是道德败坏,则是人伦颠倒;因为瑰政,所以“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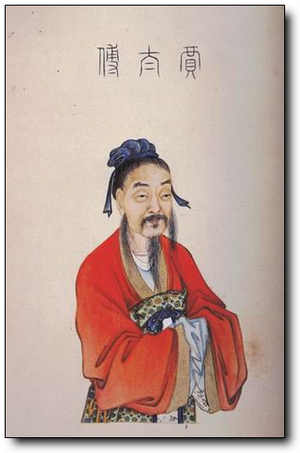 |
| 贾谊:无法逃离“无为”的历史循环 |
所以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改变现实的问题,走向天下顺治的理想,就必须变无为而有为,以至孝、至仁、至明为出发点,建立一个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的国家。很明显,在贾谊看来,要保持一种和谐,就必须有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皇权专制,就是权势法制,如果诸侯的王宫守卫、郎中、丞相、太仆、太后、后、指示都与天子一样,那么在没有区别,权力渐大的现实面前,“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谁为主?谁为臣?谁为本,谁为末?“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也就是说,要建立秩序,就必须使得上下有一种等级制,有尊又卑,有贵有贱,有上有下,有主有臣,那么,“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所以遵循的道就应该是“高者难攀,卑者易陵”,只有这样,才能“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推而广之,不仅君臣,还有父子,都是一种礼纪,而这种礼纪,在贾谊看来,就是一种天道:“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而要建立这样一种等级制度,这样一种权势法制,就必须行仁义,“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礼是一种道德,礼是一种制度,礼是一种方法,“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有礼,上才能恤下,有礼,下才能承上,有礼,才能“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而贾谊对于礼的方法论更为系统化,他提出的“容经”分为十六门,志有四兴、容有四起、视有四则、言有四术,有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有朝廷之容、丧纪之容,有军旅之容、车马之容;道、德、性、神、明、命是六理,阴阳、天地、人则以六理为内度,成为六法;六法外行,则为六术;六法与六术相应,则有六行;内本六法,外体六行,则生六艺,六律、六亲亦由此生。
以六为度,是贾谊哲学观点的框架,而遵循“容经”,则“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提出君道,提出美德,无非是一种等级制度的外化,所以贾谊将对太子的教育,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也就是说,作为未来的国君,太子必须具备圣人之德,也只有具有圣人之德,才能更好地行使仁义,更好的维护等级,“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从太子的使命,到国家的未来,再到左右的作用,其实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权势法制体系:“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长复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道之礼,明恭俭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爱以道之仁,明侗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斋肃以道之教。”
如果有了仁义的君道,有了严密的等级法制,那么在对待士民的态度上,则有了更明确更容易操作的规范,“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无蓄其实是无为,所以要改变“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的现状,就必须去瑰政行玮术,也就是要改变弃农从商的现实,改变本末倒置的制度:“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在具体的方法上,贾谊提出了“亲民思想”,不管是商汤“去三面舍一面”的做法,还是楚昭王发出“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的感叹,不管是“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还是周文王“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的看法,都是一种亲民思想,所以贾谊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名,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
民之为本,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等级制的一种体现,“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土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也就说,只有人君先有道,先有义,先有忠,先有信,才会有榜样作用,民才会如声音、影子一般跟随着人君,也就是说,作为“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的士民,他必定是在上下关系中遵循而为,是“人循其度”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贾谊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有道就是本,但是贾谊所说的道其实包含着“术”,道为本,术为末,“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道是“虚之接物”,就像镜子和秤砣,衡虚无私,而术之接物则是“品善之体”,包括孝、慈、忠、惠等五十五对范畴都属于术,“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言,则过败鲜矣”。而不管是方法论的术,还是“虚之接物”的道,其实都是德的一个组成部分:“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
德而为道,道而为术,其实虚虚实实,本本末末,建立的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一种秩序,“古者圣王居有法则,动有文章,位执戒辅,鸣玉以行。”以古者关今世,以有术替无为,贾谊的理想政治却慢慢陷入到一种改良的方法论,不管是权势法制的削藩政策,还是民为国本的民本想法,不管是皇权专制,还是积贮富民,不管是对匈奴“三表五饵”以德怀福,还是去瑰政行玮术,在“前车覆而后车戒”的思想下,其实都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甚至是一种功利主义,所以一旦贾谊被谪离开朝廷,一切的政治思想也就缺少了施展的舞台,也就有了强烈怀才不遇的茫然,所以即使一只小小的鸟飞入室舍,天生敏感的贾谊也会引起感伤,也会想到寿命将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而途经湘江那一首《吊屈原赋》,也是对于当世的一种怨愤:“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面对混乱的世道,面对被羁系的骐骥,贾谊也无法以一种超脱的方式逃离“无为”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