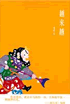 |
编号:C28·2110517·0806 |
| 作者:曹寇 | |
|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 版本:2011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6.00元 当当价16.90元 | |
| 页数:303页 |
看起来,封面卡通人物是沙僧,胸口挂着念珠,手拿月牙铲,嘴巴张开保持惊讶状,腰封上是加缪的一句话: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于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我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关系,《越来越》的书名里透出一种速度死亡的恐惧,流弹追上奔跑,或许也是一种古典人物的现代死法吧。第一次看曹寇的小说,很认真,在当当里只发现了这本小说集,《操》(坏蛋出版计划,2009)和《喜欢死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都没有发现踪迹,也越来越觉得像曹寇所说,这是一个操时代。这部中篇小说集包括《越来越》《水城弟兄》《挖下去就是美国》等篇目。作者用富有个性的文字带着诙谐与同情着意捕捉了都市与乡村双重渗透下的小城镇里的青年们,在一种近乎百无聊赖的气息里的小纠葛、小挣扎。这是一些不那么成功的人物,却渗透着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叹息。
《越来越》:一颗流弹的死亡书
这是一个让人感怀意蕴深远旷日持久、只逗号不句号的标题,而且极富感染力,我试着进行了粗鄙的模仿:比如世界越来越新鲜禅杖越来越锋利曹寇越来越诗意。这基本上概括了这本书的封面呈现给我的感官刺激:桔黄的外表下深藏着一个寓言,沙僧手持禅杖似乎正在寻找那个千古之谜,张开的嘴巴似乎正在爆着粗口,关于这一卡通形象在翻阅过的那一页中得以呈现:深邃的目光中都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喜怒哀乐,双眉紧锁的日子里,要学会对待越来越顽强的生命:死亡只是希望者的最后武器。
在这张曹寇的照片中,我一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个1977年出生的文艺青年,已经越来越重口味,在快餐文化流行的现实中,他的目光本身就带着生存的痛,2006年的邂逅让我对曹寇充满了敬仰,他不多言语也不苟言笑,喜欢抽烟,深邃地思考,给人感觉是与现实格格不入正在寻找理想的一代愤青。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于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这是阿尔贝·加缪的一句话,在封面的一张条子里,这句话刻进了纸张的肌肤里,也刻进曹寇的文字里,像涂抹不掉的标记。我一直想象流弹奔袭而来,在转角处追上脑袋,然后一命呜呼。我对这样突然的死亡充满着少有的快感,而在现实中,这样痛快淋漓的死法并不多见,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死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虚幻,以致我不得不使用文字的力量使死消除恐怖,从而回归到日常生活。
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未必需要什么深仇大恨。这是水城兄弟的死,里面有着化解不开的兄弟情义,而在更多的时候,死只是一种态度,是人生向前告别过去的态度,所以在《新死》中,我们看到:“高丽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此行彻底了结二人的关系。把未完成的完成(去乡下),把经历的重温一遍(做爱和划船),别无遗憾,死可瞑目。”死变成了另一种复古,变成了想象的的真实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死只是一种人生的际遇,一种概念,一种我们无法触摸的虚拟世界。
所以,对于文本的解读,一定要在曹寇关于文字的母体中获得,比如关于“越来越”的句式,最初在《所有的日子都会到头》中,在刚刚翻阅的第二页:“我越来越感觉自己缺少理由。”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的文字跳到了第三页,这种句子的破碎感让我对“越来越”的句式产生了疑惑,它只是一种生活着的状态,而不是对事物持久过程的描述。在主打的《越来越》中,我看到了一个文字跳跃者的内心独白:
·越来越冷的天气会使它们主动熟,能吃到正月。
·我的睡眠很浅。越来越浅。
·于是,他们真诚地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晚辈后代越来越幸福。
·他对越来越为广大青少年所喜爱的超女表示坚决的不屑。
·人民的口袋越来越鼓,越来越富裕,早已解决了温饱。
·即便是当下这个身高越来越高的时代
·她选择的也是越来越流行的长筒皮靴。
·风确实越刮越大,越来越刺骨。
我承认在一种文字游戏中,我开始感觉“越来越”背后的文字陷阱,曹寇似乎不想把这个陷阱讲透,他只站在远处,任凭世界被逐个颠覆。“我的困惑就是没人(包括自己)能搞得懂的困惑”,我一直觉得曹寇把“我”带向一个没有地位的旁观者的位置,或者说,我只是一种被虚构的产物,它来去自由,承载不了很多宏观的诉求,“有谁像我,成日里纠结于生活的鸡零狗碎?”
这样说,我觉得曹寇是别有用心的。除却《水城兄弟》,在这些小说中,曹寇一直想用一种违反规则的人物来搅乱既定的秩序,在王奎、张亮和李芫组成的世界里,“我”一直处在尴尬而神秘的地位,这其实就是“我”的缺失,第一人称的逃避,不管是《携王奎向张亮鸣谢》的“我”小曹,还是《美好的夜晚》中的我,每一个故事都试图挣脱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觉,但实际上是留下了更大的悬念,也就是说,“我”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虚拟的。
在《携王奎向张亮鸣谢》中,“我”很简单地获得了白小云的好感,那种费尽周折的追求在“我”面前不堪一击,“我”逐渐成为颠覆秩序的旁观者,看似没有任何瓜葛但实际上却是险象环生,“我”的颠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历史的,一种是空间的。历史的比如李唐和高丽的缠绵,完成了一种未完成的仪式,而空间的,从《挖下去就是美国》可以窥知一二。“教室就这么挖下去,就能挖到美国。”作为地理老师,挖下去就是美国,其实就是一种理论上的诙谐说法,并不可靠,很不科学。这种诙谐中蕴含着很多对意义的消解,包括崇高感、神圣感,以及遥远的距离,“我在沙发上跟王丽干那事的时候,也想到过她很可能正在回味大学时代与前男友的交媾场面。”王丽最多只是一个文字记录的符号,她不承载很多文化的终极意义,比如处女情结,比如爱的唯一性。
所以,曹寇对人物的塑造故意打破那种人称的意义,在《越来越》中,我们在前面看到了替换的夫妻、男人、女人的称呼,就和《所有的日子都会到头》中的余德水和桂兰,最后却变成了“我”的父母,崇高之情被瓦解成一男一女的性别建构,所以在《美好的夜晚》中,我们看到了对于生存的质疑:“你连机器人都不算?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谈你的家人,你有父母吗?我现在都怀疑你不是女人生的。”
性别、性格和家庭背景被悬空,越来越能感觉到曹寇对秩序颠覆的狂热感受,“我认为,小说是说事的文体,我只表达自身。”曹寇这样说。只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获得存在的优越感,不能获得爱情的意义,“一颗流弹”的希望并不在马路的转角,它一直出现在生活的呼热气息中,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像出轨的列车,碰撞在我们醒着的黑夜:“总之,一切看上去好像很美,或者真的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