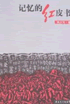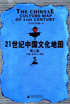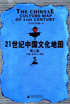  |
编号:W71·2060502·0737 |
| 作者:朱大可 张闳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版本:2004年5月第一版 |
| 定价: |
| 页数:377+437页 |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用较大篇幅以索引的方式汇集了文化关键词和文化事件。语词是文化心态的具体表征,语词的活跃不断扩展着新的话语空间,体现着小资、中产阶级的生长态势。诸如波波族、村上春树、“白骨精”、半糖、布列松等新生事物以及“死得难看”、“做人要厚道”之类的流行语言,在无形中更改着传统的话语模式。大众文化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一种话语方式。新新人类以自己的说话方式与保守的、虚伪的力量区分开来,他们通过改变语词的形式和分量来重构与现实的关系。大词依旧存在,却更多地注入了嘲讽意味。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戴着口罩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
【口罩】在2003年SARS大流行中最先出现的公共卫生学装备就是口罩。它被用以阻挡飞沬和病毒。但不久之后,口罩的功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它从嘴的卫士转变为一种美学物品,一种用于脸部的装饰物,用以替代五官(鼻子、嘴唇和脸颊)的表情功能。
橘黄色的封面,蔚蓝色的封面,它们层叠在一起,当被标注为第一卷、第二卷的时候,它们打破的是我曾以为只是上下卷的整体性思维。不是完整的合集,而是在设置了一个起点之后,通向无限延伸的某个终点——第一卷的时间标记是2001-2002年,第二卷则是2003年,“本书今后每年一卷,旨在密切追踪中国文化流变和未来动向。”内页的注释这样说,如此,当第一卷展现出“国风”式双年展之后,这套立志“成为人们巡视中国文化现状的精密地图”,则以2001年为起点,横贯整整100年——也就是说,会组成21世纪完整的文化地图。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也许在朱大可、张闳开始编撰这本系列丛书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象,它是“采风”备忘录,它是文化学习的导读文典,它是批评和研究的珍贵档案。21世纪开局之年,这一幅文化地图便以展开了卷册,而到21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们或许就可以被称为历史巨献。但是,这个涵括整整一个世纪的文化地图,这个预期会有100年的文典,记录的是一种在场的时间,还是一种回望的历史?
2019年百花盛开的春天,打开书册的时候,的确有一种回顾历史的体验感,它们在2005年的时候进入到我的视野,在一次朱大可、张闳参加的采风活动中,他们携带它们而来,作为最新的出版成果,这两卷图书凝聚着他们的心血,而当它们被陈列在书橱里,文化地图的确成为了一种静态的摆设,而在14年后真正打开,能强烈地闻到旧时的气味:2001年,蒋方舟还只有12岁,他的《正在发育》引起了“少年作家”的争议;2001年,九丹刚出版了被称为“妓女文学”的《乌鸦》,并引发了卫慧和她之间的恶斗;2001年,臧天朔还在和将其评为“国内歌坛四大丑星之一”的北京某网站对簿公堂;2001年,谢晋的新片《女足九号》刚刚开始公映,首映式上他强烈呼吁社会支持国产影片振兴。而2002年,重现大众视野的汪国真一纸诉状将百家媒体告上法庭;2002年,《大家》文学奖由于把金庸列入候选人而备受争议;2002年,诗人们正在天门山山顶完成集体裸体行为,这是中国诗人首次裸体行为艺术记录;2002年,“新北京,新奥运”大型演常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演艺明星正为6年后的北京奥运会摇旗呐喊。而在2003年,随着非典的爆发,中国作协八位作家深入一线,创作“非典文学”;2003年,网络写手木子美性爱日记《遗情书》引起轩然大波,每天20万次访问量成为中国点击最高的私人网页;2003年,巴金度过了自己100岁的生日,“我要为大家活着”成为百岁寿辰的巴金一句名言……
按月份书写的文化事件,都成为当时的新闻,新闻展现的是即时性,是在场的时间,所以当打开那一条条记录,仿佛进入了正在发生的时间内部,但是,当九丹、卫慧、木子美都已烟消云散,当汪国真、谢晋、金庸、巴金、臧天朔都已走完了生命历程,当奥运、非典、博客都已成为历史名词,进入时间内部是不是反而有了一种虚幻的感觉,退出,掩卷,进入到现实,才有某种活着的真切感——2019年至之于现在,是一种在场,而2003或者2004年,对于这些事件,是不是也是一种在场?对于朱大可、张闳,是不是更是一种对于时间的见证?
很明显,这一本“采风备忘录”的确是一种在场和见证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更像是有着时间性的杂志,而当编者立志每年一卷的计划时,他们的确用自己的努力体现着时代性:从第一卷开始,一直到2008年,他们保持了这个出版习惯,即使从最初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更换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务印书馆、上海大学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等不同出版社,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某些风格,但是这七卷图书毕竟成为了一种关照文化现时性的见证,毕竟用历时性构筑了整体性的文化图景。
但是,问题当然也很明显了,在2008年第七卷之后,再没有看到“中国文化地图”,仅仅七年时间,在辗转不同出版社之后,这个计划便被搁浅——与其说搁浅,不如说最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有了相同性质的出版物代替,或者是资金、人员甚至批评文献的缺乏,总之,当初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后在那个横跨百年的“21世纪”大帽子下消失,不管是无奈还是尴尬,本身就构成了一次文化事件——当它最后被取消了和时间同步的文本,时间就必然会成为一种静态的记录,在若干年后打开,除了闻到浓浓的旧时气味,到底还剩多少必然的坚守?
我当然无异于对此进行讽刺,而其实,当这个计划被冠以几乎看不到时间边际的“21世纪”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谁能成为永远的在场者?谁能保持一种统一的风格构建中国文化版图?——不是谁能一直继续这个计划,而是谁永远会在场?冒险是对于时间变异的一种茫然,而当初雄心勃勃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并非是没有估量到这样的风险,实际上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到底如何构建现时意义的文化批评?构建是需要寻找一个基点的,而这个基点便是新世纪,2001年是他们出发的原点,过去的一切都可以看成是进入这个起点的背景,而未来则是他们行走的方向,所以在第一卷的扉页中说:“编选立场更倾向于民间和自由个体,突破传统年鉴体例,展现出更为开放和前瞻的状态,是一本民间的重大文化‘采风’备忘录。”为了展现开放和前瞻的状态,就必须进入到时间内部,而在第二卷相同位置,这种态度更为明确:“编选者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文化事件’的经线,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而‘批评文选’则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
文化地图中有“文化事件”的经线,有“关键词”的纬线,有“批评文选”的标高,有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的坐标,如此,时间被格式化了,然后突入这个格式的时间里,便可以到达现场,便是一种在场。在场的身份认同除了能突入现场之外,重要的是带着何种立场突入——或者这个问题可以变成:为什么21世纪一开场,我们就需要突入现场?《前言》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从庞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中分裂而出,经历剧烈的动荡和改组,分化为诸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立场、利益份额以及话语方式的群体。这些变化为21世纪文化话语形态及文化批评勾勒出混乱的轮廓,也为新的话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不是以2001年起始时间为原点,而是回望的目光再向前,延伸到一个具有某种症候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像是西方所谓的“世纪末情结”,这是一个转折期,也是一个萌芽期:知识分子内在地进行了蜕变和分化,他们在剧烈的动荡和改组之后,出现了不同价值、不同立场、不同观念的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类,一类是学院官僚主义,它是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是国家主义在新文化格局中寻找到的知识代言人,他们是学院精英,掌握着主流话语权,在学术官僚化中,他们触发了道德腐败,在陈腐的学院体制下,创造力出现了衰退;第二类是媒体消费主义,它是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批评群体,没有重建国家理性的雄心,却在商业利益支配下展示了消费时代的奇妙景观,即使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恶俗与鲜活、谄媚与攻击性、敏锐和失察、反应快速和用过即扔的特性”,也无法真正建立“公民社会”这一批评空间;所以真正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类身上,那就是网络游击主义,它是以网络为阵地,敌视学院批评,也对媒体批评构成为威胁,当它们逐步融入日常生活表现了咖啡馆里的当下性,“网络批评为自由言说体系开辟了未来道路。”甚至在互联网时代的数码语境中,它们逼近了哈贝马斯的梦想。
学院官僚主义者、媒体消费主义者和网络游击主义者,是三类不同的观念群体,当21世纪真正开启,新的时代似乎正扑面而来,而构筑中国文化地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在三种观念群体中找到真正的文化批评,他们将之称为“民间文本”,称为“独立叙事”:“建构批评者敞亮的独立叙事以及自主的话语权,正是本书编撰者的基本理念。”民间的、独立的批评话语,是相对于官方的、国家主义的层面而言的,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民间文本,如何具有独立叙事,似乎是模糊的。在前言中,对民间的阐述是:“民间是国家主义领域的边缘地带,也是非国家主义话语诞生的主要语境。一个健康的理想化的民间话语体系的构架应当是:以民间资源为基础、民间团体为核心、民间话语为主要言说方式,并成为公众发表言论和采取公益行动的话语形态容器。”什么是民间话语?它在解释时却又强调了“原创性”:“在保持了话语的原创性以及批评家个人独特风格和原创意识的同时,它们比较明晰地表达了独立的非国家主义立场。”原创性和原创意识似乎是一种话语风格,而立场必须是“非国家主义”的,所以这种含混性和模糊性,在具体界定上却陷入了某种矛盾:“民间是否意味着一个道德完美或话语优越的空间?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民间知识分子?一个学院里的教师和国家公务员究竟是不是民间知识分子?或者说,使用了民间话语的是否就应当被视作一个民间知识分子?”
如果参考“关键词”条目的注释,这种矛盾性会更加突出。“民间写作”条目将其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民间写作强调肉体化的感受,反对沉思和理性,语言倾向于口语化,而且多出现中国人名,甚至是自己的熟人——狭义的民间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面,“知识分子写作”条目这样注释:“20世纪90年代初由一般诗人首先提出。主要意思是主张写作的纯粹性和独立立场,强调理性和批判性。近年来开始风靡诗歌界。其特点是:耽于沉思和冥想,经常出现一些理性的格言和不乏机智的反讽,语言比较欧化。”当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仅以理性与否、风格是口语化还是欧化作为区分标准,显然是一种表象,它们都无法真正抵达独立叙事的立场,所以“民间文本”更在于广义的定义:“指在官方文制度之外的写作,或者是写作者带有较明显的民间立场,或者是在其作品中有较浓厚的民间色彩。”
其实一样是含混不清的,官方制度之内文化就没有独立写作的立场?那些撰稿的王晓渔、赵毅衡、崔子恩、孙昌建、尹鸿就不是在官方制度之内?甚至朱大可、张闳就独立于体制之外?民间的歧义性其实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体现,它真正对抗的是一元化的价值体系,是逻各斯中心意义的叙事立场,是偏隘、机械、专制式的文本写作,他们所努力的就是构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宽容、多元甚至民主化的写作立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不存在口语化和学院化的界定,不存在原创性和经典化的对立。所以选用的批评文选,既可以是如张闳《革命的“灰姑娘”》中对《青春之歌》的林道境身份隐喻的考察,“其父系血统为官僚地主阶级,其母系血统为农民阶级。林道静的这一出身上的双重性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是对知识分子政治身份之双重性的暗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上的双重性,意味着其在血缘上与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可以如王晓渔在《诗歌公社的生产美学》中,对那个特殊时代的大批量民歌创作看成是“生产美学”的实践,“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放松对它的管制,而是顺理成章地将这种‘生产美学’纳入‘共产主义文艺’的谱系之中。”既可以像南帆一样解读摄影制造的“身体叙事”,提出视觉与享乐的关系背后是不是有权力的隐喻,也可以如杨小滨考察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的城市空间后提出了“作为幽灵的后现代”观点,“80年代的文化英雄或又化异己者被商业社会所无情唾弃之后,诗作为政治社会的出色换喻,失去了传统的光晕,而诗人也不再扮演先知的角色。”
关于《上海宝贝》一书所折射的“殖民心态”,关于电影《大腕》指涉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财经政治事件和风尚,关于行为艺术里对强权和奴役的“强迫症”式解放,关于中国摇滚中掺杂的大众和个人的想象,以及商业广告所折射的口香糖和爱情的欲望象征、杂志在封面女郎凝视中的面容“形而上学”、以色情面貌出现而进行反色情的黄段子,以及家乐福透出的经济学语法,从文学到艺术,从媒体到时尚,各种批评文选大致都在实践着这样的多元性表达,他们都“突入了文化精神的现场”,力图勾勒出时间意义之外的观念历史。但是总体上而言,对于民间独立性的含混定义,更多可以看成是一种扯大旗式的宣言,而在内文的选择上,也的确暴露了如“21世纪”这个时间定语带来的冒险性。
批评需要的是立场,是观点,是尖锐性,是创新力,而其实,里面很多文章偏离了这个标准,崔卫平关于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录影力量”》基本上是事件叙述,陈丹青的《多余的素材·邱岳峰》基本上是人物评述,毛尖的《在电影中制造香港》基本上是散文笔记。这或者只是风格上的一种软化,而当初在前言中说到的“网络游击主义”看成是民间文本的一次前沿试探,但是在两卷本里很少看到来自网络的原创性批评文章,也许在2003年之前,中国网络文学和网络批评尚处在初始阶段,那种所谓的数码叙事更多是表面的热闹,更多是行为方式上的颠覆——而在2019年的现在,更是在主流价值中失去了其应有的多元性。而对于网络事件,更多的内容出现在关键词里,比如【XP】:“XP继续着中美有关知识产权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比如【“翠花,上酸菜”】:“引号内的‘翠花,上酸菜’必须是一口土得掉渣的东北话。比如BT下载、PS、板砖……
网络游戏主义是缺失的,而一开始就批评的学院官僚主义其实在所选的文选中,还是有许多存在的影子,它们以精英主义的俯视方式来看待各种文化现象,看起来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批评,实际上本身就代表着权力,而陆兴华在一篇名为《这种纯文学不是文学》的文章中,似乎就指出了这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他举例残雪的《究竟什么是纯文学?》里亮出的观点,纯文学属于“深刻”的作家,但是这种深刻在他看来,是“虚无缥缈的,无限制的深入,向着虚无的突进,谜一般的永恒,为着人性的完美默默地努力……”还有格非,在《经验、真实和想像力——全球化背景中的写作》中,“里面竟也在沾沾自喜地用那些不知所云的大词儿抖搂他的纯文学伟大工程”。而陆兴华提出的观点是:“不是我们被文学,是我们要去文学。没有作家来给我们操办文学,那我们往往也就自己动手了。”
这种自己动手的观点在陈晓明的《超过图像霸权的文学书写》中也有指涉,他指出:“文学现在真正是回到自身,不回到自身都不行。它不再是工具,正如它也不再能充当号角或火炬一样。现在,文学以它对书写传统的忠诚,对文字的敬畏与虔诚,它倒认真而坦诚地扎根在故乡的土地上。”所以在他看来,文学书写就是还乡的书写,就是最初也是最终的书写,只有自我回归才能找到文学的未来之路。一样是回到自身,一样是破除写作的工具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对于文化批评方向的一种表达。
21世纪、中国、文化,这些太重的词就这样压在那一幅小小的地图上,文化何为?文化何去?从来没有定论,也无需定论,它在自己的方向里,在自己的时间内书写,所谓历史,真的只有在时间内部才可以成型,那种主观式的突围,那种自负式的颠覆,那种精英化的掌控,即使突入到了现场,也只是在戴着口罩的化装舞会上,在变异、遮掩中制造了一种病态,就如朱大可对SAS时代疾病美学的解读一样:
口罩美学的这种进化转移了我们对萨斯美学的拷问。口罩不过是身体的服饰体系的一种向上的延伸而已。它填补了在帽子和衣领之间的空白。它并没有超出寻常服饰的命运,也就是未能超出时尚和模仿秀的大众文化限定。它甚至切断了传统疾病美学(丑学)与皮肤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