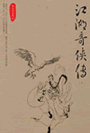 |
编号:C27·2160421·1291 |
| 作者:平江不肖生 著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62.00元亚马逊17.70元 | |
| ISBN:9787540766245 | |
| 页数:1027页 |
“至此书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固为不肖生之能事。”在文学与武术上均有深厚造诣的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中国武侠文学中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物,一生共著有武侠小说十二部。1922年,应世界书局之约开始专心从事武侠作品的创作,而《江湖奇侠传》是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处女作,书中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争赵家坪为引子,以昆仑、崆峒两派的恩怨纠纷为主线,围绕“侠”字,写出了多位剑侠的传奇人生与精彩事迹,并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正义必胜邪恶的观念,使得“侠”的精神初露苗头。本书首开武林门户之争的写作范式,对后世武侠创作具有深远影响,《火烧红莲寺》、《投名状》等影视作品,均以本书为滥觞,更增添了本书的魅力。
《江湖奇侠传》:写不尽的奇人奇事
江南酒侠复说道:“便在你们二派之中,也何尝不有死伤者。试想,修道是何等艰苦的一桩事,不料,经上了不少年苦的修炼,却为了这么一件不相干的事,而受下了伤,甚而至于死了去,这又是何苦值得呢?”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谠言严斧钺》
把争斗当成门派的劫运,并非是因为在打打杀杀中使门派之间陷入不停歇的死亡,而是在介入平民百姓的矛盾中,违背了修炼的本意,甚至破坏了所谓的“道”,所以当江南酒侠的水晶球上现出未来的征兆,便劝说各派退出争斗,重新回归到江湖的格局中,实际上,水晶球无非是江湖和民间的两种现场的分界标志,正如江南酒侠的意义,是“挽回这个劫运”,是将“一切都消灭于无形”,是干了“一件大功德”。
像是一次对于“道”拯救。本来到了打赵家坪的日子,无论是昆仑派还是崆峒派,都把这种民间的争斗当成是“天地大的一桩大正经”,所以双方在摩拳擦掌中各求制敌取胜之道,也想把自己的奇绝武功展现出来,但是在两派俱伤的结局面前,所谓江湖其实已经乱套,一年又一年,消损的不仅是各派个人的精力,也对于门派本身来说,也是违逆于道。水晶球上到底出现了什么,而使江湖遭受劫运?那里是赵家坪事件造成的死伤惨状,那是“水陆码头”之争出现的流血悲剧,而上面映照出的主人则是那些平江、浏阳二县的农民,也就是说,这本是两地农民之间的决斗,是无关江湖恩怨的,而正是因为两派介入到其中,使得争夺赵家坪变成了门派恩怨,而这种恩怨对于两派来说,陷入到一种无穷无尽、“等待明年再来”的循环中,也就是江湖规则屈从于民间规则,而这种屈从看起来更像是盲从,正如江南酒侠所说:“须知道,平江、浏阳二县农民的年年打赵家坪,已是极无聊的一桩事,你们以极不相干的人,更从而助甲助乙,也年年地帮着他们打赵家坪,这更是大无聊而特无聊的了。”
大无聊而特无聊,这是江湖门派对于这场农民争斗的定义,所以在违背了修炼的本性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争斗中退出来,水晶球的幻象归于沉寂之后,现出的十二个大字表明了这样一种“无聊”的状态:“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退出其实是回归到原则,那就是江湖的意义在于修炼,而不在于争斗,在于保存门派的尊严,而不在于介入民间疾苦。水晶球是划出了一个终点的标记,这种退出的想法看起来是为了凸显江湖的纯粹,是为了各自的修炼,而其实,更像是一种避世思想。
“巨干盘空,奇枝四茁,豪情侠态,跃跃纸上”,这是赵苕生对于《江湖奇侠传》的一种概述,不管是豪情还是狭态,最关键的是“奇”,正是这种奇,才显出江湖人士的本性,也显出真正的门派不参与俗世的态度,所以在平江不肖生“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的故事里,起着重强调的是“奇”,奇事、奇人、奇功,在他看来,奇是江湖最本质的特点,一开卷所写的柳迟,就是一个奇人,长到四岁,几乎都是在病中度过,甚至好几次已是死了过去,到了五岁也不能单独行走,而且柳迟的相貌奇特:“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个一字;两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时候,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着了,睁不开来;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替他洗涤干净,无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开眼见人;两颧比常人特别的高,颧骨从两眼角,插上太阳穴;口大唇薄,张开和鳜鱼相似;脸色黄中透青;他又喜欢号哭,哭时张开那鳜鱼般的嘴,谁也见着害怕。”
也正是这种奇特的出生和成长,让他契合了江湖的特性,七岁的时候猛然发现他能把《论语》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过了两年,练成了奇特的本领,凡是在一起的物件,只要被他看见,能够一个不差地说出来,而且他还不愿和小孩一起玩,只喜欢和六十七岁的老头子亲近,他在和叫花子在一起三年时间,就拥有了背上驼七个袋的资格。柳迟无非是一个标本,出生之奇,性格之奇,经历之奇,奇奇怪怪的最后便是孑然独立,超然于俗世之上,对于他来说,现世中的规则不适应他,所以他具备了超越民间的特点,所以与家人不辞而别,寻找得道之路,四处拜访高手,而在他看来,高手的唯一特点也是“奇”。
奇是一种反叛,是一种独立,当然,当告别了现实生活,奇的更大意义在于拥有超凡的本领,所谓奇高的武功,变成了江湖的一个标配。柳迟在千辛万苦中奇遇了黑茅峰调鹰的老者吕宣良,并拜他为师,而吕宣良送给他的一本书就是《周易》。奇特出生、离别父母,其余高手,获得秘籍,在柳迟的身上,平江不肖生建立了一种“奇侠”的标配,而正是这种标配,江湖世界才渐渐打开了。不管是放牛童解清扬的千斤闸武功,还是智远师傅“八百罗汉先期白日飞升”的功行,都让江湖世界涂上了奇幻色彩,也使之脱离了现实的平庸。
 |
| 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的“奇”葩样本 |
拥有奇绝的武功,到底是什么目的?当初柳迟在清虚观拜笑道人为师的时候,就说过是为了“于野老之中能见至道”,那么什么是“至道”?柳迟没有详述,他只说了一句“超拔弟子,脱离苦海!”超拔当然是针对俗世而言,苦海也当然是没有修炼的人才有的宿命,所以至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告别人世的种种困境,包括生死,包括贫富,其实从柳迟的出生来看,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苦海“感受,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奇幻世界的追求,所以当平江、浏阳两县县民争夺赵家坪之事发生之后,当昆仑、崆峒两派弟子助拳争夺赵家坪“水陆码头”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则是找到了一种介入的机会,找到了苦海的缘由。
所以,赵家坪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奇幻的江湖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以现实事件为线索,才能凸显江湖修道者的意义,也才能从中达到“脱离苦海”的目的。所以江湖并非只是天高皇帝远的世外,它必须介入现实,必须制造困境,也必须从中寻找到机会。赵家坪是起点,延伸出的是善恶对立,是报仇雪恨,是门派之争,而所有这一切,在现实的铺垫中也隐约拉出了那一根“道”的线索。
现世是混乱的,混乱之中当然善恶对立,而奇幻的江湖中,自然也有善有恶,有超越的高人,也有迷恋世间的恶人。周敦秉学了道术,却并没有用在正事上,却年少风流,“湘潭有名的娼妓,他十九要好”,于是所谓的采补功夫,只不过是用来勾引女人,而且还是那些娼妓;道士潘道兴略通的是邪术,会几手拳脚功夫,却性情凶悍,他不仅在赌场里作威作福,而且和毛氏通奸,当淫荡之事被毛氏丈夫的母亲撞见,两个人又用邪术设坛诅咒四十九日,拔出了眼中钉,而毛氏更是恶毒,竟将死去的婆婆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然后“翻尸倒骨地弄了一会,用符水炒热许多铁菱角和川豆子,盖在尸骨上面,仍旧埋好。”为的是不让她的鬼混半夜来骚扰。还有笑道人的徒弟戴福成,也是讲目光对准曾经恋着的妓女,而且在学了法术之后所贪欲的那些钱,为的是“快乐快乐”。
最著名的当然属于“火烧红莲寺”,那一个红莲寺,表面上看是无垢和尚募化银钱而盖造,但其实是盐枭张汶祥拿出钱来修建的,木器也是“为他自己将来下台地步的”,所以在这个看起来清净之所,里面的肮脏勾当却无处不在。张汶祥和郑时平时杀戮官府,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当看到仇家的女儿时,也不放过,不想乱娶柳氏姊妹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他们从马心仪那里骗取了官职,却又受制于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被马心仪所占有,甚至光明正大在他们面前行淫荡之事,郑时本也是个好色之徒,将仇人之女骗做老婆,不想却被马心仪霸占,想要报仇却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而马心仪在最后逃路无果的情况下,竟然在遗嘱中将柳氏姊妹处死,因为他的罪行若被揭穿出来,清廷必认为他死有余辜,反倒被张汶祥得了一个义士的好名声。
不管是道士、和尚,还是官员,似乎都在沉溺在欲望世界里,所以那种恶自然受到了报应,而对于恶的报应自然是所谓的德行,所谓的道,周敦秉用道术行恶之事,他的师父智远和尚对他的惩戒便是七星针:“居士此后如能确遵令师梦中的训示,一意修持,贫僧愿助一臂之力!若眨眼就把那训示忘了,这番即算保得住性命,搽以后随时随地,皆难免不再有七星针飞到居士背上来!”而戴福成之事被揭露之后,笑道人对他的告诫是:“道家其所以需用法术,是为救济人,以成自己功德的。是为自己修炼时,抵抗外来魔劫的。谁知你倒拿了这法术,下山专一打劫人的财物,造成自己种种罪过。”所以将他的道术尽废,让他重新开始做人。而红莲寺的罪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一把火烧之,而淫荡的潘道兴,最后则死在了欧阳后成的枪口下。
“你此刻拜师,须拜受师傅的戒律,发誓遵守。第一戒妄杀,第二戒窃盗,第三戒邪淫,第四戒酗酒……”这是后成的师父方振藻提出的戒律,而其实这只不过是对于徒弟的一种表面功夫,当后成问:“师兄屡次犯了,侮么却不灵验呢?”方振藻便说:“我发的本身咒,是一辈子也不会灵验的。因为我当日发的誓,是倘若犯了戒,就得死在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手里。我的道法,休说未成年的小孩不能制死我,我敢说当今之世,没有能死我的入。我怕甚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道具有双重性,对人的约束和对自己的规范,完全不在一个系统里,而遵守或者破解的唯一标准,就是谁的法力高。所以昆仑和崆峒介入到赵家坪之争,更多的只是展示自己的道术,和正义无关,甚至两门派之争,背后还有更大的觊觎者,哭道人的徒弟赛半仙就设下计谋:“如今我们要想个法子把这昆仑派灭了去,不但是把昆仑派灭了去,并连这崆峒派,也要使他们同归于尽。”
所以奇绝的江湖无非是道的江湖,甚至只是道术的江湖,所以所谓的“江湖奇侠传”对于“侠”的定义基本没有涉及,只是偶然提及,比如甘瘤子作为强盗,和绿林强盗有分别,他们有许多禁忌,其中之一便是不是见钱都要:“读书行善的,和务农安本份的人家,不问如何富足,他们也是不去劫取的。有时不曾探听明白,冒昧动手劫了来;事后知道劫错了,仍然将原物退回去。平日所劫来的财物,总有一半,用在周济贫乏上头。”所以江湖上称他们这种强盗,也加上一个侠义的名目。强盗是侠义的强盗,而罗慎斋的脾气里,“生平第一厌恶的,就是贪官污吏”。方绍德收卢瑞为徒的时候,就告诫他“不许干预国家政事”,“我这道法,传自佛家,佛家是不许干预国家政事的,那怕昏君临朝,奸臣当国,我门下的弟子,永远不许有出来干预的事。”这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遭到了吕宣良的反对,他对柳迟说:“我们修道的人有什么国?有什么家?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谁的事不可以干预。”
对于国家政事的干预,当然是入世的做法,吕宣良认为修道的人干预国家之事,重要的是事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而不是针对某个人,这样的标准在善恶对立中,也是泾渭分明的,而正是这种泾渭分明,使得人物基本在扁平状态中,程式化明显,甚至所谓的善人和恶人也从来没有感情发展的铺垫,正如里面的笑道人和哭道人一样,分列在两派,争斗也无非是哭和笑到底谁的功力更大,正如哭道人写给笑道人的信中说:“笑之与哭,为极相反之名词,而处于极反对之地位,固夫人而知之。……我二人倘能不藉助于其他法力,而即以此‘哭’与‘笑’二字为武器,相巫见于战场,一较道力之高下,或亦为别开生面之举,而足为一时之佳话,道友傥亦有意乎?”
哭和笑,恶与善,根本不关乎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困境,当然也根本不关心民间的疾苦,所以“奇侠”的江湖是单一的江湖,是封闭的江湖,是技艺的江湖,而在告别了“鸳鸯蝴蝶派”的缠绵故事之后,平江不肖生也树立了江湖规则,善恶对立、报仇雪恨、门派之争以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江湖世界形成了一个样板,而这个样板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其实在开创新风格的同时,也陷入了窠臼,在“写不尽的奇人奇事”的计划中,为了追求奇绝的效果,却把故事的主线埋没了,甚至可以说,小说根本没有什么重点,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在“奇”的指引下,没有多变的性格,没有起伏的故事,往往一条线索即将形成,冒出一个新人,便又开始将笔墨转向新人,而在对新人的叙事过程中,又冒出来新人,便又开始转折,所以人物目不暇接,却几乎没有有血有肉的形象,对此,平江不肖生解释说:“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写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追求奇的效果,放弃了材料的组织和加工,“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
而在106回之后,平江不肖生竟然因为其中国奇人奇事太多而搁笔不写,而后续的赵苕狂基本上沿用了平江不肖生的写法,也是在没有主线的杂乱中书写奇侠故事,而这种只追求一时好奇的效果,其原因竟然是为了“写作换钱”:
在下近年来,拿着所做的小说,按字计数,卖了钱充生活费用。因此所做的东西,不但不能和施耐庵、曹雪芹那些小说家一样,破费若干年的光阴,删改若干次的草稿,方成一部完善的小说。以带着营业性质的关系,只图急于出货,连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没有。一面写,一面断句,写完了一回或数页稿纸,即匆匆忙忙地拿去换钱,更不幸在于今的小说界,薄有虚声。承各主顾特约撰述之长篇小说,同时竟有五六种之多。这一种做一回两回交去应用,又搁下来做那一种,也不过一两回,甚至三数千字就得送去。既经送去,非待印行之后,不能见面,家中又无底稿。每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多至数百,少也数十,全凭记忆,数干万字之后,每苦容易含糊。所以一心打算马虎结束一两部,使脑筋得轻松一点儿担。
带着营业性质,只图急于出货,甚至自己修订审核的时间也没有,连故事中的人物也是虚构了忘记了所以,这或者也是卖文度日的一种尴尬,而在这种功利性的写作中,不仅人物扁平,结构松散,主题混乱,甚至也是对于创作的一种亵渎,就如那水晶球上的“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的十二个字,是劝江湖门派退出俗世之争,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警示,修道是一件苦事,只是为了赚钱卖文,何来为文之道?所以“本书借此机会,也结束了下来,不再枝枝节节地写下去了”也算是对于这样的写作搁笔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