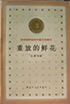|
编号:C29·2160227·1268 |
| 作者:王蒙 著 | |
|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09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30211410 | |
| 页数:354页 |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不同于刘心武的剑走偏锋,也不同于李国文的常规解读,作家王蒙对红楼的解读独辟蹊径,虽不成系统,却也灵光频现,点出了诸多疑团。《王蒙谈红说事》收录了王蒙关于《红楼梦》的文学人生评论文章。在王蒙看来,《红楼梦》首先是一本人生的大书,值得我们用一生经验细细品读,“黛玉开始很乖”、“如果你的老板是宝二爷”、“袭人算不算特务或变节分子”……王蒙认为,《红楼梦》是一个特别好谈的话题,可以借题发挥,可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作补充。所以《红楼梦》不是政治斗争史,不是宫闱秘闻,不是猜谜游戏,它只是一本人生的大书,文学的大书。
《王蒙谈红说事》: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红楼梦》果然是百科全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可以在《红》中找到雏形、例证,至少是可以找到类似参照事物。例如夺权——秦显家的夺取柳嫂子的厨房管理权;智力引进——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小报告与特殊补贴——袭人向王夫人报告而获额外月例;扫黄打非——宝钗劝诫黛玉不要看“少女不宜”的书与绣春囊事件;大小字报——揭发贾芹胡作非为的揭帖,等等。而且《红》中有“包产到户”——著名的探春兴利除弊的新政:——《一四〇 探春搞包产到户》
雏形、例证或者并不需要苦心去寻找,甚至在文本编辑上是显而易见的,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在封面正中央,而这无非是对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本的一次新包装,而新包装对应的是旧酒,此前的版本书名为《不奴隶,毋宁死?》,副标题是:王蒙谈红说事。虽然这次新版版权页上标注着2011年9月为第一版,而翻过那如词牌的封面,里面的篇目却是一模一样,甚至每一单页的页眉上还赫然迎着“不奴隶,毋宁死?”这几个字,加上双页页眉的“王蒙谈红说事”,当单页双页合上的时候,无非又回归到历史——从2008年6月版本到2011年9月版本,从“不奴隶,毋宁死?”到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同样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样是354页,无非是一次简单的翻版。
雏形、例证,当被改头换面的时候,它像新的一样,而回到历史的时候,那页眉仿佛就如爬行的“现实主义”,让人有些不快。还好,这只不过是文本的一个陷阱,没有读过2008年6月的《不奴隶,毋宁死?》,翻开第一页,阅读第一篇,看到第一行,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而当忽视了页眉,抛却了虚无的“不奴隶,毋宁死?”,回到“王蒙谈红说事”,却也看见了里面的人生。算是一种弥补,那雏形和例证倒不必过度解读,在内在的世界里,翻阅到的果真是一个既有阔达终极,又有诗意灵动的现实世界。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王蒙的说法也是跳出《红楼梦》文本的一次经历,从书名开始,便寻找那关于现实意义的雏形好而例证,比如各种书名里,《石头记》是最好的,“石头云云,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也最哲学,同时又最令人唏嘘不已。”石头可以直击宇宙,又可以直通宝玉,既可以登高望远,又可以具体而微,登高望远的宇宙观指向的是哲学命题,具体而微的个体观,则是一个人生课题,所以由石而玉,也是找到了最原始的雏形,找到了最终极的例证。
那块玉,当变成宝玉身上的关键性部件的时候,它是一种重构,构筑的是一个符号,一条主线,一种哲学,一些情节,而最主要的是构建了另一个“自我”,在王蒙看来,宝玉生而衔之的那块玉,就是其物格化的标志,他的命运似乎就是玉的一种象征,而当宝玉戴着这块玉,它又在相反的过程中完成了人格化,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物件的玉和作为个体的贾宝玉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来源于石头,归宿于石头,“贾宝玉的平安祸福都反映到了那块玉上面”,无论是丢玉还是送玉,无论是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互为主体,也互为反射,看起来是一种象征主义,甚至魔幻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现实主义,“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爬行当然是呆板,甚至是静态,它总是缓慢地走上一个统一的路线,走向一种规定的结局,但是在王蒙看来,《红楼梦》的通灵宝玉的意义是开启了一种关于人生的哲学,它是发生学,它是未来学,它是终极关怀,而每一种发生、未来和终极关怀,都和人有关,它是具体而微的,它是平静本初的,它是有雏形有例证的,它也最令人唏嘘不已。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安排一个刘姥姥?进来而出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过客类型,实际上在家族兴亡的大历史中,刘姥姥其实是一个另类的段落,而这种另类在《红楼梦》的家族变迁中,扮演了一个“进步与可爱”的类型,在“越来越有本领、越来越不动声色、越来越尖刻——越来越讨嫌”的主体线索之外,刘姥姥是“越来越可爱”,而这种可爱在宿命的结局中,自然是一种“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在个体人物的分析中,王蒙着眼于那些另类的个体,比如他说妙玉带着极其明显是变态特点,她是排他的,孤独的,居高的和震慑性的,是一种“雅妙逼人”的态度,雅的反面自然是俗,所以她对于俗的痛恨变成了一种变态,“她的变态的特点是自己受虐后变本加厉地施虐于人,干脆仇视一切俗人尤其是劳动人。”而这种变态在王蒙看来,却也是令人同情的,两个世界彼此隔绝,彼此痛恨,到最后却像大家族一样换来宿命的悲剧结果。所以,无论是“宿命地不可理喻地疏离着他人、疏离着家族、疏离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体制的一个”的惜春,还是“过分强势为自己掘了坟墓”的晴雯,都映射着某种现实的宿命感,而殉主拒嫁的鸳鸯,被很多人认为是抗击封建婚姻观的精神体现,为她大唱赞歌,而其实,鸳鸯的拒绝是为了为主子服务,甚至要一身殉主,这何尝不是封建时代的最生动注解,其身上的荒唐和残酷对于那一个现实来说,则是一首无声的挽歌。
这是最现实性的一种体现,所以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雏形和例证所对应的就是一个放大的社会,在事件上,有夺权之争,有智力输出,有特殊补贴,有扫黄打非,有大字报,有包产到户的新政,无不是现实的一种反映,而在情节的演进中,既有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非一日之寒,露出了下世的光景”的长期性结局,也有如金钏投井自尽这种天有不测风云的突发性事件,更有自四十回起“不祥之风渐渐起于青苹之未”的渐进性发展,所谓人情世情,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没有大决战,没有高潮,没有全景的世界里,却依然有命运和现实的大转折,王蒙认为,《红楼梦》真正具有现实主义悲剧意义是从七十四回开始的,傻大姐捡到了一个涉嫌淫秽的荷包,于是便有了搜检大观园,晴雯遂死、司棋自杀、宝钗迁出、芳官等人全部被逐,“这是一次扑杀青春的歼灭战”,当青春不再,便在铙钹齐鸣、鼓号皆响、天翻地覆、雷电交加中开始了大转折,“由吉而凶,由福而祸,由开端与发展而走向结束,由制高点而降落,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而走向下世、没落、分崩离析。”而到了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一个乐极生悲、盛极而衰的过程便已经有了最终的结局,“你甚至会想起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王蒙按照黄金分割点的美学理论,将七十四回放在了分界点上,虽然有些对于数字的过度解读,但也明晰了《红楼梦》大结构的衰败没落。一个家族的盛衰,是现实的折射,而王蒙认为,真正折射的是关于青春自由和放诞的终结。青春和爱情有关,和自由有关,甚至和诗意有关,而青春的代表自然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生活在女性世界里的贾宝玉说出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实际上是将青春做了一次定义,这里是平等,是交合,但是宝玉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虽然他对于封建主流价值体系和教育体系有一种逆反心理,甚至率真、任性、贪玩、笃情,但并非如评论家所说,他是反封建的斗士,“宝玉的反抗性有限,大多以孩子淘气、刁钻、撒娇的形式出现,似不能评价太高了。”实际上这种性格正是青春的典型,唯美主义、同性恋倾向,甚至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淫偶像”,都使他具有了某种自由和放诞的特点,而在这种自由之外,宝玉的“兼容性”也体现得很明显:“他可以规规矩矩地去谒见北静王;他可以乖乖地作贾母的好孙子王夫人的好儿子;他可以与花袭人或不止是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同时乖乖地听袭人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训,像对待自己的姐姐;他可以与黛玉互为知己,心心相印并张扬另类叛逆情愫;他可以与秦钟一见如故,发展准同性恋的关系;他可以与晴雯共同任性而为,胡闹一番;他可以与茗烟一起大闹书房;他可以与众姐妹一起结社吟诗;他也可以与薛蟠、冯紫英、伶人蒋玉菡和妓女云儿等为伍去吃酒鬼混,与蒋玉菡交换贴身汗巾,与他们一起唱艳曲。”
而黛玉,有着强烈的个性,重感情、轻功名,一方面显示其清高,孤独、痴情是其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却恃才、多疑,而这正是将她列入了弱者的范畴,她脖子上没有所谓的玉,她总是和诗歌、泪水、哀愁相伴,她是众姐妹里最单薄的人,正是这种弱者的形象,她“对于某某人出现、居住、享用于这里的合法性问题、资格与身份问题最为敏感,最为在乎”,说刘姥姥是“母蝗虫”便是一个例证。在这种弱势中,她唯有抓住那根爱情的稻草,“她一爱上宝玉就只能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了。”但是,在《红楼梦》里,爱情似乎并非都和青春的自由有关,在黛玉葬花之后,宝玉欲与黛玉交谈,黛玉不理他,而后来宝玉对她说的话却不像是青春的宣言,看起来更像是生活的叹息,什么陪着顽笑啊,好吃的千干净净留下来呀,亲不亲谁谁是外路呀,“完全是低水平语言:无诗情画意,无浪漫情怀,无激情浪花,无火焰喷射。”而这“不像宝玉说的”的表达在王蒙看来,却是爱情世俗化的注解:“呜呼,爱情使人超凡脱俗,使人如人仙界,飘飘然,飒飒然,云里雾里,乘扶摇而上九天,逐星月而迷五色;但爱情也使人变得现实,变得想过好日子,想过董永的而不是七仙女的生活,一句话,爱情使人如此地热爱生活,平凡的生活。”
而最后爱情在惊天动地之外,终落得悲剧下场,其实在彼岸世界里就注明了这种非世俗性的宿命性,子啊太虚幻境中,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之泪的奇绝故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所以黛玉在婚姻问题上深感痛苦,对环境与自己的运气总是唉声叹气,从个性意义上,就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主义,就是弱势者的最无力挣扎。但是在黛玉的孤独和痴情之外,在某些诗作里却有着关于政治的见解,元妃省亲时,代宝玉题诗中说:“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如果说,在王蒙看来,这是黛玉的应景文学代表,那么在“幽淑女悲题五美吟”中,却以古代政治风云中的女性为题,表达了另一种见解,《西施》中说:“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白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这是对于效颦东施的理解与同情,《虞姬》中说:“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把虞姬与汉室被诛功臣的命运放在一起比较,流露的是一种胜败得失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明妃》《绿珠》《红拂》里,也都有关于哲学、政治的观点,所以王蒙发问:“林黛玉怎么了?《红楼梦》怎么了?曹雪芹怎么了?”
或者并非是反抗,只是哀叹,或者并非是政治,只是人生,女人,悲剧,何不是历史在自我身上的投影?何不是情感最终缺失的悲剧预见?何不是青春被歼灭的宿命表达?而在诗歌中寄托情怀终究无法逃脱所谓的现实主义,雏形也罢,例证也好,现实就在那里,绝非爬行,也在伤心、疑惑、悲哀中一步步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