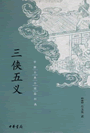 |
编号:C25·2151022·1217 |
| 作者:[清]石玉昆 著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24.00元亚马逊13.80元 | |
| ISBN:9787101093766 | |
| 页数:586页 |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中国一部非常著名的公案侠义小说,此书流传极广,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小说共一百二十回,分成两大部分。书中前半部分主要描写宋代包拯为官期间不畏权势、为民伸冤除害,后半部叙述良侠义之士除暴安良、正气热肠的壮行豪举,不同于一般荒诞神怪的小说,文笔酣畅淋漓,描述精彩,具有较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动人心魄的震撼力量。整部小说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风趣生动,读来令人爱不释手。展昭的宽容忠诚,蒋平的刁钻机敏,徐庆、赵虎的粗鲁憨直,艾虎的纯朴天真,智化的机智潇洒,欧阳春的含而不露,尤其是白玉堂豪放不羁、少年气盛,莫不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直到现今,在影视和戏曲舞台上依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三侠五义》: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
宁老先生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九岁的包公在私塾,只要宁老先生一点《大学》的句断,就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知“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背诵如流,使得宁老先生大喜,留下一句“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师之乐,并不在于包公能将圣贤之书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看见了读书的意义,那就是包公显露了“天下英才”的潜质,甚至可以说,是在启蒙中开启了一种“明德”、“至善”的风范。大学之道虽然在九岁包公那里更多呈现的只是字词而已,“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以后为国家栋梁的素质,所以宁老先生给包公起的官印是一个“拯”字,起的字便是“文正”。
“拯”为拯救,文正而为“政”,这种命名方式,其实已经将包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治世良臣理国政便也成为老师的期望,自我的目标。这并非仅仅是启蒙,一种命名的开始,其实包公之后的人生之路已经走向了“大学”,而这种预言和启示性的命运在某种方面却是对于自身多舛幼年的一种超越。母亲是四旬开外怀孕,已有二子的包员外终日忧愁,而那独坐书斋的梦差点将包公带向人生的厄运,“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梦中的怪物,是打破了本来的秩序,对于父亲来说,此种征兆也是大凶,所以有了后来包海将他抛尸野外,差点落入虎口,而包山的解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兄弟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善与恶,宽容和私狭,渗透在包公的幼年生活里,而到了七岁的时候,包公将救下他的兄嫂呼为父母,这是一种乱伦的称呼,对于伦理秩序的颠覆,其实是对于员外及兄长扼杀生命的否定;而且,包公从小到七岁从未哭过,也从未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
奇异的出生,奇异的性格,奇异的家庭,对于包公来说,的确是人生的变数,也是通向“大学之道”的坎坷,而这种自离娘胎而“天降大任”的考验其实是回应着朝廷的悲欢离合,小说一开始就以八月中秋的天象开始,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那时的宋真宗还未有储君,所以这天象的吉凶自是一个未知数,而真宗那句“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却将刘妃和李妃的命运,以及太子的命运也推向了变数,“狸猫换太子”宫廷争斗衍伸出的是关于君主的坎坷和折磨,也正是这种包公和仁宗波折中的共同点,让他们的命运契合在一起,也为后来仁宗重仁重义的明君形象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种呼应,呼应的目的就是为狭义文化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大背景。而包公在个人成长中,也逐渐开始了从江湖到庙堂的人生之路,从读书到中试,再到成为定远县知县,也是一种儒家式的成才之路,而“乌盆诉苦别古鸣冤”虽然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但是却是包公进入圣上视线的一种捷径,正直无私,断事如神,却越过了上司之嫉,直接呈现在皇帝面前,终于升任为封府府尹、阴阳学士。“阴阳”二字的意义是善于“白日断阳,夜间断阴”,是对于他判案神奇的一种说话,而在小说中也慢慢神化了包公。如果按照史书记载来看,《宋史·包拯传》只记载了他的一件断案故事:“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立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如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是,在小说中,包公不但能审民间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而且能断阴阳,审冤魂怨鬼,“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及清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包公被塑造成了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神人、法师。
这种神通广大其实是一个铺垫,一来符合自己那个“拯”字的含义,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来,也是为了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国理政的理想,才能完成宁老先生当初对于他人生之路的一种命名。而第18回《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就是将那一段“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后大白天下,余忠替死、送往陈州、开封府净室居住、李氏诰命叩天求露等沉疴细节一一展露,而包公在其中不光是历史的揭露者,也成为亲历者,包公认假母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最后利用虚设的森罗殿,终于导致郭槐招供,当初刘后图谋正宫、用剥皮狸猫换太子、陷害李妃,等等,都变成了呈堂证供,也终于将历史冤案昭雪,而随着将郭槐立剐,圣上也最后宣召包公:“刘后惊惧而亡,就着包丑卿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
包公将沉冤多年的宫廷争斗大白于天下,就是真正走进了庙堂之上,将个人命运维系在皇权至上,这是一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道路,对于包公来说,是成为治世良臣的开始,是行使治理国政的起点,也正是仁宗是仁义之宗,才使得包公能够在超越自己出生多舛命运之后,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在“在明明德”中行侠仗义。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都是把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和弘扬人间正气、除暴安良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完美的结合其实走过了两个过程,一个是从江湖到庙堂,而另一个则是从庙堂到江湖。
除了包公的命运和皇权联系在一起,三侠五义的狭义思想也是在仁宗的认可下得到展现,而他们也从一般的江湖义士变成了朝廷命官。南侠展昭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功绩累累,当初他的侠义观其实是个人随机式的遭遇,“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只是将别人的悲喜当成是自己的安危,这是纯江湖的侠义,但是后来经过包公举荐,被皇上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绰号“御猫”,才成为和国家命运有关的侠士。
在三侠五义里,锦毛鼠白玉堂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当初经过包公的举荐,仁宗金殿试艺的时候,只给了“三鼠封官”,卢方等三人授予的是六品校尉之职,都安排在开封供职,实际上都成为了朝廷命官,仁宗而又传旨,“务必访查白玉堂、韩彰二人,不拘时日”。也就是说,在仁宗眼里,充满的是一种宽容心,是一种招贤若渴的仁义。白玉堂,因少年华美,气宇不凡,行侠作义、文武双全,但是白玉堂的性格,具有多个侧面,也是五义中最为复杂的。他少年气盛,性情高傲,闻听展昭受封“御猫”,便觉“五鼠”减色,遂专程赶赴京师与展昭一比高低,先于皇宫内苑中杀了意欲谋害忠良的总管太监郭安,又于忠烈祠内狠狠地戏耍并整治了奸太师庞吉;他与有志有德的贫寒书生颜查散结为兄弟,并为其鸣冤,多方救助;最后,为探谋反朝廷的襄阳王的虚实,三闯冲霄楼,疑似命丧铜网阵。
正所谓以英雄侠义始,以英雄侠义终,所做之事,均系无法无天的惊人之举,又都不离“侠义”二字。但是从一开始的经历来看,他的侠义是完全建立在自我基础之上的,不喜欢展昭受封为“御猫”,一个“御”字仿佛是将那种侠义的个性抹杀了,所以他极不服气,内心的渴望是自由,但是蒋平对白玉堂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五义的一种转变,“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忠义祠题诗,万寿山前杀命,奏折内夹带字条,大闹庞府杀了侍妾。你说这都是是人所不能的。这原算不了奇特,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黑夜里无人看见,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这如何算的是大能干呢?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也就是说,蒋平所认为的那种江湖行为只是小打小闹,不是大能干,不是大世面,只是凭着飞檐走壁之能,血气方刚之勇,实际上是不懂规矩,甚至破坏规矩,所以“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充其量只是一个浑小子,甚至没有资格上开封府。
什么是大世面,“若是见过世面,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过天子升殿。……慢说天子升殿,就是包相爷升堂问事,那一番的威严,令人可畏。”天子升殿是大世面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直接否定了白玉堂的个人侠义,直接否定了鲁莽江湖,最终从江湖之远而转为庙堂之高,所以少年英雄最后得到了仁宗迟来的赏识,传旨:“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即着白玉兰堂补授,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辅弼。”而这也就意味这三侠五义都已经完成了一种庙堂式的命名,也和包公一样,可以真正拯救人民,可以治国理政,可以成为治世良臣。
而当居庙堂之高之后,这些侠义之士进入的另一个江湖就是自上而下的江湖,所以他们面前的任务也变得更为重大,那就是要清除最大反派襄阳王的势力。襄阳王,是真宗幼弟,宋仁宗的叔叔,他意图勾结江湖人士邓车、张华、马刚、马强、雷英等人,朝中的庞太师及其党羽,还有蓝骁、钟雄、邬泽,立下盟单兰谱放在冲霄楼中,意图谋反,颜查散上任襄阳,带领三侠五义众位英雄剿灭叛乱,为大宋的安危、人民免于战乱做出卓越贡献。在小说中,为了拿到襄阳王造反的证据,锦毛鼠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命丧铜网阵,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大宋的安定,而这便是侠义的体现。在小说中,群雄战襄阳其实并未真正展开,在第一百二十回中说:
这便是《忠烈侠义传》收缘。要知群雄战襄阳,众虎遭魔难,小侠到陷空岛、茉花村、柳家庄三处飞报信,柳家五虎奔襄阳,艾虎过山收服三寇,柳龙赶路结拜双雄,卢珍单刀独闯阵,丁蛟、丁凤双探山,小弟兄襄阳大聚会,设计救群雄;直至众虎豪杰脱难,大家共议破襄阳,设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计扫除众寇,押解奸王,夜赶开封府,肃清襄阳郡;又叙铡斩襄阳王,包公保众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辞官出家,白玉堂灵魂救按堂,颜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师闻报哭双侠,众英雄开封大聚首,群侠义公厅同结拜:多少热闹节目,不能一一尽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义》书上,便见分明。
“活捉了襄阳王”成了续集,但是在小说中,从江湖到庙堂,再从庙堂到江湖的侠义世界已经建立,所以作为一种铺垫,那种大场面等待展开,而随着大场面的展开,拯民于水火之中建立的“在止于至善”和治理国政的“大明明德”也便成为侠义文化的最好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