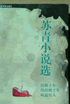 |
编号:C27·1960728·0315 |
| 作者:苏青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5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3.80元 | |
| 页数:530页 |
说起苏青,总与另一位女作家联系在一起,两个海派的女作家在旧上海曾红极一时,但苏与张显然有着很多的不同,尽管在离开人世时一样是寂寞的。在小说创作中,苏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小说就是她自己的生活,而张则站得更高,客观一点,冷静一点,这也造成了苏青小说所表现的题材相对狭窄。形容苏青,也许那一篇小说的题目更确切:《歧路佳人》,破裂的家庭、多难的政治经历几乎将苏青以后的小说创作扼杀了。1982年,苏青离世,悄悄静静。
我的薇薇,我是要永远保护她的,假如不能够了,我希望她能自动选择一个可信托的人,永远过着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只与她的丈夫两个人–那丈夫也许不像贤,而是像其民吧。
—《结婚十年》
保护年幼的孩子,保护没有了父亲在身边的女儿,并且希望她能够选择一个可以信托的人,过一种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这是对孩子未来生活的期盼,但也是一种对自我过往的无奈。对孩子的所有爱,对女儿以后生活的向往,都是建立在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生活之上,仿佛自我的牺牲一定会换来明天的美好生活。
“我”对于孩子生活、爱情甚至婚姻的构筑,无可避免带有自己的影子,甚至“不像贤,而是像其民”的范本,就是自我错失的那种爱,两颗樱桃的故事变成记忆,沉淀为青春所有的美好,但是,两颗樱桃已不再,那个说出承诺的其民已不再,甚至自己渴望拥有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已不再,那种对孩子寄予希望的未来,也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我”和薇薇组成的母女结构,这种母女结构反衬出现实的无情,更是在女性/男性之间划出了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诉请的小说创作几乎就留下了《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和《歧途佳人》,而《结婚十年》作为一个起点,很明显只是一个女人的哀叹,对于“我”来说,对面是丈夫,是丈夫背后的公公,是丈夫、公公以及一切家庭规则背后的男权体系,在这样一种传统结构中,作为女性的我,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薇薇这个未来女性身上,也只是一种臆想。《后记》中苏青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宿命,或者是女人的宿命:“我相信她以后仍旧不会好的,生在这个世界中,女人真是悲惨,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这是环境逼着她如此。”
环境逼迫,女人的命运无疑呈现着一种牺牲状态,“我”十八岁出嫁,那个希望带给我幸福的男人甚至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只不过是在信件中建立了脆弱的联系,而结婚更像是一种游戏,在婚礼上甚至找不到丈夫贤,“我”只能发出“我的房间在哪里?我的新郎又在哪里呢?”的疑问。丈夫是缺失的,是作为保护女人的男人、和女人亲亲热热的男人的缺失–而且贤似乎还和寡妇瑞仙打情骂俏,所以“我”的另一个疑问是关于自己的身份,“也许他们俩要好早在我们结婚夕前吧!是她在事实上占夺了我的丈夫呢?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无论是“我的新郎在哪里”的询问,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我”都在这决定自己一辈子的事情面前被抽离了,但是,“我”却又是脆弱的,所有的疑问似乎只是在自己内心里,“我”甚至不敢张开口。
所以,“我”作为一个结婚的女人,既要忍受丈夫的缺席,又要接受妥协的命运,无论是他救还是自救,都没有充足的勇气,都没有过人的胆识,“我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观念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所以“我”这样一种命运,也是女人自我定义之后的宿命必然。但是“满肚子都是新理论”毕竟还是给了她一点点的勇气,在无法忍受家庭生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是离开,“好吧,我明天动身赴校以后,恐怕此生再也不会回来了,今夜就算是你们替我送行。”一杯酒下肚,便壮起了胆,离开去学校,是自由的开始,甚至想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那就是“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然后在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的融合中心心相印,而认识应其明,是“我”走向自由的第二步,即使有着“我是结过婚的人”的担忧,两颗樱桃的柔情又化解了这一切。
但是只是生命中出现的一瞬,当“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而且就是贤的孩子,似乎一切的憧憬都消失了,回归家庭回归丈夫,是因为肚子里怀有的是丈夫一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对于女人来说,这是身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切断了关于自由、关于幸福的向往。回归家庭回归丈夫,其实就是回归男权,公公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或者承德或者仁德或者怀德,“德”字的世界,就是注解了孩子是“孙子”的预设,一种传宗接代的思想,一种重男轻女的传统,明显就是把女性又放置在从属的地步,“我”的命运如此,下一代的命运何尝可以被轻易改变?而“我”似乎也失去了当初离开的勇气,没有了两颗樱桃的向往,当把希望寄托在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时候,“我”内心是有某种反抗的情绪,“归宁”的那天,母亲对“我”说:““儿呀。委曲些吧,做女人总是受委曲的,只要明年养了个男孩……”而“我”挣脱母亲的手,心中的一句话是:“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去找工作,为的就是“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
“我”的女性意识是微弱的,当初的离开寻找自由生活是一种追求,和其民沉浸在两颗樱桃的浪漫中是一种实践,不想养男孩要自己找工作,是一种自我的觉醒,甚至想要读书不想成为所谓的少奶奶也是一种成长,但“我”根本无法摆脱那种束缚,根本无法成为独立个体,根本无法真正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三个月的小学教员生活很快结束,在余白的鼓励下投稿又被贤指责,而当贤说要去上海自己又只好跟着丈夫,“抛别了亲生女儿,抛别了娘,抛别了一切心爱的物件,跟着一个生疏的丈夫到上海来,前途真是茫茫然的。”即使如此,也在贤“时时,刻刻,月月,年年,永远同我在一起”的承诺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在上海似乎是慢慢独立,“我”承担了家庭琐事,而贤开了法律课,之后又开设了事务所,“我”之存在,似乎还是贤的附庸,甚至在接二连三怀孕中,真正起到作用的依然是“我”的那一个身体–贤不让“我”投稿成为知识女性,甚至不让“我”和文字接触;贤不许我倾听男人谈论国家形势,“他的意思是女人应该无意于此类的,假如她越装出不懂的样子,她便越显得可爱。”
后来上海的战乱,又使得全家回到了乡下,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对于“我”来说,乡下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忍受,“乡下有的是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以及平凡得无可再平凡了的田野……”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感觉就如飘零一般,而带着几个孩子的生活彻底将“我”的独立意识全部抹杀了,那个二十一个月的女儿最终死去,非但在战乱的局势下“母亲”这一身份变得不完整,而且让“我”对于未来更多了一种惶惑–又怀孕了,“我”几乎成了生产工具,甚至连贤也有了意见,“说我这种女人真是碰不得,动不动就受胎,下等动物是顶容易繁殖的,难道不听见人家说:好花不结子。”把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看成是“下等动物”,就是把“我”完全变成了身体意义上的存在。
“我”变成生产工具,变成下等动物,女性的独立意识其实已经荡然无存,“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个羞涩转过脸去叫我“妈妈”的薇薇,那个拿了手帕玩具总要跟着我的菱菱,那个眼睛乌溜溜医生拍了两记才哭出来的元元,让“我”作为母亲有了存在意义,即使贤和丽英在一起还让丽英受孕了,即使贤在愤怒时狠狠打了我,“我”最后一次站在了和男人同样的高度,“我愕然站起身来,觉得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应该结束。”终于“我”做出了离婚的决定,带着孩子,晚上写文章,学习日语,一切又像是自我的重生。但是这一切又在那个无法动摇的体系里崩解,肺结核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渺茫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飘零,最后只能返回到“母亲”这个不幸的角色,而这种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我”的妥协,“我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诚,心中茫茫只想跪在她脚下做祷告:愿贤幸福,愿我的孩子们幸福,愿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般消散了,忘记我,让我独自在永恒的光辉下悄悄地替你们祝福吧。”“我”祝福孩子和贤的家人,是因为“我”只有在这一种归宿里才符合传统,而这一种观念在《后记》里甚至成为了对命运无奈的喟叹:“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够互相迁就些。能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了,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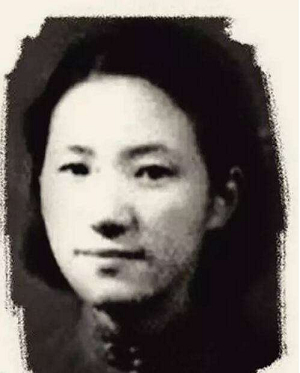 |
|
苏青:一生都没有找到拉她上岸的手 |
为了孩子,相互迁就,这是“我”的婚姻观,当“我”真正从这个世界里抽离了独立品质,我又成为“真是悲惨”的女人,成为被男权控制的女人,成为无法逃离环境的女人。《结婚十年》之后呢?苏青对于婚姻的认识似乎有了不同的观念,它们呈现了两条相异的道路,一条是《续结婚十年》中向上超越的路,一条则是《歧途佳人》向下沉沦的路。在《续结婚十年》的“代序”中,苏青陷入在一种求生的欲望里,孩子还小,自己离婚,所以她希望用写文章的方式换取生活必须的开支,在她看来,艺术家应该“爱惜羽毛”的,当时她却只能求得“果腹”,也就是在“吃饭第一”的生存中,“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即使遭遇了讥讽,甚至文章被诋毁,但是苏青认为自己“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所以在《续结婚十年》中,“我”在遭遇了家庭变故和婚姻解体之后,积极寻找一条自食其力的女性知识分子道路。
“夜是如此寂寂的,我的前途也黑暗,没有儿女,没有丈夫,没有职业,没有钱–什么可靠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是仍想活,又将如何活下去呢?”写文章让她逐渐走上了一条上行的路,因为写文章结识了电影公司、报社的文化人,甚至慢慢认识了金总理、潘长官、谢上校等一批达官显贵,自然,“我”在这样的圈子里得到了认可,而我的理想是:“我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不惯受拘束。我只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安心写作,可以自由进出。”但是当“我”逐渐上行的时候,一个无法改变的体系是:他们都是男人,他们都拥有权力,无论“我”是一个写出了多少好文章的人,“我”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是:我是女人。十万元的支票,做秘书的职位,以及出入派对沙龙,“我”似乎转变了,但是命运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上,“一切荣华富贵都如镜里月?水中花,是可望而不可触的,我要摆脱一切虚荣,只要一个可靠的归宿,然而……人家可肯相信你呢?”
“我”似乎有了一种自我意识,甚至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但其实,在这个被物化的世界里,“我”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我”羡慕那些靠敲竹杠获得上位的女人,“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可以有金钱补偿,心里总可稍安慰一些”;“我”想要成名,即使最强烈的渴望是死得轰轰烈烈,也必须在成名之后;“我”瞧不起乡下人,“真的,乡下地方太贫了,看起来连树木鸡狗都是没精神的。乡下人也真是太蠢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同他们万万谈不来,而且他们也并不善良。”在得不到男人依靠的生活里,在找不到归宿的命运中,在迷失了自我的世界里,“我”其实真的成为了牺牲品–也只有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在“母亲”的身份中,“我”才能得到一点安慰,而希望孩子找到称心的丈夫或者妻子,看起来也只是对自我命运失败的喟叹,所谓的宽恕最后也已变成了自我安慰,“我宽恕一切对不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人生是如此……如此有意味呀!”
向上之路,一样掌握在男人手里,而向下呢?《歧途佳人》中那个自述的小眉无疑从身患肺结核的姐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而这种高脆弱也被带上了女性无法自立的无奈,但是她希望自己走上另一条路,认识元泰钱庄老板黄鸣斋,和他的儿子承德结婚,似乎并没有如《结婚十年》里那颗樱桃的浓浓爱意,甚至只不过是男人喜欢漂亮女人、女人寻求物质满足的一种套路式生活,而应酬,吃花酒,热恋上一妓女,把母亲抛弃的父亲就是小眉心里的一道阴影,父权依然强有力的控制着一切。在和承德离婚之后,小眉的人生之路急转,本来想找到一个归宿,说喜欢她的史亚伦却是一个赌徒,不仅仅是出入赌场,而且也把人生看成是一种运气–被抓进保安司令部,之后又转移到了法院,小眉用十八根金条疏通关系,而其实整个司法、政府体系都是这样一种赌博状态。史亚伦更大的赌博是人生,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技术问题,要想成功一个办法是抢,第二个办法是骗,“至于’求’是没有用的。”他甚至让小眉参与赌博,在交际世界里为自己的成功带来好运。
史亚伦被宪兵队抓走,被称为靠山的窦先生消失,“拼命用功或拼命找求刺激都不能使我满足”,小眉走向了一条沦落的路,她没有自我,没有归宿,没有正当的收入,就这样在男人的欺骗中活着,所以当一切变成虚无,她内心只有等待死去的想法,“但是,近年来我渐渐悟到了一个道理,即是怜惜自己,愈会使自己苦,倒不如索性任凭摧残、折磨而使得自己迅速枯萎下去,终至于消灭,也就算是完结这人生旅行了。”在六个“?”的强烈疑惑中,小眉已经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路,她就像自己患了肺结核的姐姐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甚至姐姐在感叹生命的时候,她内心强烈的渴望反而是活着,是“生”,而不被疾病折磨的小眉却在慢慢走向死亡。
《结婚十年》,是一个女人结婚成为母亲却最终选择了离婚的故事,尽管最后是妥协,但至少选择离开不爱自己的男人,选择将孩子抚养成人,而《续结婚十年》中女人选择上行之路,《歧途佳人》中的小眉选择赌博和交际的下行之路,似乎最后都在命运的质疑、惶惑、迷失中,完全失去了女人独立的一面,“我只像一个溺水的人,要求他首先伸出援救的手。”那只手始终没有伸过来,于是如自溺一般沉入其中。而苏青自己呢?也许在文章之外,在现实里面,在向上和向下的不同道路上,多舛的命运也成为她文本的一部分,成为女性迷失的集体症候,“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飘浮在海面上,随波逐流的,忽上忽下荡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