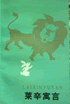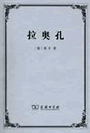 |
编号:B83·2140825·1106 |
| 作者:【德】莱辛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3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25.00元亚马逊20.00元 | |
| ISBN:9787100097857 | |
| 页数:253页 |
“诗与画终归是想象的描摹。凡是我们在艺术作品里发现为美的东西,并不是直接由眼睛,而是由想象力通过眼睛去发现其为美的。诗的意象是精神性的,这些意象可以并存在一起而不至互相遮掩互相损害,而实物本身或实物的自然符号却因受到空间与时间的局限而不能做到这点。”德国启蒙运动到莱辛才算达到了高潮,朱光潜说:莱辛在《拉奥孔》里指出了诗和画的界限,“纠正了苏黎世派提倡描绘体诗的偏向和温克尔曼的古典艺术特点在静穆的片面看法,把人的动作提到首位,建立了美学中人本主义的理想”。《拉奥孔》表面上像是在讨论诗歌与绘画的界限,实际上牵涉到当时德国文化界争论激烈的根本性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人的苦:“莱辛拿雕刻和诗比较,发现一个基本的异点:拉奥孔的激烈的苦在诗中尽情表现出来,而在雕刻里却大大地冲淡了。
他由痛苦而发出的哀怨声,号喊声和粗野的咒骂声响彻了希腊军营,搅乱了一切祭祀和宗教典礼,以致人们把他抛弃在那个荒岛上。这些悲观绝望和哀伤的声音由诗人摹仿过来,也响彻了整个剧场。
——《第一章 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
哀号从那个被抛弃的荒岛上传来,从向海神献祭的祭坛上传来,也从古希腊的史诗中传来,献祭的公牛有什么用?刺木马的长矛有什么用?空空的双手有什么用?冲着波涛而来的蟒蛇制造了“更严重更恐怖的事变”,缠住、撕吃、捆住,两个孩子和拉奥孔完全逃不出偏袒希腊人的海神的控制,逃不出毒蛇的侵袭,他的死亡成为代表整个城邦的符号:“拉奥孔以城邦的名义将一头牛献祭给海神,到头来自己却成为悲惨的牺牲”,这牺牲是对神的旨意的亵渎,是妻子与神像交媾的惩罚,是阻止木马进城的警告,而从神话变成史诗,拉奥孔的绝望和痛苦在诗人维吉尔的“整个剧场”里变成永恒的罪愆:
拉奥孔想用双手拉开它们的束缚,
但他的头巾已浸透毒液和淤血,
这时他向着天发出可怕的哀号,
正像一头公牛受了伤,要逃开祭坛,
挣脱颈上的利斧,放声狂叫。
——维吉尔《伊尼特》
像一头公牛要逃出祭坛的哀号,却终于没有实现,毒液和淤血变成了痛苦和死亡。这是听到的哀号,这是听到的痛苦,向着天发出的声音一定需要被听见,可是这“罪有应得”的死亡在维吉尔的诗歌里被听见,也在雕像里被看见,只是1506年被发现的雕像群里已经没有了举向头顶的右臂,没有了孩子的手掌和右臂,毒蛇还在缠绕,痛苦还在蔓延,极度的恐怖和痛苦是扭曲的身体,是痉挛的肌肉,是紧张的神经,可是,那张嘴巴却没有完全张开,那哀号没有完全发出,响彻整个剧场的悲观绝望和哀伤的声音只在诗歌里,而这高约184厘米、从葡萄园的罗马废墟里挖掘出来的大理石雕像却以一种破损的形式抵消了那种被听见的哀号声,“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当莱辛抛出这样的疑问时,站在他面前的温克尔曼却把这样的处理叫做“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种心灵在拉奥孔的面容上,而且不仅是在面容上描绘出来了,尽管他在忍受最激烈的痛苦。……但是这种痛感并没有在面容和全身姿势上表现成痛得要发狂的样子。他并不像在维吉尔的诗里那样发出惨痛的哀号,张开大口来哀号在这里是所不许的。”不允许的哀号,是不允许张开大口,因为,“哀伤要通过歪曲原形才表现得出来,而歪曲原形在任何时候都是丑的。”也就是说,在雕刻家看来,在身体苦痛的情况下,激烈的形体扭曲和最高度的美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须把身体的苦痛冲淡,必须把哀号化为轻微的叹息。这样的冲淡在温克尔曼那里变成了对于优美自然的一种超越,“这种伟大心灵的表情远远超出了优美自然所产生的形状。塑造这雕像的艺术家必定首先亲自感受到这种精神力量,然后才把它铭刻在大理石上。”
这是高贵的单纯,这是静穆的伟大,只有这样的单纯和伟大才可以打动灵魂深处的痛苦感受,才能使我们“愿望自己也能像这位伟大人物一样忍受困苦”。温克尔曼对于希腊绘画和雕塑推演出来的普遍规律实际上区分了野蛮和文明,“荷马写特洛亚人上战场总是狂呼狂叫,希腊人上战场却是鸦封雀静的。”仿佛就在这声音的传递中,对于内心灵魂是一种必要的沉淀,但是号喊是身体苦痛发出的自然表情,即使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当情感人出现号喊、咒骂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忠实于一般人性的,而温克尔曼建立的“伟大的静穆”的普遍规律,却是一种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
莱辛不同意温克尔曼的静穆观,实际上是反对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如果人们看到主角凭伟大的心灵来忍受他的苦难,这种伟大的心灵固然会引起我们的羡慕,但是羡慕只是一种冷淡的情感,其中所含的被动式的惊奇会把每一种其他较热烈的情绪和较明确的意象都排斥掉。”而莱辛的目的并非是要完全恢复“较热烈的情绪和明确的意象”,也并非是要让人在痛苦中张开大口发出哀号,他实际上从拉奥孔在诗歌和雕塑中不同处理中看到了诗歌和造型艺术的区别,《拉奥孔》的副标题是“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就是要在艺术爱好者、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这三类人的比较思考中找到画与诗的界限。画与诗在更多的时候是有着存在的共性,被称为“希腊的伏尔太”说过的那句话“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而诗则是一种有声的画”实实在在在对比中寻找到了他们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只是在效果上具有共同点,而“无论是从摹仿的对象来着,还是从摹仿的方式来看,却都有区别。”在莱辛看来,正是这样的一种混淆,使得艺术家下了最粗疏的结论:“他们时而把诗塞到画的窄狭范围里,时而又让画占有诗的全部广大领域。”画与诗在趋同中其实丧失了它们的独特性,在诗里追求描绘的狂热,在画里追求寓意的狂热,就是想把诗变成一种有声的画,把画变成一种无声的诗,而不知道诗能画些什么,也不知道画在多大程度上能表现一般性的概念。
画与诗的混淆是一种虚伪的批评,是一种“错误的趣味和没有根据的论断”,不可否认,人们在画与诗中寻找的是普遍的美,“美就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尤其在绘画上,无限宽广的题材可以作为模仿物体的艺术被画在平面上,在希腊艺术家看来,在他的作品引人入胜的东西必须是题材本身的完美,所以寻常的美,较低级的美,都只是一种练习或者消遣,而那些描绘奇形怪状的东西,描绘在寻常自然美的水平之下的低级趣味,是一种畸形和丑陋,“我要建立的论点只是:在古希腊人来看,美是造形艺术的最高法律。”所以必须抛弃那些歪曲原型表现的哀伤,必须抛弃丑陋的趣味,而让表情服从于艺术的美的规律。
 |
| 莱辛:没有哀号,只有叹息 |
这种美的最高法律表现在雕塑这样的造型艺术中,就变成了一种永恒,而要创造这种永恒之美,必须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也就是在某一顷刻被表现的造型艺术上,“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正因为如此,当激情达到了顶点,也就意味着它叨叨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因为想象跳不出感官印象,就只能在这个印象下面设想一些较软弱的形象,对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它不能向上超越一步。”而在雕塑中拉奥孔只有叹息而没有哀号,在莱辛看来,正是处理好了激情的顶点和想象的延伸的关系,“所以拉奥孔在叹息时,想象就听得见他哀号;但是当他哀号时,想象就不能往上面升一步,也不能往下面降一步;如果上升或下降,所看到的拉奥孔就会处在一种比较平凡的因而是比较乏味的状态了。想象就只会听到他在呻吟,或是看到他已经死去了。”如果逼迫拉奥孔哀号,那么这种激烈的痛苦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因为想象在这个顷刻消失了,“否则就要断送受苦痛者的性命”。但是可以摹仿“整个无限广阔的完善的境界”的诗歌却没有这样的局限,即使拉奥孔放声哭号,读者也不会联想到一定会张开大口,而即使张开了大口,在诗歌的世界里,也无法呈现那种扭曲的丑,“其次,诗人也毫无必要,去把他的描绘集中到某一顷刻。”诗歌里是永恒并不在某一顷刻表现出来。
那么再次回到拉奥孔,在关于哀号的不同处理中,关于画与诗的界限分析中,莱辛似乎想走一条捷径,那就是找出画与诗创作的先后时间,也就是说,是雕刻家摹仿了诗人,还是诗人摹仿了雕刻家?当然抛弃诗人和艺术家对于拉奥孔这个故事的更古的来源,仅仅在“这时他向着天发出可怕的哀号”的《伊尼特》卷二和化为叹息的雕刻群大理石上找到彼此的承续关系。“维吉尔是第一个人而且是唯一的人,让两条毒蛇把父亲和儿子一齐缠死;雕刻家们也就照办了;作为希腊人,他们照理本来是不应该这么办的,所以他们可能受到了维吉尔的启发。”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是应该说是雕塑家们用维吉尔史诗作为蓝本,但是诗歌中的拉奥孔穿着祭司的道袍,但是在群像里,他和两个儿子是完全裸体的;在诗歌里,拉奥孔的头巾被浸透了毒液和淤血,而在雕刻群里,也无这样的处理。所以即使雕刻家用维吉尔史诗作为蓝本,也在具体的创作中“牺牲了表情”,也牺牲了习俗,因为“雕刻无法摹仿衣料,衣褶会产生很坏的效果。”所以莱辛认为:“艺术的最高目的可以导致习俗的完全拋弃。美就是这种最高目的;衣服的发明起于需要,艺术和需要有什么相干?”如果反过来,是诗人摹仿了雕刻家,但是在维吉尔的诗歌里,拉奥孔的苦痛却从雕刻家的叹息变为哀号,“诗人如果见到雕刻作品中的那种苦痛与美相结合的动人的效果,试问他有什么绝对不可避免的必要,要一笔勾销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大丈夫的尊严和伟大心肠的忍耐心意而不把它表现出来,就突如其来地用拉奥孔的可怕的哀号,来使我们感到震惊呢?”也就是说,假如维吉尔真是用雕像群为蓝本,他一定会做好哀号之前的那种循序渐进的准备,而不是突如其来的表现痛苦。
其实,不管雕刻家摹仿了诗人,还是诗人摹仿了雕刻家,也不管是独创性还是抄袭,在莱辛看来,其实并不是一条捷径,甚至是一个死胡同,因为画与诗的界限决定了他们必须抛却摹仿中的共同性,而显示它们各自的独特性。把拉奥孔的哀号放置在一边,从画与诗的本质特点开始分析,莱辛认为,“诗是一门范围较广的艺术,有一些美是由诗随呼随来的而却不是画所能达到的;诗往往有很好的理由把非图画性的美看得比图画性的美更重要。”诗解放的是非图画性的美,譬如“由复仇愿望和忿恨情绪所驱遣的维纳斯”,不管是复仇还是忿恨,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样的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爱单就它本身来看,是既不发怒,也不图报复的。”而在诗歌里,维纳斯即代表爱,却“能爱慕也能怨恨”,这是画与诗在塑造形象上的分别,诗人要将抽象概念人格化的时候,只要通过他们的名字和所作所为,就能表现出来,而在雕刻家那里,他必须替人格化的抽象概念找出一些象征符号,使他们成为可以辨认的,成为一种寓意的形象,“节制者”手里的缰绳、“坚定者”所倚的柱子、“公正者”手里的天平、文艺女神手里的竖琴或笛、战神手里的矛以及火神手里的铁锤和火钳,都不是象征符号,而是表现的工具,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工具,艺术家才能塑造形象的特征,将抽象化为具象。
“诗的标志代表事物本身,而寓意性的标志则只代表某种类似这事物的事物。”这是画与诗在造型上的区别,而在构思和表达上,“对于艺术家来说,我们仿佛觉得表达要比构思难;对于诗人来说,情况却正相反,我们仿佛觉得表达要比构思容易。”也就是说,艺术家更需要表达,诗人更需要构思,如何表达,在画家看来,可以眼见的人物和动作,不可以眼见的人物和动作,他都必须化为可以眼见的,也就是按照朗吉弩斯的观点,绘画把神降低到人,因为“在画里凡是诗人使神超出像神的凡人之上的东西都完全消失了”,即使用一层薄云遮住,制造一种神秘的效果,也已经在可见中失去了神性,或者说,云雾已经变成了人为符号,而不是自然符号,而在诗人的世界里,“这种看法是完全违反诗人精神的。”对于诗歌来说,能否入画并不是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一幅诗的图画并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一幅物质的图画;诗人在把他的对象写得生动如在眼前,使我们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他的语言文字还更清楚时,他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都是一幅图画,因为它能使我们产生一种逼真的幻觉,在程度上接近于物质的图画特别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幻觉,也就是观照物质的图画时所最容易地最快地引起来的那种逼真的幻觉。”所以在密尔顿与荷马之间,肉眼和心眼在诗歌中的这种局限,成为了关于“失明”的一种证明,看见和不看见,并不是诗歌必须承担绘画的题材局限,而是在失明中消除这种局限。
实际上,绘画和诗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空间和时间上对于物体描述的区别,“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莱辛把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成为自然的符号,把事件中先后承续的符号叫做人为的符号,自然的符号是线条和颜色,而人为的符号是语言,所以,“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叫做‘物体’。因此,物体连同它们的可以眼见的属性是绘画所特有的题材。”而“全体或部分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一般叫做‘动作’。因此,动作是诗所特有的题材。”绘画摹仿动作是通过物体的暗示来表达,而诗只能通过动作的暗示去描绘物体。也就是说,在画家的作品中,只能看见已完成的东西,而在诗人的作品中却看见它完成的过程。一种是时间的先后承续,一种是空间的表现,如果把时间的两点纳入画里,就是画家对于诗歌领域的侵犯,而把事物一—历数给读者,就是诗人对于画家领域的侵犯。
所以,绘画描写的是物体美,“物体美源于杂多部分的和谐效果,而这些部分是可以一眼就看遍的。所以物体美要求这些部分同时并列;各部分并列的事物既然是绘画所特有的题材,所以绘画,而且只有绘画,才能摹仿物体美。”而诗人则是“就美的效果来写美”,荷马的诗里,尽管只偶尔听到说海伦的胳膀白,头发美之类的话,但是,正是荷马的那些诗歌,“才会使我们对海伦的美获得一种远远超过艺术所能引起的认识”。所以,对于诗歌来说,诗人的意义就是“替我们把美所引起的欢欣,喜爱和迷恋描绘出来吧,做到这一点,你就已经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
可看见的美,想象的美;物体的美,动态的美;已完成的美,过程的美……画与诗,都在实践着作为最高法律的美,但是在美之外的丑呢,在莱辛看来,丑按照本质来说,是不能成为诗的题材,绘画也拒绝表现美,但是莱辛所指的丑并非是一种低级趣味的丑,而是在题材的运用中“产生和加强某种混合的情感,也就是冲淡形体的丑陋所引起的反感,在可笑性和可怖性所伴随的情感中反衬出一种美,就像画家的”反衬色调“一样,是彼此融合,“身体讨人嫌,那心灵却引人喜爱,各走各道。”就如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所说:“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害的,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在莱辛看来,丑的作用在可笑中于喜剧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在绘画中,虽然也同样利用丑的可笑和可怖的混合来加强其他感觉,但是由于绘画着重表现的是物体本身的状态,所以那种无害的丑停留在可笑上面,也会惹人嫌厌,而有害的丑带来的可怖性逐渐消失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丑陋,“不可改变地留在那里。”
反对静穆的伟大,也抛弃禁欲主义,但是对于莱辛来说,鄙视“污秽画家”,谴责密尔顿诗中的恶魔主角,都为了是诗歌和绘画达到古典艺术的最美境界,实际上,他也没有完全摆脱新古典主义的文艺趣味。对于诗和画的界限分析中,莱辛是想要建立的是一种理想美,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他在1769年3月26日给尼柯莱的信中说,“绘画和诗都有两种,高级的和低级的。”在他看来,高级的绘画“是只用存在于空间中的自然符号的那一种绘画”,而较高级的诗“也是只用存在于时间中的自然符号的那一种诗”。所以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历史画和寓意画都不能属于高级的绘画,而戏剧诗“文字已不再是人为的符号,而变成了人为的对象的自然的符号”,把人为的符号完全变成自然的符号,便具有了理想的美,这种理想美不是静穆,“而是静穆的反面”,“包含的动机愈多,愈错综复杂,愈互相冲突,也就愈完善。”理想化和高级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莱辛的启蒙贡献,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也否定了诗歌和绘画的多元化,否定了艺术对于美的突破,当然也否定了艺术的社会意义,在亚里士多德哲学、荷马史诗的古典主义光亮照射之下,莱辛其实没有听到那从荒岛上传来的痛苦哀怨声、号喊声和粗野的咒骂声,也没有祭祀和宗教典礼,对于他来说,响彻整个剧场的也只是那静穆而理想的叹息,最终连同冰冷的大理石,一起被埋入罗马帝国的废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