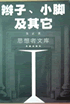|
编号:C38·2190421·1566 |
| 作者:【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2.30元 | |
| ISBN:9787020142668 | |
| 页数:256页 |
三个女人,三种生活,三个大洲,同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印度,斯密塔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贱民”,为让女儿逃离残酷而荒谬的传统,她把女儿送进学校,最后,斯密塔决定带着孩子远走他乡。意大利西西里,朱丽娅在父亲的假发厂工作,父亲因车祸陷入昏迷之际,她在恋人的帮助下决定利用网络从印度市场收购头发,拯救工厂和家人。加拿大,萨拉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律师,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投入了全部精力,她即将登上事务所最高位,却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事务所在得知她的病情后,以让她好好休息为借口,把她隔离起来,萨拉一度消沉,之后决定积极面对困境。最终,印度女人的辫子,经西西里女孩加工成假发,戴在了加拿大女人的头上。她们原本素昧平生,却被这条辫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辫子》:她就是人格化的肿瘤
我享受这孤独的时光,双手在舞蹈的时光。
这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
我们谱写着一个有关编织和辫子的故事。
这是我的故事。然而它并不属于我。
三根尼龙绳紧绷,一只手抓住线头,然后将它们扎在一起,“接着,重新开始/反复千次”。这是“双手的舞蹈时光”,这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享受的孤独时光,但是,这反复千次的编织为何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为何“这是我的故事”,然而它“并不属于我”?怪诞却“不属于我”,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像是游离在故事之外,一个编织的作者,把三个故事变成“三股头发交叉编成的集合体”的时候,是不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自己在这个集合体之外?
女性作者,女性主角,这是一个关于女人命运的小说,当那些头发从印度巴德拉普尔、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女人的命运是不是真的被改变了?当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在题辞中说这是“怪诞”的故事,说这不属于自己的时候,她为之建立的体系其实是脆弱的,虽然她是献给“所有勇敢的女性”,虽然他引用《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的话“只有女人与轻浮女人正好相反”,但很明显,她笔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命运的女人真的不算勇敢,当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自由。
要勇敢并且自由,就是女人对于命运要进行反抗,这是基本的逻辑线,反抗什么?当然是那个男人主宰的社会。《斯密塔》的故事里,站在印度女人斯密塔前面有一个男人,他就是丈夫纳加拉简,“她属于他,是他的所有物,他的奴隶,就应该对他唯命是从。”女人是男人的一个奴隶,男人对女人发号施令,所以这种男女对应的二元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丈夫纳加拉简和斯密塔同属于“达利特”阶层,这个阶层在印度就是“不可接触者”,是“处于种姓之外,制度之外,一切之外”的存在,甚至纳加拉简和斯密塔的命运相差无几:“他是个捕鼠者,和他的父亲一样。他在贾特人的田里干活。”用田里捕来的老鼠维持生计,这便是一家人的生存下去的保证,在这种命运里,他们其实是同病相怜的,而且,在 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这里寻找一种未来的时候,斯密塔的内心也有过挣扎:“斯密塔突然感到心里一酸。她是爱过这个男人的,也习惯了他那令人安心的陪伴。可是,她恨他的懦弱和用来掩饰他们的生活的宿命论。她多想和他一起走啊。然而,从他放弃斗争的那一刻,她不再爱他了。”
爱过这个男人,现在不爱他了,因为他没有像斯密塔一样选择离开,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将斯密塔的反抗指向纳加拉简显然是粗暴的。而其实,对于身为“不可接触者”,最大的命运压迫来自于其他的阶层。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女人,一个是决定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的女人,当比达利特更高一层的贾特人知道她要离开之后,就在她穿过田野逃跑时逮住了她,他们将她拖到一片无人的荒地,八个人把她轮奸了整整两天;另一个是斯密塔在车上遇到的一个寡妇拉克什玛,丈夫在几个月前因为流感而去世,她的婆家便抛弃了她,因为在他们看来,拉克什玛是一个“没能挽留住死去丈夫灵魂的罪人”。
身体上和精神上备受折磨,这是印度下层女人所受到的痛苦,而这两个女人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并非是男人所为,而是他们面前强大的阶级观,就像斯密塔和纳加拉简永远是达利特,女儿也无法改变命运成为贾特人,他们的一生都是“不可接触者”,都要在掏粪和捕鼠中度过,都会受到他人的贬低甚至侮辱。“你是一个达利特,一个清扫工,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这么活着。”所以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男人,而是特权。特权撕破了拉丽塔身上的纱丽,特权让她一个人打扫教室,特权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特权也强奸了女人,惩罚了寡妇。
对于西西里的朱丽娅来说,男女之间的二元关系也被解构了,她二十岁就在父亲的兰弗雷迪公司里做头发,在她的生命中父亲反而是让她学会了独立,当父亲在收头发的时候出事,整个公司似乎陷入了困境,走向了破产的边缘。在朱丽娅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是母亲口中可以结婚的男人:吉诺·巴塔格里奧拉这些年一直爱着朱丽娅,做梦都想娶她。但是这个男人并没有成为朱丽娅命运的压制者,他的确有钱,但是朱丽娅却反对这门亲事,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另一个男人却是她爱情的拯救者,这个来自克什米尔的男人卡玛是个难民,他是朱丽娅在游行中认识的,之后两个人产生了感情,朱丽娅抛弃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转而投向了这场来自不同民族、阶层两个人的爱情,卡玛甚至在爱情中,帮助她走出困境:用印度人敬献给神明的头发做假发卖掉。
实际上,压在朱丽娅命运之上的巨石不是男人,而是一种传统观念,“意大利人只能要意大利头发”,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兰弗雷迪家一直以来都在西西里进货,收集头发是这里一项古老的传统。”所以在这个命运中,“谁也不可能动摇传统而不受惩罚。”而从朱丽娅面临的困境又可折射出西西里岛的人的观念之可怕,无法收集到头发是因为“饱受现代生活折磨的西西里人不再保留他们的头发了”,不仅仅是头发,只要是用久了的东西就会扔掉,再去买新的。
特权的等级的存在,使得斯密塔一家都处在穷苦和丧失尊严的命运中,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使得朱丽娅的头发产业陷入困境,而在《萨拉》的故事中,作为律师事务所的一员,萨拉的确活在“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事务所里,就像她在十年前第一次踏入大厅面试的时候一样,“她面对着八个男人,包括事务所的创始人、管理合伙人约翰逊本人。”正因为要在众多男人面前出人头地,甚至要成为下一届管理的合伙人,萨拉牺牲了太多——“为了工作,她经常熬夜,还搭进去两段婚姻。”最后的结果是因为疲劳身患癌症,而为了不影响工作,不影响地位,她甚至只能一个人承受。
三个女人都面临着困境,对于他们来说,需要反抗,需要唤醒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是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当女人反抗而改变的时候,其实在部分体现了勇敢精神之外,并没有抵达自由,甚至她们的行为只是一种妥协。斯密塔无法忍受“不可接触者”的命运,在她内心来说,一直有一股弱小的力量,就像她妈妈传给她的那只用灯芯草编织的篮子,是命运的写照,“这个篮子是她的劫难。一个诅咒。一种惩罚。就像妈妈说的,她前世一定造了什么孽,需要今世来偿还。”所以斯密塔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的,她觉得要改变一切,必须让女儿接受教育。但是当女儿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她想到了离开,但是离开是为了什么?
“她向毗湿奴发愿,要是她们能成功逃脱,要是婆罗门的妻子什么都没发现,要是贾特人没能抓住她们,要是她们能平安到达瓦拉纳西,坐上火车,最终活着到达南部,那么她们就会到蒂鲁帕蒂神庙去为他朝觐。”向毗湿奴发愿,奔向蒂鲁帕蒂神庙,这是斯密塔祈求命运改变的做法,实际上在宗教意义上希望结束这一切,并不是自由的表现,更不是自我意识,她只不过是改变了在自己头上的命运形式,但她爬上蒂鲁马拉山,当向卡特斯瓦拉神献祭,当终身不剪的头发变成了敬献的财物,只不过对斯密塔的内心来说,是一种安慰:“这是一个流传千年的传统:献出头发意味着弃绝自我,将自己最谦卑和原始的样子展现在神明面前。”
真的弃绝了自我?斯密塔会向何处去?她还是达利特,在她上面还有贾特人,还有婆罗门,甚至还有把她当奴隶的丈夫纳加拉简——她一定会带着女儿从蒂鲁马拉山下来,而在命运丝毫不曾改变的情况下,失去了头发的母女甚至会陷入更深的命运深渊中——仅仅是改变了头发的属性,难道就能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改变被压迫的命运?而对于朱丽娅来说,当她在卡玛的帮助下重新开始了头发产业,看起来是女性的一次解放,而她的所有举动依然是和男人有关,父亲在病床上似乎给了她孤立,男友给了她爱的力量,这样一种自食其力的方式改变了西西里人的某些传统,而当他们把斯密塔敬献给神的头发变成了商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亵渎行为:斯密塔弃绝自我,是在神性保护的自我安慰下进行的,如果她知道自己和女儿的头发变成了意大利某一个工厂的商品,怎么能心安?
头发具有的宗教属性变成了商品属性,不仅没有在信仰意义上赋予女性独立地位,而且弱化甚至取消了其中的命运抗争因素,而最后戴上这个假头套的是萨拉,更变成了一种掩饰,而考察萨拉的命运起伏,她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也当成了这个大男子主义社会的一份子:她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身份被放在了边缘地带,取而代之的是高管、职业女性、IT女孩、神奇女侠,这些标签与其说是是和男性社会抗争,不如说是融入;她的车位上写着“约翰逊&洛克伍德律师事务所,萨拉·柯恩”,她感到骄傲,“这不仅仅是一块标示着她的车位的名牌,更是一个头衔,一种等级,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她不喜欢别人称呼她“女士”,而要称呼为“律师”,是因为在这个称呼里她才感到自己是和其他男人同起同坐的。
正是因为她在乎这些命运、等级和地位,所以她付出了所有的时间,最后积劳成疾,而当癌症侵袭她的身体时,她身上的那些女性特征又慢慢消失了,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一只乳房被割除,头发掉光——而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遭受了身体的摧残,因为她想用谎言维持这样对外的身份,而揭露这个谎言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伊奈斯,“库斯特的手上连一滴血都不会沾,完美的犯罪。就像下棋,一棋子倒下,后面的所有棋子都可以前进一步。而这个棋子就是萨拉。”萨拉的这种心理活动有着太多的嫉妒,甚至变成了一种病态。
而最后她对命运的反抗,无非也只要一种结果: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虽然她戴上那个头套,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自己,只有告别过去,告别曾经撒谎的自己,才能找到真实的生活,“一个尽管被生活粗暴对待却敢于带着伤疤、缺陷和伤口,坚强地活着的女人。”她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变得坚强,而坚强的意义就是不让社会看不起她——在她面前永远有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永远属于“大男子主义”,看起来是独立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当那个遭遇沦为商品的头套从印度的圣山到西西里的工厂,再到她的头上,女人和头套一样,变成了商品社会生存的牺牲品。
“她想,为了使她痊愈,整个世界同心协力地在努力。”三个女人的头发被编织在了一起,“凡救一个人,即救全世界。”萨拉想要向整个世界致敬,但是在活着看起来新生的轮回中,无论是弃绝自我找到了信仰的斯密塔,还是重新开创了属于自己事业的朱丽娅,在“然而它并不属于我”的故事中,命运依旧张开了大口,她,她和她,不能挣脱的不是女人自身的命运,是弱小的个体无法改变整个社会规则的茫然,就像萨拉,“她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萨拉成了癌症本身。她就是人格化的肿瘤。”在对本质意义的社会不做彻底的改变,她们或许永远是“人格化肿瘤”里的一部分,抗争着,却又牺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