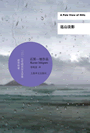 |
编号:C38·2171213·1438 |
|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27.00元亚马逊16.70元 | |
| ISBN:9787532753451 | |
| 页数:249页 |
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的文化背景,石黑一雄是极为少数的、不专以移民或是国族认同作为小说题材的亚裔作家之一,当他他致力于写出一本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但是在《远山淡影》这本石黑一雄处女作中,他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转向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乱的阴影与心魔,始终忘不见那里的 “远山淡影”。在作品中是浓浓的感伤与反讽,而在这一段迷雾重重、亦真亦幻的回忆之后,当忆者剥去伪装,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需要灵魂去感悟的?一部问世30年仍在不断重印的名著,其内核或者正如瑞典学院给出石黑一雄的获奖理由: “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远山淡影》:我不想再见到那个地方
可是,一个长成了快乐、自信的年轻姑娘——我对妮基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个越来越不快乐,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六章》
远处是山,远处是海,远处是云,以及远处更远,是一个模糊的世界,而那近处的雨水,溅落在透明的玻璃上,清晰可见,却又时刻准备着坠落。远和近,模糊和清晰,背景和现实,就这样成为封面的一种解读。像一帧明信片,提供了视线和视野,那么,是谁看见又看不见?是谁在回忆又不该回忆?
是那个叫悦子的 “我”,她一定是在站在落雨的季节,隔着某一种透明的存在,将目光放在远处更远的地方,只是风景的意义,并不是都可以提供真实的意义,当无法穷尽的远处成为背景,当背景被模糊地遮蔽,其实有时候是看不清自己,看不清现在,一滴一滴的雨会溅在透明的世界里,然后在滑落甚至坠落中一遍一遍清洗残存的印记。那时候她已经离开了长崎,那时候她已经居住在英国,那时候景子已经上吊自杀,那时候妮基已经出生长大,那时候面对的是现实,那时候想起的是记忆。
两个城市,两个女儿,甚至两个时代,其实就是提供了远和近,模糊和清晰,背景和现实的参照,悦子说一个是快乐自信的姑娘,一个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两种命运或者可以直接写成:生和死,但是两个人完全相异的选择并非是注定的, “都是火爆脾气,都有很强的占有欲;生气的话,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很快忘记他们的怒火,而是会闷闷不乐一整天。”她和她, “小时候有多像”似乎注解了相同的性格,但是这种相同似乎抽去了他们生活的背景,一旦把景子放在了走不出来的远处,把妮基放在了离开日本的伦敦,她们便成为两种坐标,关于战争,关于生命,关于现实,关于记忆,都会在 “远山淡影”中成为一种感伤和反思。
“和妮基不同,景子是纯血统的日本人,不止一家报纸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事实。”景子跟随着悦子来到英国,在曼彻斯特的房间里上吊自杀,当一种死发生的时候,必然带着某种异域文化的观念解读, “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导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而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陌生化的注解,就像妮基对悦子说的: “她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不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在爸爸的生活里。我从没想过她会来参加爸爸的葬礼。”生和死其实并不仅仅是不同文化之间造成的差异,当一种死发生的时候,感伤之外的反思,必然会回到长崎,回到日本。
长崎,日本,就是那远处的山,远处的海,远处的云,以及远处更远的存在,20多年的时间,也并不能像雨水可以清洗残存的印记。战争的结果是战败,对于那一段历史来说,多少人能真正走出?多少人只是以模糊的方式看见?如果要把那段历史做一种清晰的呈现,悦子的公公绪方先生应该是一个参照,他经历过战争,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但是在战后的生活里,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过去,从福冈到长崎来看儿子三郎,最喜欢的就是和他下棋,在棋盘上,绪方先生也在考虑着战略和战术, “下棋就是不停地贯彻战略。就是敌人破坏了你的计划也不放弃,而是马上想出另一个战略。胜负并不是在王被将时决定的。当棋手放弃运用任何战略时,胜负就已经定局了。”一盘棋就是一种人生,就是一种态度,他把无心恋战的三郎看成是投降主义者,并且以父亲的名义批评他,对于他来说,战争是一次摧毁,但并不是带着反思的目光来看待这一切。
当三郎的同学松田重夫发表文章,认为那一代日本人 “在战争结束后就该被解职了”,绪方先生要三郎写信告诉他,这篇文章侮辱了家族名声,并且要三郎予以回击。而当儿子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的时候,绪方先生甚至去找松田重夫,当松田重夫认为那时候学校老师教给学生的是 “可怕的东西”: “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但是绪方先生却告诉松田重夫: “我们打败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枪和坦克,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胆小,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浮浅。重夫,你不知道我们多么辛勤地工作,我们这些人,像我,像远藤老师,你在文章里也侮辱了他。我们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国家,辛勤工作让正确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
活在那一种传统中,并且还要在战后继续保持,甚至发扬光大,要 “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所以当他听说有夫妻将选票投给不用的政党时,他生气的是所有人丢掉了忠诚: “人人借着民主的名义丢掉忠诚。”忠诚,一个曾经熟悉的字眼,也是一个给日本人带来过阴影的观念,但是在绪方先生那里成为了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上一代人的观念,它在远处更远,只是它从来没有消失,甚至会突然闯进来。而在绪方先生的另一面,藤原太太则提供了上一代人的另一种参照,丈夫是长崎的重要人物,当炸弹投下来的时候,一家人除了藤原太太和大儿子以外都死了,对于藤原太太来说,这一定是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灾难,但是在灾难面前,她选择的是积极面对生活,开面店过好每一天,就像她对悦子说的那样: “心态决定一切。一位母亲应该得到她想要的所有的照顾,她需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抚养孩子。”
绪方先生和藤原太太提供了上一代人的两种人生观,他们或者可以看成是一种远山般的背景,而这一代呢?如何面对战后的世界?如何走出灾难的阴影?悦子无疑是这一代的代表,她就生活在长崎,在那里结婚生下了景子,而后离开日本来到了英国,再婚,再育。跨文化的生活方式无疑也是提供了两种选择,当景子和妮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便形成了两个相异的方向,而相异的方向却只有一个出发点:如何面对那个远山般的背景?或者可以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景子为什么要自杀?
“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景子在曼彻斯特的房间里以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在这之前她 “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在我们之外,在打开的世界之外,那个关着的封闭房间里到底有怎样的痛苦?这是一个隔绝了这一代和下一代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从悦子在长崎遇见的万里子入手,在某种意义上说,万里子就是景子的一面镜子,她的生与死,她的反叛和妥协,她的无奈和绝望,也许正是景子自杀的原因。万里子是佐治子的女儿,他们就生活长崎那片和战争有关的土地上, “一座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我从窗户就能看见木屋独自伫立在那片空地的尽头,就在河岸边上。”
 |
| 石黑一雄:记忆在别处 |
佐治子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结婚, “那时没有。我嫁入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我从没想到战争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战争到底是什么,她不知道,所以, “要不是战争,要是我丈夫还活着,万里子就能过上我们这种地位的家庭应有的生活。”但是这只是假设,当一切无可回避,唯有面对。但是战争一旦被看见,灾难一旦被降临,不仅对于佐治子,还是对于万里子,都变成了一种阴影,而留在他们脑海里最大的阴影便是那个在空袭中死去的女人,并不是被炸死,而是在被轰炸之前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一个女人自杀或者也并不是战争中最恐怖的事情,而是当她被人从水里捞上来的时候,她抱在水里的是一个婴儿。
“是个婴儿。我拉住万里子,离开了那条巷子。”这是佐治子的 “离开”,而正是从这个离开开始,她几乎都在逃离记忆,逃离现实,那个叫弗兰克的男人,那个叫美国的地方,成为佐治子想要抹去阴影的一种救赎力量,甚至把它们看成是为万里子设定未来方向的唯一办法: “而且万里子在美国也会过得更好。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在那里,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她可以成为女商人。她可以进大学学画画,然后成为一个艺术家。所有这些事情在美国要容易得多,悦子。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在这里她能有什么指望呢?”当佐治子以自己的方式驾驭女儿的生活,其实在万里子那里同样变成了阴影。
万里子总是看见那个女人, “她住在河对岸。她昨晚来这儿了。那时妈妈不在。”看见女人就像看见了死亡,看见了灾难;万里子讨厌 “像猪一样撒尿”的弗兰克;但是万里子的世界对于佐治子来说是陌生的,她把那个女人说成是万里子编的故事,她要万里子接受弗兰克,因为只有接受,才能离开,只有离开,才能忘记。佐治子其实是决绝的,万里子也是决绝的,那一晚从家里离开爬上树,无疑是万里子自杀的预演, “万里子躺在水沟里,短裙有一面浸在黑色的水里。血从她大腿内侧的伤口流出来。”但是佐治子把它看成是一次不小心的事故,她没有在意万里子空洞的眼神,没有抚慰万里子孤寂的心灵,甚至在想要离开之前,把万里子喜欢的猫浸到了水里: “这只是一只动物,悦子。就只是一只动物。”万里子跑向了远方, “眼睛仍然看着河水,似乎没有听见在叫她。”
当二十年前的记忆翻现在悦子脑海里的时候,万里子预言的死亡其实在印证景子之死,也是离开,也是背向,那一种阴影其实一直没有抹除。而不管是绪方先生为代表的上一代,还是悦子、佐治子的这一代,以及景子和万里子的下一代,关于战争,关于故乡,关于生命,都被一种阴影笼罩着,而从藤原太太到悦子、佐治子,再到景子和万里子,构筑的是一种女性视角,甚至是一种母性视角,这种视角其实更直接面对生与死的问题。
藤原太太生下了孩子,也见证了自己孩子的死;佐治子和悦子也孕育了生命,但是在死亡意识中他们却在苦苦寻觅一种超越的方式,万里子有着无法抹去的死亡阴影,那么离开之后她如何直视自己痛苦的生活?景子之死便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不管是万里子还是景子,他们本身作为孩子,是一种生命存在的代表,但是死亡却将他们带向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在景子和万里子之外,是另一种可能的面对方式,那就是以妮基为代表的生活。当悦子告诉她: “也许你很快就会结婚生孩子,我怀念小孩子。”而妮基却回答: “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了。”她问悦子的是: “我干吗要结婚?意义何在?”
这或者也是一种女性视角,在另一种意义上她回避了生,或者她并不是在母性的角度来为自己定位,这并非是一种逃避,当战争成为灾难,是那个在空袭来临之前自杀而让孩子死去的母亲;当战后制造阴影,是渴望着逃离却没有走进女儿世界的母亲佐治子。当那些东西都渐渐远去成为了背景,都已渐渐模糊,在记忆转身之外是应该看见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以悦子对妮基说: “我并不为你感到羞耻,妮基,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那时的天空起了风,告别了悦子的妮基回往伦敦,那是她的生活,那是她的未来,那是她的人生, “到门口时,妮基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还站在门口,似乎有点吃惊。我笑了笑,朝她挥挥手。”每一个人都不再是别人的背景,看见或者看不见,都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回忆或者不回忆,也终于能够自如地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