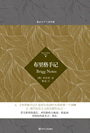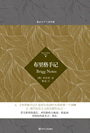 |
编号:C36·2190222·1540 |
| 作者:【德】 里尔克 著 |
|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
|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
| 定价:55.00元当当27.50元 |
| ISBN:9787220104572 |
| 页数:352页 |
《布里格手记》的全称是《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它是里尔克创作生涯中所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作品之一。小说叙述一个出生没落贵族、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的回忆与自白,某种程度上即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小说由七十一个没有连续情节、不讲时间顺序的笔记体断片构成,这些断片因为共同的主题——孤独、恐惧、疾病、死亡、爱、上帝、创造等,集中表达了里尔克终生关注的各种精神问题,在精神暗流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有机整体,被誉为现代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先驱作品之一。第一句:“就这样,也就是说人们来到这里,原为求生,我倒是以为,这里在自发死去。”
《布里格手记》:不在场给了他事物的密码
当她以性的无限的意图突破它的暂时的用途。当她在拥抱之黑暗中不是采掘满足,而是采掘渴望。当她蔑视这个,即两人中一个是爱者另一个是被爱者,而那些虚弱的被爱者,她把她们背到自己的床榻上,在身旁烤热她们使之成为爱者,她们便离开她。在这样的崇高的离别之际她的心化为本性。高于命运她为昔日的爱人们唱她的新娘之歌;为她们提升婚礼;为她们夸大那位邻近的夫君,以便她们为他全神贯注像为一位神而且也还经受住他的荣耀。
——《68》
爱者和被爱者,是一个和另一个,他们仿佛在“两人中”变成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只有爱者施爱,被爱者接受,他们才能合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便可命名为爱。但是这样一种看似整体的关系却是脆弱的,易变的,当疾病缠身,当死亡降临,甚至当爱者背叛,被爱者如何才能得到爱?或者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被爱者如果反身为爱者,在这个本已固定的结构中,如何突围,如何超越,如何改变?
第68节,似乎已经脱离了1902年8月28日开启的巴黎生活,“巴黎这般充满此欲望,因此这般贴近死亡。这是一个陌生的、陌生的城市。”在图利耶街的廉价旅馆里,里尔克感受到了浓烈的死亡气息,“就这样,也就是说人们来到这里,原为求生,我倒是以为,这里在自发死去。”而死亡不是结束,是背叛了生存意义的“生存欲望”——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里尔克说:“生存是某种宁静的、宽广的、单纯的东西。生存欲望则是匆忙和追逐。这种欲望:拥有生命,立刻,完全,在一个时辰中。”第68节,似乎也远离了童年的乌尔斯伽德,当作为侍从官的祖父克里斯托夫·德特勒夫·布里格在那里死去,并非是一种恐怖的终结,而让死亡成为一种永生,“它像个国王,人们称之为恐怖王,此生及永久。”——里尔克唯有在写作中忘记那一道童年的阴影:“我做了些事情来对付恐惧。我坐了整整一夜并不停地写字,现在我累坏了像走了很远的路穿过乌尔斯伽德的田野。”
充满生存欲望的巴黎,充满死亡恐惧的乌尔斯伽德,似乎在记忆和现实意义上解构了爱者和被爱者的关系,而在这个整体结构走向终结的第68节,里尔克却在呼唤着一个“她”:她有着性的无限,她采掘着满足和渴望,她蔑视着“两人”尤其是那个爱者,而最后当她离开了爱者,在新娘之歌里,在提升的婚礼上,虚弱的被爱者似乎又拥有了爱,在这个爱者已经不在场的情况下,被爱者而具有一种人性意义上的爱,就是里尔克所渴望的“不及物的爱”。
不及物的爱,并非是将爱埋葬,也并非是留着一个空位,而是把爱当成是超越物的“艺术之物”,而是把被爱者也当成爱者——爱者和被爱者的二元结构被打破,其实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终结,在转变、超越和突围中,爱是不及物的,爱者也成为“伟大的爱者”:“难受地活着,被爱者活在危险之中。唉,但愿她们经受住自已并成为爱者。围绕爱者的是真正的安全。没有谁再怀疑她们,而她们本人不能背叛自己。”而创造了不及物的爱的“她”是斯坦帕,是阿尔科福拉多,是萨福,是杜塞:《新诗集》中里尔克赞美了萨福,称她为“伟大的爱者”;而1906年11月而易卜生的戏剧《罗斯默斯霍尔姆》中里尔克第一次见到了演员埃莱奥诺拉·杜塞,他便为她建造了一种爱的剧院:“那时候在维罗纳,当你,几乎还是个孩子,演着戏,将纯粹的玫瑰捧在你面前之时,它像一个假面似的前面,应该掩藏正被提升的你。”
历史的,神话的,舞台之上的,剧院里的,她和她,是伟大的爱者,献出“不及物的爱”,而当爱者成为伟大的人,被爱者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甚至悲剧者、痛苦者,以及不可言喻的感人者都在对面消失,“像一个孩子”,拥有纯粹的玫瑰,于是那些松弛的门、骗人的窗帘、眼前的器物都被抛在了身后,不再背叛他人,也不再背叛自己,从此,通向不及物的无限,“被爱意味着燃起来。爱则是:以永不枯竭的油闪光。被爱着是消逝,爱是持续。”
如天使,如上帝。但是,在这个被爱者反身为爱者、爱又成为不及物状态的理想世界到来之前,似乎是痛苦的,而这个转变过程亦是漫长的,里尔克说:“一年对我们是什么?一年又是什么?还在我们开始了上帝之前,我们就已向他祷告了:让我们经受住黑夜吧。尔后病患。尔后爱情。”《布里格手记》似乎就呈现了这个“尔后病患,尔后爱情”的曲折过程,从童年的乌尔斯伽德开始,延续到只有生存欲望的巴黎,在里尔克所看见的世界里,似乎都在那个“及物”的层面上,物是什么?是肉体的疾病和死亡,是匆忙和追逐的人生,是被物化的爱,甚至是从未摆脱的恐惧——它们构成了里尔克称为“在场”的东西,而在场也意味着生存的“外部”状态。
“只是蒙在一个腐败物上面的一套巨大礼服。”祖父布里格死了,他躺在地板中间,一动不动,那巨大的、陌生的、再无人认得的脸上双目已经闭合,深蓝色的制服被撑开了,一个“恐怖的主人”的死亡,把整个乌尔斯伽德都笼罩巨大的恐怖中,把相关的日子都变成了沉重的死亡,“从我的祖父、昔日的侍从官布里格身上,人们还可以看出,他体内驮着一个死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呀:长达两个月而且吼声之响,就连旁侧庄园之外都能听见。”这是一种关于死亡之物的开启,而在十几岁的里尔克生命中,即使他和父亲来到了乌尔涅克洛斯特看望外祖父,这种巨大的死亡之物也像那间宽大的蓝色制服,被撑开而成为一种恐怖的象征。
即使那里有花园和山毛榉,有牛奶场和狗,有可以得到的牛奶、面包和水,甚至有我可以享受的自由,但是这只是某种幸运,外部世界提供的幸运,它会像被爱者一样成为虚弱的代名词:我发烧了,而医生要给我施以电疗,像是无法逃脱的命运:“我专心观察着这一切,并冒出一个念头,看来这便是早已为我确定的地方,因为我相信现在终于来到我生命的那个位置,我会待在此处。没错,命运走的是奇诡的路。”这或者只是降临在我身上的命运,而在我之外,那无法逃避的死亡气息让一切都成为了恐怖之物。
外祖父的远方亲戚用客套的方式谈论的是我母亲之死,而我想起来,曾经给我讲过西弗森童话的母亲希望我是个小女孩;克里斯蒂娜·布拉厄死于第二次分娩,“是在生一个男孩时,而他朝着一种令人恐惧的、残酷的命运成长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一个死去的人。”母亲的姐妹英格博格在盛夏时被下葬在那里,她曾经告诉我:“仿佛一颗流星坠落而没人看见它,也没人给自己许个什么愿。”而当死亡降临,“那里全然被掩盖了,仿佛再也没有一个人坐在这张桌子旁,而我们确实全都相当舒展地闲坐着。”还有厄勒加德·斯基尔女伯爵,她是被烧死的,“在一场舞会前她想对着烛台照亮的镜子把头上的鲜花插成另一种样式。”还有外祖母玛加蕾特·布里格夫人,“当人们早晨发现她时,她已经冷得像玻璃一样。”
死亡总是带着记忆,它进入了和我有关的生命,而死亡之外呢?克里斯蒂娜·布拉厄从旁边走过,“只有唯一的一声呜咽划破这寂静像发自一条老狗。”还有那个和死亡同时发生的分娩过程造就的生命,变成了“想必会爆裂于纯粹的诞生”——死和生仿佛牢固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如英格博格所说的“封闭”的世界,“这一切在此停止,轻柔地似乎小心翼翼地停止于那个轻微的、从未补描过的轮廓,它封闭着她。”所以从这一些记忆里来,对于里尔克来说,再也无法逃避,甚至变成了欧维进入巴黎之后的一种情结:“可以肯定,我心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悲哀而沉重的自豪。我想象,我将会怎样四处漂泊,充满内心感受而且沉默。”
在巴黎的图利耶街廉价旅馆里,在六楼的写作中,在充满生存欲望的世界里,我只想起死去了559个死人的床,“上帝也许知道,为什么。我的旧家具正霉在一个粮仓里,别人曾允许我把它们放进去,而我自己,是的,我的上帝,我头上没有房顶,雨下到我的眼睛里。”毫无遮挡地发霉、腐烂,就像在塞纳河中死去的那个无名女人的脸,后来以她的面型作了墙饰,死亡仿佛变成了一种美丽的东西,和我在六楼写下的诗歌、小说以及书信一样,无非是在外部世界里,建立了经验、图像和事实,借以抵抗那些死亡,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被堆砌起来的自己,“我躺在那里,身上堆满了我自己,并等待那个时刻,届时我会受命将这一切重新分层堆放到我体内,按照顺序,有条不紊。”
一堵墙却也是分隔的开始,高大、厚实,甚至不可逾越?起先我是跑开了,因为那是恐怖的事情,但是回过来会发现它其实通向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便是那个不及物的世界,“我现在认出这里的一切,因此它们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内部:它们的家在我内部。”从死亡、病态、神秘和压抑的生存欲望开始,逾越一堵墙,是要摆脱虚弱者的命运,是要远离物化的恐惧,是要寻找没有客体的爱。其实,英格博格生之前所说的画里就有了那通往内部的进口:“千万不要忘记,给你自己许个什么愿,马尔特。祝愿,这个人们可不要放弃。我相信,不会有实现,但是有愿望,长久持续的愿望,整整一生之久,以至于人们恐怕根本等不到实现。”
谁会不求回报地许下愿望?谁会在内心世界里培植爱?“这里有些毯子,阿贝洛娜,壁毯。我想象,你在这里,有六张壁毯,来吧,让我们慢慢走过去。”阿贝洛娜是里尔克的小姨妈,在乌尔斯伽德的世界里,正是她让里尔克打开了阅读的世界,看见了纯粹的生命,体验了内部的爱。六张壁毯里的五张对应着五种感觉,它们是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并非是一种物的存在,才能激活这些感觉,而是它们本身就存在着,像爱一样,生成了图像,生成了经验,最后通过那堵墙进入内部,“我相信,每当我从书上抬起目光并外看去,那里是夏天,那里阿贝洛娜在呼唤。”
在里尔克看来,阿贝洛娜是“挚爱的女人”,是超越了被爱的人,“她的献身就像是无限的:这是她的幸福。她的爱的无名悲苦迄今为止却始终是这个:她被要求限制这种献身。”不是被爱者,是永恒的爱者,而爱所涉及的是纯粹的色彩,内心世界的阅读,本真的生命,它和对象无关,和目的无关,和呈现的物无关,就像阿贝洛娜曾经唱起的那首歌:
唯有你,你会一次又一次诞生:
因为从未抓紧你,我才把你留住。
从未抓紧你,才能把你留住,爱不是占有,没有客体,它只在不及物的世界里成为自己,但是这个不及物却又是及物的,那物是艺术之物,是美之物,“这仍然是可能的,阿贝洛娜在后来的岁月里尝试过用心去思考,以便悄悄地直接地进入同上帝的关联。”它像一道光,透过外部世界的空隙,进入到内部,从而以不在场的方式打开密码,就像里尔克1903年《致莎乐美的书信》中说:“物是确定的,艺术之物则须更确定;摆脱一切偶然,清除任何模糊,被解除了时间并交付给空间,它变得持久,能够企及永恒。”从人性意义上深化,触及美学和信仰,触及人的存在本质,“就是那个时期以此开始了,他觉得自己普通和匿名像一个在迟疑中刚复原的病人。他不去爱,除了爱这个:存在。”生存的欲望重新变成了存在本身,在迂回的过程中便建立了一种与自己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不仅仅是在生存内部看见自己,也看见了上帝——“我们的脸与上帝的脸望着同一个方向,乃是一致的”。
朝向一个方向,并非都是对于“持续的爱”的一种完美呈现,里尔克1912年2月的书信中就说:“我最近认识到,对于在自己本性的发展中变得敏感而乐于探寻的那些人,我必须给予严厉的警告:切莫在手记中为他们所读到的寻求相似之处;谁挡不住诱惑并与此书相偕并行,谁就必定走偏;而它兴许有人喜欢,也仅仅是几乎不随大流的读者而已。”受制于物的占有常常将“不及物”的爱变成手段,所以《布里格手记》标注的永远是属于自我那个造物主的“物”——从死亡到生存,从恐惧到爱,从外部到内部,从虚弱的被爱者到永恒的爱者,迂回而同一,对于生命的解读,是里尔克建立的一种象征主义,而只有在内部,它才是唯一的,无需抓紧,却能留住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