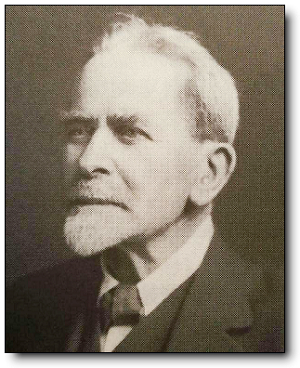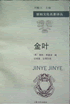|
编号:B56·2130520·0999 |
| 作者:詹姆斯·弗雷泽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2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88.00元亚马逊69.00元 | |
| ISBN:9787100088961 | |
| 页数:1247页 |
“金枝”缘起于一个古老的地方习俗:一座神庙的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却又能由逃奴担任,然而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他日夜守护的一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有资格与他决斗,就能杀死他则可取而代之。这个古老习俗的缘起与存在疑点重重,为此,J.G.弗雷泽的目光遍及世界各地,收集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的丰富资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并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展望。作为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阐释有关继承阿里奇亚狄安娜祭司职位的奇特规定,主要内容包括:森林之王;祭司兼国王;交感巫术;巫术与宗教;巫术控制天气;巫术兼国王;化身为人的神;局部自然之王等。
“该死内米的圣林中有一棵大树,无论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可看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在它周围独自徘徊。他是个祭司也是个谋杀者。他手持一柄出鞘的宝剑,不停地巡视着四周,像是时刻提防着敌人的袭击,而他要搜寻的那个人最后将要杀死他并取代他的祭司职位。
——《第一章 林中之王》
如果对着直射的光线偏离几度,银色的封面会闪烁出点点黄金的色泽,这一种色泽正好诠释了封面上“金枝”这个书名,当世界需要在角度的偏离中被发现,是不是反而将一种仪式化的命名隐藏在其中?“因为它本身就是金黄色的”,弗雷泽在蕨孢子里发现了黄金,但是他却认为这种金子般的性质是次要的,“保存它的人永远不乏黄金”,当那种金黄偏离了黄金般的诱惑,它其实是一种烈火似的闪光的隐喻,那么,所谓的仲夏节或者圣诞节,是不是就变成了古代异教徒庆祝的节日?
不管如何,必须从仪式开始,在被塑封包裹着的封面,无论如何也无法看见隐匿在光线之外的金黄,于是轻轻地撕去,缓缓地偏离,然后慢慢地打开,就是用一种手势和目光启动一个仪式,上下两册,精装本,1247页,即使是从十二卷本变成了两卷本的节本,弗雷泽十二年辛勤耕耘的这部著作,以它辑录的丰富资料,阐述关于巫术、宗教和科学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开创性研究,它一定是一部经典。用仪式来开启经典,就仿佛看见了如黄金一样的光泽,照耀我的阅读世界。
可是为什么会有“下让灵魂离体”的句子?为什么谷物女神的人称变成了“他”?为什么图宾根和图林根混用?甚至为什么从第405页到437页会出现太多的空白页——一页是文字,翻过去是空白,再翻过去是文字,又翻过去是空白,有文和无文间隔出现在文本里,那么无文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内容?当塑封包裹着的时候,你无法看见金黄的光泽,也一样无法发现这许多的空白,空白是缺失,是中断,是仪式的取消,是阅读的停滞——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竟然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错误。
前言中说,这本书最早由徐育新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但是因病谢世导致手稿散失,之后刘魁立邀请张泽世石和汪培基补译了文稿,所以这一本经典既有先前的旧译,又有遗漏的补译,而且不同的人翻译不同的篇章,也只是最后通稿而成,“译者水平有限,兼之参考书籍不足,疏漏舛误,在所不免”,我以为是一种谦虚,却原来变成了事实——或者其中字词句以及空白页的错误并不是译者的缘由,而是出版社粗心导致,但是当一部历史十余年创作的人类学著作以如此拙劣的方式被出版,那一种阅读的仪式感怎会存在?
而错误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种巫术在控制着?“总之,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弗雷泽注解了巫术之本质的谬误,而这种注解就在那不忍直视的空白中变成了怪异的文本。就像那个有着圣殿的内米森林,那个有着“狄安娜的明镜”的奇幻世界,那个闪烁着想象力金色光辉的“金枝”里,却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有着出鞘宝剑制造的谋杀,有着奇特悲剧的演绎。
意大利明媚的蓝天不见了,蓊郁的夏日林荫不见了,阳光下的粼粼碧波不见了,一切的和谐幽美变成了凄凉和死亡,变成了挽歌和悲剧,英国画家特纳的那幅浸透了非凡心灵的画作在那里?“树枝发出闪烁的金辉,好像严冬森林里的槲寄生——寄生在大树上的植物,绿叶扶疏,金黄果实,绕树累累——似乎是浓荫圣橡上的茂叶金枝,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维吉尔的诗歌在何处?那么回到既存的文本里,回到弗雷泽的世界里,以想象来弥补缺失,“正是这种习俗的粗暴和野蛮,使人们产生想要解释它的期望。”粗暴和野蛮的习俗是关于奇怪的祭司承袭制度,而在展开之前,它的确是风景秀丽的,是幽静和谐的。内米的这片森林是出于对狄安娜的崇敬,一个传说是这样将这片森林变成了狄安娜的圣殿,迈锡尼王阿伽门农被妻子和妻子的奸夫杀害,他的儿子奥列斯特便由姐姐送到了父亲好友处收养,奥列斯特长大后杀死母亲为阿伽门农报仇,但是被复仇女神追究,于是女神雅典娜解救了他,宣告他无罪,并且在回国后让他继承了王位。而在这过程中,奥列斯特曾经和姐姐逃到了意大利,他们把狄安娜伸向藏在一捆柴禾中随身携带。奥列斯特死后,他的尸骨从阿里奇亚运往罗马,葬在卡彼托山坡上康科德庙旁的萨图恩庙前。
狄安娜的崇拜由奥列斯特创始,在意大利的这片内米森林中就建有圣殿,而在圣殿附近有一棵特殊的树,它的树枝是不允许砍折的,只有逃亡的奴隶才被允许折断,而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有了和守卫圣殿的祭司单独决斗的机会,如果能杀死祭司,那么她可以接替祭司的职位并获得“林中之王”的称号,而这根决定命运的树枝就是“金枝”。对狄安娜的崇拜,使之成为一个圣地,祭司之存在,就是维护这种神圣的地位,但是为什么祭祭司承继制度必须以死亡的方式延续?为什么这闪耀着金色光辉的森林会成为悲剧的场所?所以弗雷泽从传说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内米的狄安娜的祭司,即林中之王,必须杀死他的前任祭司?第二,为什么这样做之前他又必须去折下长在某棵树上的、被古代人公认为就是“维吉尔的金枝”的树枝?
|
|
“这类故事包含着一个更深的哲理——即是关于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可悲的哲理导致了悲剧性的行为。”副标题“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弗雷泽就是从这个悲剧性行为出发,探讨巫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世界充满了一种神力的观念,而未开化的人则在关于自然法则观念形成胚芽之前,却先期出现一种巫术观念,他把巫术分为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而不管是那一种都是交感巫术,通过一种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而这个传输过程,是一种纯粹是“联想”的错误应用,它以歪曲自然规律的方式建立体系,又以谬误的行动建立准则,不管时积极性的法术也好,还是消极性的禁忌也罢,巫术“一种奇怪的应用是对受伤者实行法术。”
但是当个体巫术过渡到公众巫术,当部落的福利造就了巫师,当巫师具有了影响和地位,取得了和首领或国王一样的权势,其实就变成了“人神”,而这标志着早期宗教的产生。更具巫术意义的人神是一个凡人,他拥有不同一般的权力,比如在控制天气时会用仪式来求雨,这种权力是小范围的,但是当从巫术的人神变成宗教的人神,凡人则变成了不同于人却超于人的存在,而且是化身在一个人体里,通过血肉之躯做出的奇迹和预言来显示超人的威力和智慧,肉身只是一个脆弱的、尘世的、寄居着不死神灵的驱壳,他的神性来自神祇,于是这种人神就变成了宗教意义的神——巫术以一种非人力量控制着具有人格的对象,而宗教作为一种“对超人力量的邀宠”,统治世界的力量是有意识的,是具有人格的。
巫术信仰呈现了单一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宗教信仰则呈现了无穷多样性和多变性,这是一种发展和过度,弗雷泽认为,其实巫术和宗教具有某种同源性,甚至巫术和科学一样都是“自由与真理之母”,因为巫术“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而在同源性之外,巫术和宗教却也形成了冲突,弗雷泽认为:“巫术与宗教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抵触,足以说明在历史上为存在祭司经常追击巫师的这种毫不放松的敌意。”
当巫师从个人意义发展到公众意义,从非人力量控制变成人神控制,他拥有了和国王一样的权势,而正是这种权势,国王变成了祭司,也变成了作为人神之间的中介而受到尊崇的神灵。当人被赋予神性或超自然力量,巫术便退居到了后面,甚至沦为了妖术,而宗教信仰便开始在祭司的世界里形成了祈祷与祭祀的仪式。树身崇拜就是仪式之一种,那种人神的力量也延伸到了自然界,凡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都具有了灵魂,弗雷泽认为,这是人类宗教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树木从树神的身体变成树神灵魂随意居住的住所,是由泛神论到多神论的转变——无论是人还是树木,或者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一种神,而这种神就在狄安娜崇拜中具有了繁殖和婚姻的意义,“她经常被比作希腊的阿尔忒弥斯,总管自然的女神,特别是生育繁殖女神。既然原则上繁育女神自己必须是能繁育的,所以狄安娜应该有一个男性伴侣。他们结合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促进大地、动物以及人类的繁殖。”
生命之繁殖,象征着王位的嬗替,于是在罗马就有了通过竞赛赢得新娘的“奔逃”仪式,甚至演变成了在殊死决斗中获得王位的做法,神的代表“很容易被废黜或死于任何能以铁臂利剑证明自己有神圣权利居此王位的勇敢者的手下”。当然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当国王和祭司拥有了超自然能力,那么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公众利益,“他是世界平衡的支点,他身上任何极微小的不合常规的地方,都会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于是这种“王位的重负”便有了国王和祭司的禁忌,禁忌包括不能露出面孔、不能离开王宫等禁忌的行为,包括酋长和国王、悼亡人、战士等禁忌的人,包括铁器、血、头发的禁忌等禁忌的物。
这种禁忌象征着灵魂可能遇到的危险,“我们必须知道威胁这位国王生命的危险的实质,那些奇怪的限制正是要保护国王免遭这些危险。”也正是这种免遭危险的观念,出现了“杀死神王”的信仰,在他们看来,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人注定是要死的,那么人的创造物也处于同样可悲的境地,“此处是死去的狄俄尼索斯,塞墨勒的儿子。”狄俄尼索斯墓碑上的这句墓志铭,正是表达了神之死亡。而当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杀死神王变成了对于灵魂走向危险的一种救赎,“人、畜,以及植物的繁盛据信都依赖于神王的生命,并且神王都死于非命,不论是单独械斗或是其他办法,为的是要使他们的神性传给精力充沛的、未受老病衰颓影响的继承者,因为,在神王的崇拜者来看,他如有任何这类的衰退,就会引起人、畜和庄稼相应地衰退。”同样,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生命,都有灵魂,所以也必须处死衰老的树神。
避免衰老而处死,并不是制造死亡,而是避免灵魂的危险,同时实现神灵转世的目的,就像在希卢克人,“杀死神王的做法以典型的方式流行着,他们有一条基本信念,即该朝代的神灵创者的灵魂存在于每一个被杀的继承者身上。”也就是人神的死亡是为了复活,“这绝不是神灵的消灭,不过是神灵的更纯洁、更强壮的体现的开端。”无论是阿多尼斯的祭祀仪式,还是阿帝斯的神话的祭祀仪式,无论是东方诸神,还是西方宗教中的神,无论是女神伊希思,还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都在死亡中复活,都形成了一种神的复活仪式。而在杀死神性动物仪式上,还有一种转嫁灾祸的作用,达到驱邪的目的。
所以到此为止,弗雷泽关于米内森林里的祭司要杀死前任的做法有了合理的解释,“这样,通过强壮的替身连续他一脉相承,神灵生命就可以永葆青春年少,这样也就保证了人畜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持青春,播种和收获、春天和夏天、雨水和阳光,也永远不会失调。”那种恐怖和悲剧就变成了复活的仪式。但是为什么祭司要折下金枝才能杀死祭司呢?弗雷泽从北欧神话人物巴尔德尔那里得到了启示。巴尔德尔是善良美丽的神,他是诸神中最聪明、最温和、最受爱戴的神,但是在死去而复活的信仰中,如何让他死去?在众神大会上,瞎了眼的神霍德尔用槲寄生树击中了巴尔德尔,把它刺了个穿胸透,倒地而死。”
在欧洲,槲寄生一直是迷信崇拜的对象,他们相信这是上帝选中的东西,一旦发现他们就举行隆重的仪式然后采集,而且采集者必须是身穿白袍的祭司,他爬到树上将槲寄生割下来之后,人们在树下用白布接住,之后就献祭牺牲,祷告赐福。但是弗雷泽提出了有一个问题,如果说神的生命寄托在槲寄生里面,那么他又怎么会被槲寄生击中而死呢?他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的死亡系于某物体之内,那么用该物击某人,某人就必然死亡,这就十分自然了。”而这种击中的方式在他看来是天神朱比特乘着闪电降落在人间时制造的崇拜,也就是雷电寄生在金枝中,所以本身的金黄色,是一种像烈火般的闪光,而不是蕨孢子里的黄金。
杀死神王是为了复活,复活是为了承继,人神观念已经超越了巫术而具有宗教意义,而金枝作为槲寄生之存在,在仪式中也变成了对于自然现象的神化解读,巫术是联想的错误应用,宗教是人类对于神的委身,巫术是假定自然界现象具有不变的规律性,而科学是在假说中寻找规律性,于是巫术、宗教和科学都变成了一种关于思想的论说:“科学取代了在它之前的巫术与宗教,今后它本身也可能被更加圆满的假说所更替,也许被我们这一代人想象不出的、写记录宇宙这一荧幕上的影像、看待自然界一切现象完全不同的方式所更替。”他用黑线表示巫术,用红线表示宗教,用白线表示科学交织起来的王,人类的思想就是在这不同的纺线中编织了一个复杂却多彩的网,当林中女神的殿宇已荡然无存,林中之王也不再守卫在金枝之旁,但是在内米的丛林里,那晚祷的钟声,国王驾崩的消息,似乎还穿过罗马的平原和沼泽,在人类的世界里成为不断探索自由和真理,不断在思想的道路上前行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