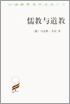|
编号:B82·2200918·1682 |
|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49.00元当当25.00元 | |
| ISBN:9787208161863 | |
| 页数:176页 |
《批判施塔姆勒》是马克斯·韦伯对鲁道夫·施塔姆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观念与法律观念:一项社会哲学研究》一书所作的细致评述与批判,也是韦伯继《罗雪尔与克尼斯》之后又一重要的方法论(元理论)著作。在对施塔姆勒的批判中,韦伯意在通过考察社会文化科学领域之一的法社会学的逻辑特征,来维护自己有关解释性社会文化科学,也即秉持理解论题的社会文化科学的观念。本书揭示了许多关键联系:《罗雪尔与克尼斯》专著与《经济与社会》的问题意识之间的联系;韦伯的方法论与当代诸多方法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包括彼此交叠的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诠释社会学以及日常生活社会学等学说。韦伯认为,任何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在五十年内必然会过时。这是科学进步内在辩证的结果,也是科学分工日趋精细的结果。但韦伯方法论(元理论)著作背后的意图,是要去发展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研究逻辑,一种可以定义社会文化科学主题、问题、方法与理论宗旨的新范式或问题意识。
《批判施塔姆勒》:消失在真理的丛林中
他的全部学说都是基于“自然”与“社会生活”这两种对象之间绝对严格且互斥的概念区分。因此,反思一下什么是“自然”,对施塔姆勒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
——《施塔姆勒的“知识论”》
施塔姆勒的著作缺乏科学依据,施塔姆勒的目的是为了自命不凡,施塔姆勒提出观点的作用是制造混乱,施塔姆勒的研究方式是“学究式做派”,以及施塔姆勒的论辩模式就是“退回到僵化的经院哲学”——这个犯了幼稚错误、自称是“认识论者”、被驳斥的施塔姆勒到底是谁?他无非是站在韦伯对面的一个人,无非是韦伯眼中的一个人,当韦伯“批判施塔姆勒”的时候,是一种经验论还是一种概念论?是将其当成是一种“自然”存在,还是当成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
新康德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的施塔姆勒,作为韦伯批判对象的施塔姆勒,这是不同维度的施塔姆勒,或者可以将他们分别命名为本体和对象、形式和内容——一种被严格区分的存在?就像韦伯批判时界定了自然和社会生活的不同概念一样,他也认为施塔姆勒的著作宗旨就是为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科学做出“绝对的、确切的区分”,这种二元划分的有效性,就是为了从与自然的分野中发现“社会生活”的特性,发现“社会生活”这个概念的构成属性。所以二元划分不仅在施塔姆勒的著作中有着有效性意义,在韦伯对施塔姆勒的批判中也具有认识论的作用。
不妨从施塔姆勒作为本体存在的维度开始,寻找他二元划分的逻辑基础。作为德国法学家、新康德主义法学派的首创人,施塔姆勒第一个提出了“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概念,在他看来,自然法的存在是基于法律内容不断变化发展的观点,“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日新月异的自然法”,法律内容的可变性,意味着它不具有普遍妥当性,但是法律形式具有普遍妥当性,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法律不是表达任何必然的东西,它的基本意义就在于按照人们的意愿规定“应当”实现的东西,所以法律是社会的一种形态,经济则是社会的实体,形式不依赖于实体,实体却要依赖形式来规定自己的属性。由此施塔姆勒认为存在着一个法律理想和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就是“自由意愿的人们相互结合起来的团体”,在社会生活这个概念里,法哲学是社会科学的“构成性概念”,即“基本概念”,因此,一切为社会科学确立认识论基础的尝试,都必须从分析这个概念开始:什么是社会生活?其构成属性是什么?在哪些条件下,一个既定事项可被视为社会现象?
在施塔姆勒看来,社会生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共存模式,是被视为应然世界中的对象在相同时空中的共存,“这里,我们寻找的关键因素是某种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社会生活被界定为知识的某种特殊对象。”施塔姆勒认为,“这种标准就是:人类根据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调控相互交往与集体生活。”从这个标准出发,施塔姆勒认为,规则就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现象,受规则支配的这种属性,使现象能被界定为社会科学的对象。社会生活的共存性、规则性意味着它和自然科学一样,背后的逻辑就是一种客观原则,只不过自然科学手因果律支配,社会科学受目的论支配。这是施塔姆勒学说在本体意义上的阐述,但是当施塔姆勒进入到韦伯的视线,当他成为韦伯的批判对象,文本批判中的“施塔姆勒”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施塔姆勒正是以这些东西来达成其自命不凡的目的。他这本书中那些有价值的元素,消失在表面真理、半吊子真理以及被错误表述的真理的丛林中,隐藏在暗含虚假的模糊表述中,被诡辩与学究式谬误所掩盖。”韦伯1907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上的这篇题为《施塔姆勒对唯物史观的“驳斥”》的文章,一开篇就对施塔姆勒进行了盖棺定论,当施塔姆勒以自命不凡的方式使有价值的观点消失在“表面真理、半吊子真理以及被错误表述的真理的丛林中”,韦伯是不是反其道使隐藏在虚假、模糊表述中的价值元素重见天日?首先,韦伯从施塔姆勒的著作出发,认为他的宗旨是科学地驳斥“唯物史观”,那么,就应该对唯物史观提出两个问题:施塔姆勒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观?施塔姆勒对这种历史观所做的科学批判有何确切理据?
施塔姆勒批判唯物史观,在于他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其他变量可以追溯到宗教态度变化上来,这种自然法的可变观念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但是在韦伯看来,宗教因素是社会生活唯一的因果动力,也是单一因果观念,将单一因果观念推进到综合观念形成某种总体性知识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人为分离出来“试图再现历史结构”,被确立的总体性则是一种虚构——韦伯更是仿照施塔姆勒的行文风格,将文中的“宗教的”一词代以“唯物的”,在他看来,插入后的那些段落、改变后的文字就是施塔姆勒对唯物史观的看法——施塔姆勒试图证明,只有在“目的世界”中,社会生活与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的“根本统一”才会形成一个“形式原则”,从自然科学的因果论到社会科学的目的论,韦伯认为施塔姆勒是通过“一系列概念的操作”才得以完成的,虽然不是错误,但也是不完善,“概括,作为一种确立理论知识的方法,乃是基于一种假设:存在着一种终极的、统一的观点,也即问题意识,必须根据它来揭示社会生活终极的、根本的统一,否则理论知识就不可能。”
所以韦伯认为,重要的不是施塔姆勒的唯物史观问题,而是他所秉持的“知识论”提问。在施塔姆勒的书中,韦伯发现了十个命题,几乎每一个都用到了“法则性规律”这个概念:施塔姆勒认为个别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它是一般性法则规律的因变量,除非它是“普遍有效的知识标准”,除非它“建立在基本的法则性规律”之上,除非它是基于一个“统一的、绝对的问题意识”,除非它是基于对“普遍有效的法则性相关”的洞见……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像自然科学把自然的法则性规律作为自身基础一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确立一般性的法则性规律?”施塔姆勒遗憾地认为,目前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也就意味着,在施塔姆勒看来,法则性规律的科学知识“作为条件使得以法则般的方式来建构人类集体生活成为可能”。
这就是施塔姆勒的“知识论”,他提出以法则性规律来统摄社会生活,让社会生活的“终极法则性规律”流溢到“有关个体与总体间关系的根本观念中”,从而调控相互交往与集体生活,使之与自然科学一样在这种客观原则支配中被认识被构建。为此,韦伯认为,“施塔姆勒欺骗了自己”,施塔姆勒用语的含混性造成了对概念的误读:陈述纯粹“事实性”不是经验-科学命题的“有效性”,统一问题仪式也不等同于科学的“法则性规律”,所谓的目的论或者只是一种价值论——它是经验的还是概念的?它是法哲学问题还是历史问题?
这些疑问让韦伯在批判施塔姆勒时开始阐述他所认识的规则概念,对比施塔姆勒将规则概念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属性,韦伯则认为,规则只能被视为一种经验准则,它既具有因果效力,又能被因果地说明,它是规律,是规范,也是准则,甚至韦伯将规则视为一种“游戏规则”,他举斯卡特纸牌为例,认为这种游戏就是历史产生的文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一方面,玩家会遵守游戏规则,会在规范性准则中完成游戏,但是上升到法则性规律概念,一个问题是,当玩家出错了牌是不是就是输?沿着这个问题可以揭露背后的各种问题:玩家为什么会出错牌?他是不是故意的?而这些问题都变成了纯粹的经验问题,是“历史”问题,某个玩家玩得“好不好”,则是一个价值问题——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价值问题,都可以根据经验概括来解决,所以斯卡特纸牌游戏中包含着实践理性,包含着经验命题,甚至斯卡特纸牌游戏还会充斥着规则之外的环境因素,比如玩家会吸烟、喝啤酒、拍桌子……
由此,韦伯认为,生物从纷繁多样的事件和过程中做出选择,他们选择是那些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东西,所以,“经验的东西与规范的东西之间始终有可能混淆,毫无解决希望,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韦伯认为,法则性规律只是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当社会生活形成之后,它更多的是进入到更多主观性的经验领域,而且作为前提条件的法则性规律和真正的法律经验存在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法律经验存在更多体现的也是“价值有效性”,从这里韦伯得出结论,“法律规则的确不是社会生活的‘形式’——无论在概念上如何定义社会生活这个概念。”它就是实验存在的一种客观要素,一条准则,“是一切既定情况下大多数人的经验可见行为的一个因果决定要素。”——而回到施塔姆勒的观点里,韦伯认为他在著作中就是使用了诡辩术,故意混淆了规则般、受规则支配、法律上手规则支配等概念和说法,也让法律规则和经验现象、应然与实然、概念与概念的对象“始终在变来变去”。
当然对施塔姆勒的批判,作为“科学纯粹主义”的代表,韦伯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只有自然科学才能拥有精确性和客观性,而在文化科学领域,即在目的和规范领域,一切都是主观的。当韦伯认为施塔姆勒没有把握住“法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他就是为自己的观点阐述留下了一个进口,具体情况指向的是经验现实,经验现实面对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主体就是每个人,所以施塔姆勒所谓的客观性的“社会生活”概念,在韦伯看来,应当包含着与“自然”及他们相关的“一切人类行为”,在知识世界里,能知之外还有所知,主体之外还有知识的对象,而且韦伯认为,经验现实中还有所谓“更高的人”的功能构成,如此,规则便不只是经验事实层面的,而是观念意义上的。
把施塔姆勒看成是职业法学家和哲学上的票友,认为他的认识论判断很糟糕,甚至把他的方法论看做是“某些类似方法论瘟疫的东西在我们的学科内盛行”,韦伯的批判显然有着人身攻击的影子,但是作为一个反笛卡尔社会学家,韦伯把社会文化学科看成是一个竞技场,只有在各种方法、基本概念和前提假设的争斗中,才能实现“问题意识的永恒流变和概念的不断重新定义”的目的,而价值多神论的意义就是在诸神和魔鬼之间永不消解的斗争中形成现代文明的“现代性”,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构成属性,关于社会文化的问题范围,关于社会文化的科学理论宗旨和社会文化科学的方法之争,韦伯的这些界定性问题之争,或许就是为了在流变和重新定义中,在危机和怀疑中,走出迷失状态,而把施塔姆勒看成是批判对象,在某种意义上,韦伯也在这样的争斗中找到了“极强的刺激”,“要论证这样一本书缺乏科学依据,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但这却正是我们此处要做,且必须带着充分真诚去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