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08 风穿过了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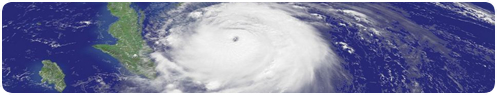
身体却一直在风之外,不被侵扰不被吹拂,当然更不会被击穿。这是风的世界,风的传说,以及风的暴戾,活生生地摧残,活生生地剥夺,活生生地拖走了那些平静,就如一种描写:“像一支侵略军,从内地,从安第斯山来的。朝着海洋一路扫去……”
是台风,之后的超强台风,威力在增强;之后再变成台风,以及之后的强热带风暴,热带风暴,威力在减弱。这个过程仿佛最初是个孩子,出生,成长为茁壮的人,然后又慢慢变得苍老,然后死去,销声匿迹。一个过程,一种路径,24小时或者72小时,黄金时间或者威力最猛的时间,一切都在等待,以及等待之后的抗击,三部曲不变,总节奏不变,最后的结果,却是,台风并没有穿过我的身体。
现实没有?那么这个句子可能是个诗歌中的一句,是一首诗里的情绪,风在别处,一定会狠命地击破身体的阻挡,断裂成无数的碎片,风无形,如火,风无色,如水,却穿透现实的每一个角落。在黑夜的深处,吹来。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在现实的某种不眠中,身体正带着未知的痛,所以不在痛中穿过,只是如一首诗一样,被阅读被阐释被押韵。不是故意要听出什么声音,摧毁的还是欢快的,耳朵早已经睡了,醒着的只是一种形式,多年来就是一种形式,喜悦的形式,骚扰的形式,安静的形式,吵闹的形式。
竟是梦里的声音。有一些微的呻吟,很远地传来。风之为风,就是它会哭会笑,会发出我们听不懂的声音。悄悄地逼近,悄悄地展开,声音里有些令人害怕的东西,风没有透明的身体,它隐藏着秘密,黑暗中不见的阴谋,不见的路线和力量。以为是缓慢逼近,却是气势汹汹,狂风暴雨而来,飞沙走石而来。“他是爱,是未来、力量与爱情;站在疯狂与与烦愁之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掠过风暴的天空和狂乱的旌旗。”这是“精灵”,爱的极致,还是在诗人的笔下,掠过的天空中是狂乱的旌旗,还有狂乱的树枝,狂乱的飞鸟,甚至是狂乱云,狂乱的雨。力量充盈其中,可以将一切的阻碍都击碎,何况小小的身体。
一定是害怕了,我以身体的投降说明耳朵的沉睡。梦中结束的故事没有终点,风也没有终点,它在寻找归宿,寻找落脚的大地,就像那只鸟,本来是可以永远飞翔的,但是为了寻找大地它希望站立下来,却原来是最后的死亡,停下来就是最后的归宿,万劫不复的“身体寓言”。所以,尽管是摧毁,尽管是威力的体现,却是它赴死的开始,无可逃避。
海洋之于陆地的命运,运动之于静止的命运,台风只是从黑夜深处找到落脚点,找到自己不断消耗自己的那个起点。登陆,所谓的从海洋到陆地,从运动到静止,所以它的行走只是一场行为艺术,一场赴死之前的表演,终究是要走出这一步,向着未知的方向而去。而风之为风,就在于它能看见什么,能识别什么,能绕过能击穿能迂回,柔软的风,能把树变成它自己的形状。
而我的身体不被穿过,也就不曾感受风在肆虐在寻找自己最后归宿的努力,只居于一室,安静的梦境里没有起伏,然后就是远离中心,远离台风,就想远离一种诗歌的情景,“那台风的眼穿过台风/那和平的沙子从战争里漏掉”,这是更宿命的过程,台风制造了台风眼,却走向极致,走向相反的那个起点,世界本来就是安静就是水样的柔软,多一点“世界的血”又何妨?那么它就真的来了,透过窗户和门,透过那些树叶变动的叶缝,世界变得摇摆不定,甚而至于,一切都在大幅摇晃之中,树被吹倒,洪水肆虐,还有泥石流,灾难的世界,因为这无足的风,而变得残酷。
所以,风是一定要穿过身体,人的身体,或者风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走进自己感受自己对话自己,才能在风中找到风摸到风杀死风。最后一定是一种自杀,无影无踪,它带着大地上很多不能实现的故事,带着离开的人,游荡在属于它的自由世界里。超强台风,台风、强热带风暴、热带低压,如此循环便是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次自然过程,只不过几年一遇让我们淡忘了很多时候,他并不会击穿你的身体。
沙子漏掉了,风穿过了世界的身体,潇潇雨歇,我的身体还在风之后继续成长,就像一个词语,长在一种风样的故事里,坚强、诡异,以及自我毁灭。身体终究是一个可以被逃避的住所,风只是经过,抚摸而已,然后离去,就像不曾来过一样,让身体平静地听雨的声音,听沙漏的声音,以及大地断裂的声音。
身体外的洪水猛兽,真的吞噬了我们,空留下一个挣扎的影子。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812]
顾后: 子午伦敦眼⒀:三驾马车谁扬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