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8《迷人之星》:当爱作为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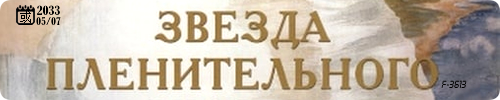
没有中文字幕,但有中文配音,167分钟的电影是一部长篇巨制,引入中国内地由上海译制片厂译制完成,当通过配音构建对话、塑造人物、展开剧情,这一基础之上的理解多少变成了一种“辨识”:电影所涉及的是三对恋人,但是形象的辨识度并不高,也就是容易造成混同感——除了波莉娜形象有些特别,再加上她随身带着一条狗,而且她的身份是法国女孩,而和波莉娜发生故事的伊万当然也有了辨识度。但是同样美丽的卡特琳娜和玛利亚就容易造成误解,还有他们的贵族丈夫,伏尔康斯基、特鲁别茨柯依公爵也很难分辨,当他们通过“配音”而讲话,伏尔康斯基公爵由童子荣配音,当然就有了辨识度。
如此观影,的确太累,个体似乎就湮没于群体之中,而这部弗拉基米尔·莫德尔导演的电影讲述的正是一个群体的故事,开场旁白说:“君主制在欧洲摇摇欲坠,天翻地覆的时代快到了。”这是对于那一段历史的描述,之后便是献辞:“献给俄罗斯的妇女们!”“俄罗斯妇女们”就代表了一种群体存在,莫德尔所选择的也是三位女性的故事,而和她们相关的则是身为丈夫的“他们”的故事,无论是她们还是他们,都构成了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故事,个体形成的群体成为对那个时代的解读,但是在这种叙事中,莫德尔既要讲述不同个体的遭遇,又要将他们纳入到时代之中,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个体故事是不是就具有一种独立性?为什么选择不同的个体?
在三个故事中,波琳娜和伊万的故事就像他们的辨识度一样,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尤其是他们的相识和相爱,他们面对身为贵族的母亲的态度,以及母亲对波莉娜作为法国女孩的“偏见”,讲述得都比较生动,而当伊万成为革命党面临囚禁,他断然拒绝了波琳娜和他结婚的想法,“我应该和同志们在一起,你不可能当犯人的妻子。”伊万让她忘了自己,爱成为了无法跨越的鸿沟,但是波莉娜没有放弃,一方面她找到伊万的母亲,想要她出面去解救伊万,在母亲拒绝之后,她又决心去西伯利亚找他,而母亲最终也被波莉娜所感动,她冷坐在一旁,然后摸着眼泪,让波琳娜留下来陪自己,“我身边都是妖魔鬼怪。”这是母亲第一次放下姿态,在那一刻她是母亲,她更是柔弱的母亲,而波琳娜已经做好了去西伯利亚的打算,眼前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变成了过眼云烟。而当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西伯利亚矿区,看到了伊万,历经波折的婚礼在冰天雪地中上演,即使伊万再次被戴上镣铐,即使伊万重新变成一个囚犯,但是对于波琳娜来说,“我很幸福。”
| 导演: 弗拉基米尔·莫德尔 |
虽然玛利亚和卡特琳娜的故事有着各自的讲述方式,他们的家庭不同,丈夫的作为不同,去往西伯利亚的阻力不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缺乏辨识度,反而造成了一种同质化的倾向,而这也许就是整部电影最大的问题。莫德尔基于群体叙事表达了女人们对丈夫的深厚感情,但是三对夫妻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他们很少有交叉,故事就构成了一条条的支流,甚至变成了互不干涉的文本,甚至直到最后在西伯利亚也没有汇聚成一条线,这就明显削弱了“妇女们”这一群体所需要构建的情感逻辑——不如将波莉娜的故事作为叙述的主体,然后再以旁支的方式讲述其他女人的故事,就不会变成平均主义叙事模式。
电影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将“妇女们”和“丈夫们”并置,同样犯了平均主义的问题。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是时代背景,而在尼古拉斯一世上任之后举行的武装暴动自然就变成了男性视角下的故事,从沙皇统治下的贵族变成革命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推翻专制统治,就是结束奴隶历史,“他们不知道该忠于谁,是皇帝还是宪法?”但是举起武装暴动旗帜的他们知道该忠于谁,“沙皇是国家公敌”,尽管是立宪还是共和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但不管是立宪还是共和,都必须推翻沙皇统治。电影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讽刺了帝制,当革命失败,很多革命党人被抓捕,其中重犯面临着绞刑,但是绞刑架是临时搭建的,而且是用瑞典人建造,于是出现了绳子太短,木板没有固定牢的问题,甚至在实施绞刑的时候,绳子直接就断掉,犯人没有死,从塌陷的绞刑台上走上来,他嘲笑道:“我为自己死两次而感到高兴。”于是犯人再次执行绞刑。这一幕变成了对历史的讽刺,“可怜的帝国,连像样的绞刑架也不会做。”
重刑犯从“绞刑架”下掉落,这是对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反讽,而在男性视角中,并不够构成重刑犯的革命者,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他们不再以身份作为追求的目标,“有这个一个典故,陛下,它提出了一个很可恶的问题。 欧洲有个皮鞋将造反,是为了想当贵族富翁。可我们的那些出身贵族的革命家,为什么拼命往皮鞋匠那儿钻呢?”他们以前是贵族,有着公爵头衔,可以享受土地、财产和奴隶,这一切构成了沙皇赐予他们的“恩情”,但是革命之后他们不仅失去了这一切,还戴着镣铐成为了囚犯,而流放西伯利亚意味着他们再无回来的可能,由此他们就拥有了一生无法再改变的身份:农奴。从贵族到农奴,他们付出了代价,但是他们却撼动了沙皇的通知,为建立平等世界开辟了道路,所以男性叙事更多表现了他们对革命的坚决,表现了他们自我牺牲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革命信仰,它代替了对于沙皇的愚忠信仰。
如果说男性叙事是一种英雄主义,那么“妇女们”则强调的是爱情的信仰,她们没有革命意识,也没有付诸实践,可以说就是一种对丈夫的爱,但是在电影中,莫德尔只是在平均主义叙事中以闪现的方式再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并没有在刻骨铭心的意义上阐述爱,但是爱却成为了他们前往西伯利亚的动力,这似乎就有点哗众取宠了。不过莫德尔让女人们通过“在路上”的遭遇将爱的信仰得到了升华,他们面对的是贵族家庭的反对,面对的是遥远的路途,便对的是不测的雨雪,更重要的是沙皇颁布的法律规定,妻子们再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他们将和囚犯丈夫永远在西伯利亚,而且一切的荣誉和身份也将失去,甚至他们的孩子也永远是农奴,在这一残酷的命令面前,她们并没有放弃,等了6个月、去了11次“省长”办公室的卡特琳娜面对省长对她的劝告甚至威胁说:“只要能去,怎么都行,给我上铐吧”而当她行走一万四千里来到矿山,见到了空洞里满脸胡子的丈夫,亲吻着丈夫的镣铐,“宽恕他吧!”卡特琳娜向着上帝祈祷。
男性叙事占了大半的篇幅,女性的回忆占了女性叙事的一半,而真正讲述她们做出痛苦抉择去往西伯利亚的过程只有很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她们在西伯利亚之旅中坚守爱的信仰,成为真正“迷人之星”只有最后结尾部分,这种虎头蛇尾的叙事方式让电影的主题变成了说教,“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政权的废墟上;将会写下我们姓名的字样!”

《迷人之星》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