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5 身体里的“内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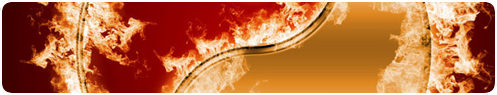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黄帝内经》
不是圣人,也不是真人,只是一个病人。所谓阅读,最后也变成了浏览,变成了翻阅,文字在里面,打开那些篇章,似乎就是打开自己的身体,打开已经病态的身体,所以从自身出发的一次检阅,到最后以一种非文本的方式介入到生活,介入到身体。
从《素问》到《灵枢》,从上册到下册,《黄帝内经》摆放在书桌上,从一开始充满诱惑的探知,到有些难受的关闭,并非只是一套介绍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的文本。里面有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藏象经络”,有阐述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以及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的“病因病机”,有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的“诊法治则”,有养生防病经验的重要总结的“预防养生”,有研究自然界气候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的“运气学说”。只是这些理论和实践,在那些充满生死的预示中,让人看见某些和自己有关的文字,仿佛一下在刺进了我的身体。“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慄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这是阴阳所逆,其实也是身体反常的一种病理阐述,所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虽然《黄帝内经》讲到如何不得病,甚至是在如何在不吃药的情况下能够健康,所谓“治未病”,就是在天人合一中发挥“天真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而其实这样的论述只是理想状态,或者是一种虚构,“圣人”当然是撇开“已病”,调养和调摄未患病的机体只是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假设。而在这些文字的阅读之中,身体还是存在着,甚至那隐隐的感觉也在现实深处无限逼近疾病。
春节的到来,似乎开始将自己置于健康的状态中,终止了那黑涩的中药,也开始满足各种食欲,甚至饮酒。这只是一种理由而已,其实远远没有实现对这些禁忌的突围,暂时的状态虽然没有出现某种直接的病症,但是按下暂停键的时候就知道还是要回到这个轨道上来,而这《内经》似乎开始提示我,被搁置的身体需要再次用一些行动来唤醒,而这种唤醒在“治未病”的翻阅中带上了某种不安和忧虑。其实,今年的春节是最糟糕的,时间被切割,在各种加班、值班中成为碎片,甚至在某些荒诞而荒唐的指令中被肢解,从正月上班到现在,还没有休息过一天,今天又是起早赶去开一个会议。
不是《内经》刺痛我,是不能改变的现实刺痛我,所以即使昨晚九点入睡,今天午睡到下午三点,身体依然像不在自己身上,感觉到无法摆脱的困顿,而从今天开始,一切的暂停状态都将恢复,晚饭又回到小半碗的状态,酒当然也不能喝了,而且在小径上行走,也从断断续续、散乱回到了必须完成22圈的魔鬼状态。其实原本走个10圈、15圈,也是微微出点汗,虽然距离22圈并不远,但似乎这是一个临界点,当晚上用几乎一个小时走完,才发现进入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体状态,除了出汗量大小不同外,身体的确感到疲乏,甚至肌肉、筋骨开始有了明显的不适,特别是双腿的肌肉,酸痛得很,甚至下腹还有坠痛的感觉。
寒冷的冬天开始让身体回归到原有状态,在《内经》上似乎也是一种违逆,所谓冬藏,也是为了保护精神和元气,但似乎只能在这种悖论中开始身体行为,因为我不是圣人,不是真人,只是一个被身体之忧围困的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797]
思前: 没有相遇的强迫症
顾后: 《红高粱》:生命膜拜的红色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