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7《节日的准备》:春梦了无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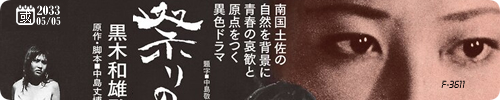
利广把借来钱还给了楯男,利广把楯男送上了去往东京的列车,利广跟着列车奔跑,突然喊出了一句“万岁!”——关于送别,关于逃离,关于寻找,于是就有了一种经典的书写:一个身无分文的男人,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为什么要喊出格格不入的“万岁”,它的口号性是不是完全脱离了时代和现实?
因为利广送别的正是想要离开这里的楯男,而迫切需要离开的何尝不是自己,“有的人像我一样,想回回不去,也有人像你一样,想要往外跑。”这是利广在听说楯男想要去东京时说的一句话,和“万岁”的经典画面形成呼应的是:利广在这一刻不再是偷鸡摸狗、东躲西藏的逃犯,而是渴望寻找自己位置的人,回不去和想出去都变成了命运的一种束缚,这就是现实,只有在大喊一声“万岁”的疯狂中,只有在不辞而别的决定里,才能真正挣脱束缚,实现人生的可能跨越。尽管楯男上车之后的举动证明这只是一种可能:他望着窗外流动的风景,又望着镜头,当列车向前行驶,进入的却是黑暗的隧道,他的目光是迷惘的,火车必须经历未知的黑暗就是楯男对未来的注解,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鼓起勇气的离开本身就比方向更重要,那一声“万岁”就比无数次坚持却又放弃的决定更有意义。
这就是行动本身赋予的意义,而这也成为了经历了漫长的“节日的准备”之后的爆发。完全可以把“准备”之后付诸行动看做是利广、楯男等个体的一种行动仪式,这个仪式标志着遵从自我而实现的自由,就像在离开之前楯男放飞了笼子里的绣眼鸟,鸟儿挣脱了牢笼就是获得了飞翔的自由,而鸟儿本身就属于自由的天空,楯男的这一举动就是对自我的暗示:鸟儿拥抱自由是一种基于本能的渴求,人离开被束缚的世界也是对自由本能的呼唤。但是追求本能的道路何其漫长,因为那时一段充满了未知的“准备”之路,而对于楯男来说,这种“未知”的准备更表现出“我向何处去”的人生母题。
| 导演: 黑木和雄 |
黑木和雄把楯男为主角的选择归于对本能的渴望,恰恰是要展现这个不允许放置本能的现实。离开是本能,自由是本能,而最大的本能就是性的本能,在信用社每天面对着资金、数字,每天重复着生活和工作,性无疑是压抑的,但是对于楯男生活的现实来说,性本能合理性的恰恰是荒诞的不合理。电影一开始,楯男起床就迟到了,母亲说了他两句,楯男不吃早饭就骑上自行车赶了出去,而爷爷正在屋顶修理,这是家的一种展现,但是除了母亲和爷爷之外,却没有看到父亲,父亲清马在哪里?在别处,在别的女人处,女人市枝和野枝子在工友面前大打出手,她们所要争的就是清马,清马没有回家长期和市枝住在一起,而这两天他离开了市枝和野枝子生活在一起,打架时市枝喊着把男人还给自己,而野枝子显然是胜利者,但是这个清马不是他们的丈夫,更不是他们可以争夺的情人,而是楯男的父亲,阿寿的丈夫,在家庭关系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两个女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争夺别人的丈夫,这非但不是耻辱,也不会被人议论,而是一种常态。
这就是一种用不合理取代合理的现实,这种现实就是荒诞的现实,更为荒诞的是:楯男去找父亲,市枝把清马的两包东西丢了出来,楯男只好去野枝子的住处,父亲清马在那里,清马也没有半点羞愧,还让楯男在哪里喝酒吃饭,父子和和气气,似乎完全没有道德感丧失而带来的不安。而这也不是最为荒诞的,当野枝子突发疾病死去,清马厚颜无耻地回了家,阿寿见此不允许清马踏进家门,“一直以来我就把自己当寡妇了。”而清马嬉皮笑脸地说:“把我当成房客好了。”阿寿没有给他打开家门,而是拎着东西去找市枝,本是仇人的两个女人却分外礼貌,阿寿甚至麻烦市枝照顾清马,当市枝答应下来,阿寿甚至磕头致谢。把自己的丈夫大方送给情人,还万分感谢情人对丈夫衣食起居的照顾,这是怎样一种想法?这又是怎样一种生活?目睹一切的楯男把这一切看成是“丢人”,丢人违背的是道德,是伦理,是规则,但它又是如此合理的存在,这就是楯男所面对的现实的荒诞性。
这或者只是一个性关系的倒错样本,珠美被人从大阪送回来,已经是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在大阪她经历了什么,遭遇了什么,利广一家毫无所知,而现在当珠美回到村里,荒诞的故事又开始上演了:在夜晚的海边,楯男看见了珠美总是一个人在沙滩上,他听人说在珠美出去之前本来是要嫁给楯男的,类似娃娃亲的存在,而现在珠美疯掉了,所谓的婚事也只是一个玩笑。楯男在大海边忽然就脱掉了衣裤,然后悄悄接近珠美,在和珠美亲热的时候,忽然被人暴力赶走,楯男赤身裸体在大海边奔跑。这个赶走他的人不是别人,是每天在海边补织渔网的爷爷,不久之后珠美怀孕了,而担负照顾她任务的也不是别人,而是爷爷,而且爷爷是光明正大和珠美在一起,珠美的母亲也感谢爷爷承担其照顾的重任,一个是年轻的女孩,一个是年迈的老头,两个人像夫妻一样生活,无论对于珠美家人来说,还是对于楯男一家来说,都变得合情合理,利广甚至因为妹妹有了归宿还找楯男喝酒,说两家从此是亲戚。

《节日的准备》电影海报
除了父亲清马和两个妇人相关的浪荡生活,除了爷爷和珠美之间乱了辈分的疯狂行为,还有利广兄弟之间的性替换故事,利广的哥哥贞一偷盗成惯,警察找上门说他又偷了电视机,贞一连忙逃走了,最后当然被抓进去了,而利广钻进了嫂子美代子的被窝,他对美代子说的是:“哥哥进去了,我可以代替他,这样才是亲兄弟。”而美代子似乎并没有反抗,在他的抚摸中也完全顺从了。而楯男有一次还发现做裁缝、脚瘸的菊男和女人在里屋里,他仔细窥视,才发现那个女人不是别人,而是菊男的母亲,在那晚,楯男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母亲搞在一起,就像菊男和母亲一样,还好梦惊醒了,大汗淋漓的楯男回到了现实之中。这实在是一个性混乱的现实,父亲和不是妻子的两个女人有染,爷爷搞大了女人的肚子,弟弟可以代替哥哥和嫂子同房,男人和母亲做不伦之事……它们是倒错,是混乱,是对伦理的违背,是对法律的亵渎,但是在村子里这却是一种正常的事,没有人指责,没有人议论,即使存在矛盾也是内部矛盾。
将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性关系变成了合理、合情甚至合法的生活,这就是荒诞,甚至荒诞是对合理的一种解构,珠美生下孩子之后甚至竟然恢复了,她避开了爷爷,爷爷说这是自己的孩子,那一刻,不仅珠美,珠美的母亲,清马也都不说孩子是爷爷的,“你就当是个短暂的春梦,该知足了。”当然失去了“孩子”的爷爷上吊自尽。生活就是在神志不清中合理地发生,一旦变得正常,它带来的就是死亡的悲剧。对于楯男来说,从爷爷到父亲,所构成的正是一种“家族传统”,“我是爷爷的孙子,爸爸的儿子。”仿佛对于楯男来说,这是自己进入荒诞世界的可能,但显然,黑木和雄在这里构建了对于正常本能的解构,性不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本能,而是一种永远倒错、混乱和荒诞的存在,而这正是他想要离开的原因。父系构成了这样的倒错,而母系呢?楯男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照顾他的生活,但是母亲却成为他追求本能生活的一种束缚,当他提出要去东京的时候,母亲几乎哭喊着求他留下来,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如果他离开了自己如何生活?楯男和母亲的不伦只是一个梦,他没有恋母情结,但是母亲却天生将他保护起来,让他留在身边,她完全把楯男当做了笼子里的那只鸟,当楯男放飞了绣眼鸟,母亲竟然以为是鸟儿自己飞跑了,这就是自由和束缚的不同解读。
但是,在楯男身上发生的性故事,既不是性倒错的荒诞,也不是性混乱的不伦,而是和暗恋着的阿凉上了床,即使阿凉哭泣说自己和老师船山已经睡了,但是楯男并不在乎这一点,毕竟他们的关系才是正常的。但是这也并非是正常本能关系的表现,阿凉一直参加聚会,讨论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讨论左翼青年的理想和行动,她甚至希望楯男写作关于工人阶级的剧本,当看到楯男跟着利广在街上喝醉了酒还去找妓女,就骂他们“无耻”。可以说,阿凉代表的是寻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却又必须以传统道德作为武器,于是他们自然成了高高在上却不切实际的政治青年,理想变成了一种标榜,变成了一种消费。而当最后阿凉回到楯男身边,回到本能之中,却以更为荒诞的形式出现:在楯男值夜班的时候,阿凉找他睡觉,不想半夜发生火灾,上司批评他上班时间和女人睡觉,而第二天楯男身上披着烧焦的棉被,尴尬地走向海边,这成为了另一个荒诞意象,性和本能在合理世界里发生,却变成了完全讽刺的“惹火上身”。
黑木和雄通过性的荒诞性展示,解构了性作为本能的存在意义,所以在无法通过性得到满足,亦无法在剧本创作中虚构现实,对于楯男来说,这一切就是一个“春梦”,唯有在漫长的准备性经历之后选择逃离,即使未来是黑暗的,未来是未知的,未来甚至依然是荒诞的,但那一声“万岁”一定是逃离仪式的真正命名。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