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7《审判》:法的门前站着一个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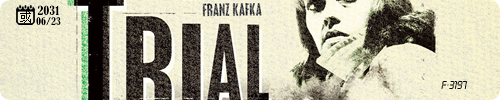
除了你,没有人允许进去,别人不可能进去,这道门只为你打开,而现在,我将要关上它。
曾经门是打开的,曾经可以从打开的门进入,但是现在门被关上了。这是守卫对在法的门前的乡下人说的。门关上,漫画也关上了,旁白也关上了,甚至,卡夫卡小说《审判》也关上了。
这是奥逊·威尔斯1962年的电影《审判》,当这部118分钟的电影成为奥逊·威尔斯的代表作,意味着只属于电影的那扇门在关闭中打开了。威尔斯引用了卡夫卡小说《审判》中K和神父的对话,揭示了“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的寓言,这是解读小说《审判》的一把钥匙。但是现在它属于电影的开篇,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关闭了小说之门。根据卡夫卡的小说改编——编剧栏里还标注着弗兰茨·卡夫卡的名字,但是很明显,电影叙事和文字叙事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想要通过卡夫卡的小说理解威尔斯的电影,或者想通过威尔斯的电影深入卡夫卡的小说,都是一种错觉,当威尔斯完成了电影,《审判》就只属于威尔斯的叙事,那扇门关上或者打开都属于一部1962年的电影、一部118分钟的电影、一部带着强烈威尔斯风格的电影。
这或者是解读电影的一个关键,漫画和旁白甚至只是最初的过渡,当守门人说完这句话,卡夫卡的小说就被完全合上了,那么,站在法的门前就只剩下了一个观众。而实际上,这个“审判”的寓言里,站在法门前的自始至终也只有一个人: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卫,乡下人请求进入法之门,因为他听说法之门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守卫却告诉他:“未经我的许可不要试图进入,我很强大,然而我也是守卫中最弱的一个,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有更强大的守卫。”在守卫的禁令面前,乡下人只好在门口等,但是他一直等到年老,临死之前也都没有能够进入法之门,“所有人都想了解法之门,为什么这些年来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来求见?”于是守卫说了那句最经典的话,这句话就成为了打开法之门甚至法本身的钥匙。
看起来,在法之门之外的只有乡下人,他一直等到死都没有能进入法之门,按照守卫的说法,乡下人被挡在门外才是唯一的意义,因为法之门只为他而存在,无法进入才彰显了法之门的存在,这像一个悖论,所以这是一个“梦的逻辑”;但是,乡下人从乡下而来,如果他知道无法进入,那么他也可以选择离开,所以乡下人反而是自由的,法之门进入或不进入都不能改变他可以离开的自由。但是守门人却不一样了,他必须在法的门口,即使在乡下人等待而老去、死去,守门人还是在门口,即使乡下人拥有自由而离开,他也必须在门口,也就是说,这道门不是为乡下人而设立的,更像是为守门人而设立的,守门人为法而存在,为法的门而存在,“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法”,在只为法而存在的意义上,守门人才是真正的乡下人,而在最后的结局上,乡下人死去,门失去了意义,这也是守门人之死,这个寓言真正的悖论就在于:守门人才是乡下人,只有死去法的体系才有意义,而一旦关上法之门,守门人也就失去了意义。
不是乡下人无法进入真正的法之门,是守门人永远无法真正进入体系之内,这就是整部电影关于荒谬性的设定,之所以荒谬,因为它就是一个梦,而电影一开始,约瑟夫·K刚刚醒来,他就是从梦中醒来,醒来他便成为了那个乡下人,实际上他也是守门人。威尔斯就是在这样的悖论逻辑上建立了叙事,当警察进来告诉他被逮捕了,K就像是在做另一个梦,他的疑问是:我犯了什么罪?谁指控我?继而对警察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你们是警察吗?”从梦中醒来又进入到另一个荒诞之梦,梦和梦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其实就是法之门:分开法的外面和法的里面的那道门在哪里?如果回到那个寓言,乡下人要进入法之门,他想要干什么?法之门里面到底有什么?没有答案,所以实际上在寓言里,这个界限就被取消了,当进入到没有分界线的门口,乡下人、守门人或者K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法之门到底意味着什么?
| 导演: 奥逊·威尔斯 |
因为取消了那道必然的界限,这个寓言就走向了一种虚无:K问自己犯了什么罪,K想要知道谁指控了自己,都变成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也变成了没有原因的事实,那么这种取消意味着另两种东西的取消:进入法之门,有时候是因为你犯了罪,但有时候是你需要申诉、辩护甚至救赎,所以当原因取消,那么就意味着申诉、辩护和救赎的可能性被取消了,也就是你必然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和无罪的可能性变成了有罪的必然性;既然是诉讼是审判,那么在K是被告的情况下,就应该有原告,但是在K被审判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原告,反而他看见了和他一样在法庭办公室外等待的许多被告,被告是一种复数,原告却缺席,审判需要被告和原告在场并处于同一地位的场景就被取消了——在申诉、辩护甚至救赎被取消、原告永远缺席的状态下,“审判”就变成了一种单且不可更改的状态:嫌疑人有罪,他就是罪犯。
在这里就牵涉到这个寓言最核心的部分,法之门毕竟只是一个象征,真正难以进入的是法本身,而法作为一种规则,一种制度,一定有在其至上的存在,那么这个在法律之上的又是谁?当然法的背后就是一个权力系统,威尔斯对“权力”的展示其实变成了一种影像化的直观,K工作地方的有数百台打字机,坐在打字机前面的不停打字的打字员,打字机和打字员整齐划一,他们构成了体系化的一种景观,而这种景观的背后就是无处不在的权力,当权力永远存在于系统的背后,操纵着体系的运转,打字机和人合一,或者人也是打字机,那么这就是权力体系制造的异化。除了打字场景之外,看上去具有高度统一性外观的高楼、可以计算犯罪数据的巨大计算机、被一捆捆卷宗堆积起来的档案室,以及压抑的隧道、光影交错的通道,这些都是异化的景观呈现;在威尔斯制造的影像景观之外,那些看不到希望却在苦苦等待的被告们,身上挂着牌子像死刑犯的病态者、瘸腿而总是拖着沉重箱子的马里卡、躺在床上“患病”的律师哈勒斯、生有鸭子一样的璞说自己有生理缺陷的护士莱尼、在夜总会上班的比尔斯纳、像狗一样跪在哈勒斯面前的布洛克,以及被孩子们的目光监视着的画师蒂托雷利,也都是被异化的人。
这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世界,这个异化的世界就在于权力统治了法,就在于审判变成了有罪的证明,而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并非仅仅是拥有审判权的那些人,初级法官、高级法官、没有权力的法官之外,还有律师,还有守卫,还有画师,他们手上都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叔叔马克斯向K强调的家族荣誉,还有闯入进来的警察,他们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都是权力的代言人,在如此众多的权力面前,每个人都可能被异化,每个人都成了像守卫一样是法的仆人。而在这个取消了法的界限的权力世界里,它更可怕的地方是:被审判的人可能是审判的人。当K出现在那些被告面前的时候,那个声音低沉的老人却认为他是官员,所以向他申诉自己的冤屈,曾经K在审判时呵斥那些对自己审判的人是冠冕堂皇的官员,自己是无辜的被告,但是现在在众多的被告面前,他又被当成了审判被告的官员,这就是一种权力的泛化和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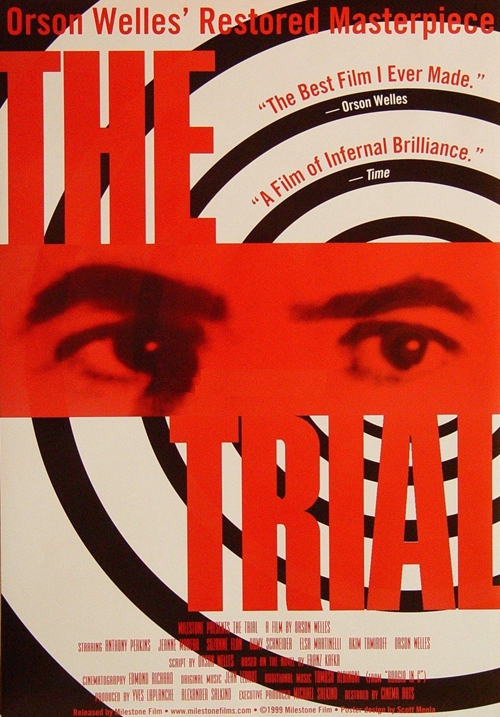
《审判》电影海报
威尔斯提出了法的悖论,展现了权力带来的异化世界,但是这个“审判”的寓言还有更“威尔斯化”的一个主题,那便是比犯罪本身更普遍存在的“负罪感”,而这或许就是这个异化世界本质性的存在。K在醒来后被宣布逮捕,他疑问于自己犯了什么罪,谁提起了诉讼,这是一种巨大的质疑,但是在比尔斯纳回来之后,坐在她的房间里K告诉了她自己被捕了,然后说:“我没有犯罪,但有负罪感。”犯罪需要有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但是负罪感并不需要这些所谓的证据,它是内心的一种感觉,而这种内心的感觉在电影中泛化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而这就是威尔斯鲨鱼的母题,“在这个扭曲、变态的世界上,没有人是无辜的。”当比尔斯纳听到这个消息,安静的她开始大声呵斥K,“不要将我拉下水。”然后让K滚,一个在夜总会上班的女人,她是不是被触发了负罪感?那些警察被关在小房间里,他们怀疑是K告状说他们贪污,他们相互之间指责甚至打斗,而封上口不是为了让K听不见而是让自己不再祸从口出,这是不是一种负罪感?女裁缝的丈夫是守卫,但是她告诉K自己可以帮助他,因为自己认识预审法官,而且一直在写报告的预审法官对自己感兴趣,这是不也是道德上的沉沦?当律师蒂托雷利说:“锁起来有时候比自由更安全。”K骂布洛克不是客户而是律师的一条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不道德甚至罪恶的东西?
甚至当最后K的所有罪都被证实,他被两个人拉向了行刑地采石场,那两个人退缩,拿着匕首又相互退让,最后又引爆了炸弹,是不是也是负罪感在作祟?“这是肮脏的把戏,全世界都疯了。”疯了的不是被审判而处罚的K,而是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噩梦缠绕的世界,一个永远被挡在法之门外的世界,一个处处是异化的世界,更是所有人都在道德沦丧、信仰迷失、法律缺失的负罪世界里挣扎,没有原告,所有人都成了被告,不被救赎,所有人都将被惩罚——这个异化、发疯和罪恶的世界,在K行刑之前,又出现了电影开头的漫画布景,当影子被投射在漫画上,这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柏拉图式的洞穴寓言?所有人都是乡下人,所有人都是守门人,所有人都是无知的囚徒——在这个洞穴里,拯救大家不再是法官、律师,而是普遍真理的哲学家,但是哲学家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法的门前站着一个观众”提出来的,当然摄影机后面、洞穴后面的威尔斯自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根据卡夫卡小说改编,我饰演了律师并导演了电影,我是奥逊·威尔斯。”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