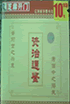 |
编号:H96·2020313·0616 |
| 作者: | |
| 出版: | |
| 版本: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 |
资治通鉴(光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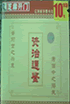 |
编号:H96·2020313·0616 |
| 作者: | |
| 出版: | |
| 版本: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 |
资治通鉴(光盘1)
 |
编号:H99·2011219·0613 |
| 作者: | |
| 出版:北京卓群数码公司 | |
| 版本: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 |
中华传世藏书全(光盘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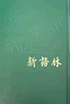 |
编号:H76·2011029·0602 |
| 作者: | |
| 出版:上海书店 | |
| 版本:1982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9.05元 | |
| 页数: |
《新语林》,文艺半月刊,原徐懋庸主编,第五期起改为“新语林社”编辑,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月停刊,共出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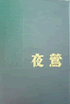 |
编号:H76·2011029·0601 |
| 作者: | |
| 出版:上海书店 | |
| 版本:1983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14.10元 | |
| 页数:317页 |
《夜莺》,方之中编辑,月刊,1936年3月创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四期。
 |
编号:H76·2011029·0600 |
| 作者: | |
| 出版:上海书店 | |
| 版本:1983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66.00元 | |
| 页数: |
中国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的毓机关刊物,1922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创造社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等主办,泰东书局出版发行,以刊发文学创作和译著为主,亦发表文艺评论。1924年2月出版第三卷2期后停刊,共出6期。本书根据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合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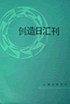 |
编号:H76·2011029·0599 |
| 作者: | |
| 出版:上海书店 | |
| 版本:1983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6.00元 | |
| 页数:508页 |
《创造日》是创造社前期为上海《中华新报》编得文艺副刊,1923年创刊,同年11月2日停刊,共出101期,本书是它的汇刊本,据光华书局1927年版印行。
这是立秋的晚上。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业者。
——郁达夫《立秋之夜》
一个穿着洋服,一个着着长衫,一个从访同乡处归来,一个则要送别赴美国的朋友,不同的打扮,不同的朋友,似乎是两个方向的行走者,似乎在面对不同朋友的境遇,但是他们殊途同归:一样是在立秋的晚上,一样是迎着风沙,一样站在三岔路口,偶遇的他们更具有相同的身份:失业者。
当郁达夫在《立秋之夜》这篇小说中描述了两个殊途同归的失业者,不管是三叉路口,还是狂猛的风,都构筑了现实的困境,他们其中一个没有坐电车回家,一个不从叉路回去,也都展现了他们的迷惘。这是无法走出的现实,这是无从抉择的生活,“二人默默前去”似乎把他们重又拉回到同一的世界里,而所谓的“同乡”和“赴美国的同志”也便成为一种隐喻:在被现实困住的立秋之夜,回到故乡或者远赴他国都不是最终的出路,“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者在那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向内回到故乡和向外走出国门的选择。
郁达夫描写立秋之夜是中国当时的普遍的现实图景,群体如邓均吾在《面包》一诗中所描写的劳工:“黄尘雨汗的劳工们,/你们最大的希望不过面包,/假如面包也有灵魂,/他会为你们同情而悲悼!”劳工和面包之间呈现的希望和失望在个体意义上更是涂抹上了悲情色彩:“现在我又听到这种尖锐的汽笛声,我正等侯我的运命来实现我的失望。我卧在这个如坟墓的床上,我的思潮杂在窗外的雨声里飘着,我满帐中都酝酿着幻想了。”沈松泉在《汽笛声》分明听见了将希望拉回来的“汽笛声”,它是运命,它是幻想,它最后是一张“如墓的床”;而如郁达夫小说中的“同乡”,全平的《故乡之游》里则让回去的故乡变成了死亡的渊薮:“这故乡,正是我理想中故乡:路上铺着正义,路上砌着真理,流着汗,流着血的小孩子,正立在路上猛力攻打那兀立的残败的古旧城墙。”当旧有的记忆和旧墙一起最后轰的一声坍塌,他发出的疑问是:“理想中的故乡,终不过是一个甜美的梦么?”
倪贻德《寒士》中的“我”,也是沉浸在这样一个梦中,只不过和梦见理想中的故乡不同,“我”梦见的是让文艺找到理想的都市生活。和朋友辩论中“我”总是认为都市才是文艺应该存在的地方,他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文艺要表现近代生活,而近代生态或显著表现在大都会里,所以艺术家就应该到大都会里去观察去描写;第二,中国古代文艺偏向于山林田野,这是一种偏离,必须进行补救;第三,都市生辉情调丰富,是简陋乡村无法达到的,所以,“南京路是常欢喜去跑的了,市内电车上是常有我的踪迹的了,夜深更静的时候,是常要踏进小酒店小面馆里去吃喝的了……”这是一种理论式的构想,而当“我”用实际行动开始进入都市的时候,起先是看不起乘坐开往南京火车上的旅客的,因为他们带着土特产,穿着贫民的衣服,而当自己真正来到南京这个理想中的大都市,才发现一切都只是梦想,现实击碎了这个文艺梦:“什么是王气金陵?什么是龙蟠虎踞?都不过是些骗人的话!在我的眼光里看来,不过只有些清冷的长街,低陋的平房,和灰色的空气的集合体罢了。”
这是一种失落,因为失落才要反过来审视理想,倪颐德的另一部短篇《江边》更是思考着青年的出路问题,亚白咒骂的是社会,“这都是受了经济的压迫,可恨的金钱哟!万恶的金钱哟!我们这许多有为的青年,都被他压制得不得动了!”而充满了失望的N更是嘲讽着自己,“我在学生时代,常冷眼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怜虫,哎!如今我自己也变了一个可怜虫了!”他终于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希望,那就是去镇江CW公学求职,坐上轮渡,带着希望而去,但是在公学里却遭遇了不公,希望破灭了,N像是被人又推向了万丈深坑,于是冰冷麻痹的他对自己说:“此地那里是我的安身处,还是回到家乡去渡孤独的生活罢。啊!我还是归去……”从失望到希望,从奔波到麻痹,N代表着一代人的困顿,当他带着醉意来到大江边,向着世界发出了呐喊:“啊啊!我若能从此地,乘风而西,过九江,泊乎洞庭,去访访屈贾行唁之地,听听潇湘夜雨之声………啊!我的屈原!我的贾生!我崇拜你们的孤高!我崇拜你们的节操!我…我……”
郁郁不得志,是现代版屈原的再现,是另一篇《离骚》的问世,敬隐渔在《破晓》中呼唤着:“我的爱,你快把门儿打开!”楼建南在《龙山顶上放歌》中代表着一代人不愿昏睡的呐喊:“我纵在这么的嘶声高歌,/黑越越的人寰还在贪着睡眠!”要告别脏脏的世界,要离开梦境,就要站在最高处,迎接照满人间的鲜红朝阳,“醒来吧!快醒来吧!”但是如何醒来?面对现实的困境,倪贻德是在怒骂,在自省,敬隐渔在呼唤,在期盼,楼建南在攀爬,在呐喊,但是也有另一种态度,张友鸾《随感录·服从》则表达了另一种“服从”的心态,在他看来,服从不是耻辱,反抗引起的争斗才是耻辱,“有能吃人的人,我们便让他吃,总比兽吃我们好些罢?兽想吃我们如果是热忱哩,我们也可让他吃,总比让‘面上不吃我,肚子里想吃我’的动物吃去好些罢?”由此他认为,服从的你我构成了永远和平的世界,而不服从的你我则制造了斗争的世界——服从选择的不是动物,不是野兽,而是人,期望用服从的原则得到和平,其实是一种卑劣的人生观,是一种奴役心态——诵邺《猎狗庸奴》给出了这种人生观的下场,当老狗最终失势,他得到的是讥讽和冷笑,是良心的呵责:“都是我底罪恶呵!一切都是我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呵!我现在觉悟了!我现在忏悔了!赦了我罢,如果你们肯宽恕我;裂了我底肢体罢,食了我底肉罢,如果你们要寻我报仇,都可以!一切我都很愿意!因为我已经觉悟了!因为我已经忏悔了!”最后等待的是被审判。
不管是面对现实而理想破灭,还是咒骂社会的不公,不管是山顶上放歌而排遣苦闷,还是以服从的媚态来换取和平,其实都是那个时代面对迷惘现实的一种态度,都是遭遇困境时想要寻找出路,而这种出路观似乎又回到了郁达夫的两个方向论:穿长衫还是穿洋服?回故乡还是去美国?东方和西方是一条岔路口,有人选择向外,王珏在《日落江上行》中问道:“西方有乐土,/友们哟!是否由这儿寻去?”敬隐渔在《罗曼罗朗》中发现了西方另一个文学世界,“如今看若望克利司多夫小孩子时代的生活倒比我自已经过的事情看得明白多了,更觉得有意思,方才知道了一点人与生命底观念。”而郁达夫则盛赞已经接受西方思想的日本在翻译上取得的成就,由此看到了中日之间文化的差异,“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西方世界已经打开了国门,但是对于西方文明还存在着矛盾心态,或者是在观望,或者是盲目接受,全平的《他的忏悔》则以“忏悔”为关键词写出了一代人的迷失。青年受到了现代思想的教育,对于父母安排好的传统婚姻存有质疑,在没有采取抗争的行动中,他希望能感化他们,“这已是定局的了。我不能违拗尊长;取社会的责怪。并且不美观可以修饰补救的,放足,读书,便渐渐的会使旧式变成新式了。”新式在他看来就是让旧式女子放足、读书,“否则不娶。”但是回家之后,这种理想主义似乎覆灭了,他还是结婚了,看着妻子的小脚,他心生诅咒:“旧式而顽固的讨嫌女人!”他以西方的平等观对照妻子,“这原不能怪她,因为旧式的女子,被家庭礼教所束缚,仅能晓得服侍她丈夫是应当的,而不晓得有所谓爱情,比服侍还要紧,她仅晓得待我好;我生病的时候,她也很关切的照料我,当心我,甚至坐在床边啜泣,但总没有爱情的举动现出来:我烦闷发怒的时候,她也会用很和慰的言语来劝解我,但总不会用甜蜜的爱情来安慰我。我所以很失望!我或者能原谅她,然绝不会爱她,虽然她是我的妻!”终于在六年之后他和妻子离婚了。“离婚”作为一个新式词语和生活方式,让他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他爱上了一个新妇女领袖,而且也成为了他的良伴,在四个月的甜蜜生活之后,他忽然发现,“他像一枚荔枝,清香的果肉,被满长棘刺的壳在外面包着。又像一粒桃核,外面的甜肉吃完了,中心藏着一粒很苦的仁。”于是他又和夫人离婚了,这次离婚是新式妻子表达了不满:“他的名誉和地位,不足以增高我社交上的声望,并且他不贡献真诚的爱情,使我的身心愉快。并且……”
他成为了独居的人,他在忏悔中感觉到了自己的谬误,“懊恨怨悔的回忆,把他的良心,从偏执的胸中现出来了。无形的责罪,使他在昏暗而阴沉的空气中,起了全身的战栗。”起先是小脚的旧式女人,后来是新妇女的领袖,但一样是离婚的命运,就像郁达夫的《立秋之夜》,不同的穿着,不同的方向,“殊途同归”的两个人都有着失业者这一相同的身份,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式和旧式,都是在同一个叉口找不到归途的人,而小说中的青年从迷惘而追求,从追求而忏悔,更是对于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一代人的讽刺,“思想是谬误的,正和美丽的她待他的差误一样。”但是这谬误和讽刺中,是需要回到旧式生活中去吗?抱着“服从”态度的张友鸾在《随感录》中再一次提出了“骸骨的迷恋”这一种被鲁迅批评的守旧思想,在他看来,西方夹面包的工具“偏是筷子一双”,“但我却不相信,西洋终会化我,而我终会永远改化而同于西洋!”所以否定要吃面包肯定只吃饭的张友鸾发出了自己的宣言:“今朝开始,我读古书!”
这是一种绝对的态度,“骸骨的迷恋”是回到故纸堆,是坚持保守派,针对这样一种对西方全盘否定的观点,洪为法在《我谈“国风”》中提出了批评,“……我们如今读国风,我以为与其费时费日去读那汗牛充栋的诠释国风的著作,不如先以自家的心灵吟味他……因为这时读者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已经感印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韩,我怕只有损失杜韩的真价值,国风(诗经全部其实都是的)之难研究,正因注家太多,我们研究时没有先跳出万千注家以外。……”《读卷耳集》更是表达了对“整理国故”的批判,“研究诗经!研究诗经!这种呼声,我得听得也好多时了。其成绩表现的在那里呢?唉!还不是旧解之迷恋—一骸骨之迷恋!谈到能摆脱一切,另觅‘诗’的真生命,在历来诗经研究上辟一个新纪元,那不得不推沫若的卷耳集。”他把郭沫若的《卷耳集》看成是“整理国故”正确主张的范本:
国风之价值之可贵,就在于它是一班活活泼泼自自由由的男女性在欢愉或悲戚的时候吐出的心声,所成就的作品,是真挚的,是自然的,是不加雕琢,我们读到它,谁不懂憬于那时作者优美可恋的世界?所惜历来解诗者多斤斤于字句,翼翼于惩劝,把一部诗经几乎变成一部“说文解字”或是一部“太上感应篇”,沫若这个小小的跃试,便是还它本来面目一个抽刀斩乱丝的办法。
正如郭沫若在《卷耳集》自跋中所说:“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说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不迷恋于古文古字,不执著于注解,而在于对其中真生命的挖掘,才是“整理国故”该有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洪为法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去从来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在翟秀峰看来则体现在成仿吾的作品中,由此他认为,“他的爱慕之情比人强,他的憎恶之心比人大,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良心,他便是良心的战士,他是对于时代的虚伪与罪孽用猛烈的炮火者。他是真善的战士,彷彿是美的传道者。”
要革“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要做“真善的战士”和“美的传道者”,郭沫若和成仿吾成为领军者,而作为《创造社》主将的他们,自然也在实践着创造的意义,而这也是“创造日刊”一直以来体现的时代意义。革命就是为了创造,战士就是在创造,郭沫若在《怆恼的葡萄》中发出了呼喊:“矛盾万端的自然,/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人间世的难疗的怆恼,/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宗在《啊我要创造个新的》中开始了自我的革新:“啊我的身躯!/啊我的身躯!/你这不可改造的物体!/我今誓将你弃去。/我要创造个新的,/如此青春之树所象征。/啊,我要创造个新的!”郑伯奇在《A与B“对话”》中探讨了创造的意义:“我只想永久活动。我只听生命活泼泼地发挥。为忠于生命,我要破除一切羁绊,打破一切藩篱。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同时我要永生!”刹那刹那地生着便是循环不灭的永生。郁达夫在《苏州烟雨记》中从目睹行旅中那些“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的迷失而发出了创造的宣言:“你们若欲上空旷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气,一则可以醒醒你们醉生梦死的头脑,二则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谢的青枝绿叶,豫藏一个来春再见之机,那么请你们跟了我来,Und ice。Ch Sohnucre Den Sack and wandere,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吃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
生命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自由,这便是创造的宗旨——1923年7月21日,由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的《创造日》创刊,这个为上海《中华新报》编的文艺副刊处处体现了创造精神,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说:“现在我们的创造工程开始了。我们打算接受些与天帝一样的新创造者,来继续我们的工作。”这创造的工作需要的是“纯粹的学理”,是“严正的言论”,是“唯真唯美”的精神,从政治经济到文学文艺,无不需要创造——“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属言的。”创造远离时局,远离政治,是因为创造只属于纯粹的批评和唯美的文学,“我们这一株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
但是正如站在三叉路口的中国一样,穿长衫和穿洋服,回归故乡和外出接受新学,都是殊途同归的,创造要远离时局远离政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乌托邦,所以和中国现实的矛盾一样,出刊101期、存在100天的“创造日”终于走向了它的“终刊”——11月2日正式停刊,郭沫若在停刊前两日的《创造日停刊布告》中认为,“创造日”是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但我们深恨没有力量可以使荒漠成为良田,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使他独立以至于永远;我们只好忍心,我们只好听他在荒漠中萎谢。”与郭沫若将停刊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力量局限不同,成仿吾在终刊当日发表的《终刊感言》中分析了终刊的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力量太弱了”,而是“不辨黑白的群众对我们的诬枉倒使我们每期作呕三日了”,一边是自身的不足,一边则是读者的原因——读者为什么会不辨黑白,又为什么会诬枉他们?成仿吾没有细细分析,但是从创造日的停刊来看,它似乎也没有走出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迷局,就像当时的民众,就像当时的文艺,就像当时的政治,但是“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的永生观让“创造”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一种不竭的动力:
我们的“创造日”虽只道一百余日的生涯,但我们相信在我们小部分的关系者心中,在我们小部分的爱读者心中,他如像种子中含的胎芽一样,他是依然活存,而且必有一日迸出地层,奋发参天的时侯。朋友哟!我们请暂抑着悲哀,同声唱他的薤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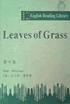 |
编号:H73·2010814·0588 |
| 作者:(美)Walt Whiteman | |
| 出版:海南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501页 |
In 1855 Whitman published at his own expense a volume of 12 poems, Leaves of Grass, which he had begun working on probably as early as 1847. It was criticized because of Whitman’s exaltation of the body and sexual love and also because of its innovation in verse form—that is, the use of free verse in long rhythmical lines with a natural, “organic” stru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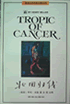 |
编号:H73·2010814·0587 |
| 作者:(美)Herry Miller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10.60元 | |
| 页数:276页 |
No punches are pulled in Henry Miller’s most famous work. Still pretty rough going for even our jaded sensibilities, but Tropic of Cancer is an unforgettable novel of self-confession. Maybe the most honest book ever written, this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about Miller’s life as an expatriate American in Paris was deemed obscene and banned from publication in this country for years. When you read this, you see immediately how much modern writers owe Miller.
 |
编号:H73·2010620·0585 |
| 作者:辜鸿铭 | |
| 出版: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 |
| 版本:1998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6.00元 | |
| 页数:143页 |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天才辜鸿铭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中国人的精神》原载1914年的《中国评论》,1915年更名《春秋万丈》在京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本书力阐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当时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境况下,其影响尤为特殊。
 |
编号:H73·2010620·0583 |
| 作者:Edited by Dolley | |
| 出版:外文出版社 | |
| 版本:1989年第一版 | |
| 定价:4.00元 | |
| 页数:318页 |
本书选录的短篇小说为英国20世纪的作家作品,在英国广受影响,最初出版于1972年,前后重印15次。书中共选录15篇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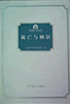 |
编号:H31·2010620·0582 |
| 作者:刘小枫 等 | |
| 出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 |
| 版本:1995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316页 |
“同时具有灵魂和肉体的个人世界上可能的命运——流亡与栖居。”这是这本书的主旨,文集收录的文章既有国内的,也有西方的,既有文学的,也有艺术宗教的,但这些驳杂的文章往往掩盖了主题的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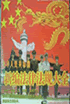 |
编号:H99·2010531·0578 |
| 作者: | |
| 出版: | |
| 版本: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 |
中国法律法规大全(光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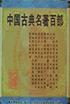 |
编号:H99·2010513·0577 |
| 作者: | |
| 出版: | |
| 版本: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 |
外国文学·中国古典名著一百(光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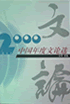 |
编号:H12·2010428·0576 |
| 作者:杨克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7.00元 | |
| 页数:400页 |
共选录2000年37篇文论。
九十年代的历史和社会就这样作为一个他者之物疏离个人而存在,在它行将结束的时候,人们才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们而去。比起其他的历史时期,这真是一个平静自在的年代。
——陈晓明《自在的九十年代: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
21世纪一〇年代也已经远去,新冠疫情开启的二〇年代依然在某种不安和惶惑中。当20世纪的百年都成为历史的档案,翻开一本终止于2000年新世纪最后一年的文论选,“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疏离感似乎就真的成了隔阂,在这样一种隔阂状态下,当读到陈晓明所说的“九十年代”的他者之存在的时候,平静自在甚至变成了虚空之后的真正空虚:在走过了新世纪2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的文学又在怎样的轨道上,文学批评又在何种道路上?
已经阅读了“秉承真正永恒的民间立场”的《2000中国新诗年鉴》和《2001中国新诗年鉴》,也阅读了更官方更自负也更宏大的《2000中国年度最佳诗歌》,还阅读了“可能与不可能混合”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再加上即将阅读的《90年代中国实力诗人诗选》和五卷本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这些文本让我返回到新世纪还未到来的时间状态中,一种复古的阅读心情是在回味那个世界末图景?还是不想进入已经走过了两个年代的21世纪?转身而进入的逆流方式是不是也如陈晓明所说是一种“他者”的选择?
九十年代成为一个历史区间,陈晓明也是用回望的方式完成了解读,他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就将它命名为“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历史时期,而且他定义这是一个“平静自在的年代”,这种平静自然一方面是基于历史本身,他认为九十年代就是一个“他者之物疏离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也在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叙事分崩离析的时候,处于“一种严重的历史停顿中”,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造就了后者的停顿,后者映照了前者的疏离,所以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无法成为开创性的一代,他们只是“坐享其成的一代”,他们的写作是轻松自如的,也是缺乏挑战性和刺激性,看起来文学写作获得了相对较大的空间,但是在文化的市场化去世中,写作不得不靠近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但是,陈晓明并没有全盘否定九十年代的创作,他认为必须用建设性的目光看待20世纪最后十年的文学,“我也乐于把那些拆解视为一种可能性,把那些混乱视为充满生机的变异。”
这种可能性以指向一种变异,他总结认为九十年代相对于八十年代,也具有开创的经验与提示的可能性,它包括非历史化的表象叙事、非社会化的个人化叙事、非叛逆的表意策略、非前卫化的时尚体验和非文学化的批评倾向,这五种可能性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以统一的“非……”结构被呈现出来,陈晓明有意进行的命名就表明,“这些动力并不是主动性的历史建构,而是一种无目的性的反本质主义的分裂运动”,也就是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指向“不明确并且把自我界定为主体‘他者’”的选择。当自我成为“他者”选择,这种无目的性的反本质主义分裂运动并不是最积极的建构方式,或者说,它依然回归到这个“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疏离了个人存在的他者时代。
他者时代的他者选择,所以从九十年代进入到新世纪,陈晓明并不乐观地称其为“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与陈晓明一样对新世纪中国文学走向存在担忧的还有雷达,他在《小说进入新世纪》中说:“21世纪的小说家,即使不是最后的小说家,也属于最传统的一族守望者了。”这也是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所下的结论,当他们成为“最传统的一族守望者”,无疑也在平静自在中“坐享其成”。但是在杨杨看来,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动,它表现在关系学上,“一种是以作家—作品为主而展开的文学关系;另一种是以作家—读者关系为主所展开的文学关系。”而吴思敬在《90年代诗歌主潮》中对诗歌创作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一时期更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平民化倾向,这种倾向似乎也是文学创作在历史转变时期的一种主动呼应。
陈晓明和雷达认为九十年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处在历史的停顿中,杨杨和吴思敬则认为他们在主动呼应中正准备进入新世纪,那么,“进入”是一种自我主动的建构还是“他者”的选择?这个问题似乎在“女性写作”这种局部的样本观察中得到了较为一致的回答,在一场名为“女性文学与‘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讨论中,谢冕、岛由子、肖鹰、赵栩、林凤、杨克、李学武参与了讨论,讨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谢冕就认为,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思潮进入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女性的性征受到文学写作的重视,这不仅是女性外表的特征,而且深人到她们的心理、生理,包括那些最隐秘的男性很难涉及的领域,于是有了女性文学空前的发展繁荣,他甚至认为女性文学的繁荣是“70年代以来除了朦胧诗之外的文学的大收获”,而到了90年代,女性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无疑是继承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成果,但又提供了新的经验以及新的倾向”。肖鹰则认为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必然是女性化和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学意义的绝对化和实在化为女性写作设置了一块封闭领地:女性作家在现实存在的巨大的虚无境遇中,拥有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她的躯体。”躯体是惟一确切的真实,因此栖居于这个惟一确切的真实,女性写作必然走向一种私密性,走向而进入,杨克也乐观认为,进入新世纪之后,“新的美学原则最终在新一代都市生存的背景中确立。”
这场讨论所针对的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可能走向,王岳川在文论《女性话语与身份写作在中国》中,比较具体地回顾了女性话语在中国身份书写的历史,尤其是在当代文学语境下,女性书写意味着某种权力颠覆,“写出自己受压迫损害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历史及其历史记忆,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作家写作的行动指南。”而且在诗歌中,他惊诧于一个现实现象:在90年代前后男性诗人纷纷自杀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女诗人走向自杀?这虽然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但是他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女性对于生命本体的珍惜,“她们的生命写作是如此地感性,生命力量如此地充沛,使她们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去发掘对生命、生活、母性和人类的一系列看法。”即使女性写作在某一方面表现的是肉体叙事,但是他认为更多的女性作家从自我的身体描写、自我的隐私兜售,又回到了“自我精神定位自我意义命名的灵肉苏生之路”,所以女性写作在世纪末的意义是:“张扬真正的女性生命意识,张扬人格化个性化的生活情思,我以为是不可谓不重要的。”
郭宝亮从女性话语和身体书写中更是看到了个人化写作的存在意义,一方面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以“私人化写作”“私小说”的方式出现,这是针对文学创作“宏大叙事”而提出来的,而宏大叙事是与一元化文化霸权相联系的,所以个人化写作是为了终结现代理性、启蒙话语、总体化思想和历史哲学;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在形成新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着市场话语的叙事规则,体现了隐私和躯体成为新的开放市场的趋向,而且“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叙事也要和时代、社会直接发生关联”等反思声音的出现,正是个人写作的福音,因为它们远离了感官刺激的追求,远离了窥私癖的时代症候。颜敏更是在《橄榄枝下“幸运”的一代》中把“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看做是“在路上”的一代,说他们的创作“尚没有完全展示出断代的意义”,也不一定是革命性的一代,但是他们以个性化的多样写作构成了“新生代”甚至“晚生代”这一群体。
七十年代以后作家是在路上的一代,九十年代的个性化写作形成了新的公共性,九十年代的女性书写是中国文学新的收获,这些满怀期待的评价正是将九十年代的写作者变成了“进入”新世纪的主动书写者,甚至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进入”的状态不是隔阂,进入的选择不是他者。实际上,不管是把九十年代看成是一个平静自在的年代,还是重新建构新的文本的书写时代,九十年代不是一个断层,20世纪是他们必然关照的一个大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是他们认识的大背景——这百年中国,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曲折过程?到底有着怎样的得失?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误读?到底对“进入”新世纪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五四新文学是百年中国绕不过的一种历史存在,余虹在《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中写道,“对五四新文学论者而言,有两种牵引似乎难以抗拒,即思想启蒙的道义担当和追求真理的学术关怀。”她认为,出于思想启蒙的目的,文学成为启蒙的工具就不可避免,出于追求真理的关怀,文学自身存在的价值又不容忽视,她认为,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序言中言及的新文学运动理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命。”他认为,自己是“活的文学”的理论阐释者,就是用“活的文字”这一革命推动文学革命,而周作人则是“人的文学”的理论阐释者——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就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文字改革更多是一种工具论的体现,而人的文学所构建的则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话语逻辑和价值立场,但是,“人的文学”所凸显的“自主论”一直在曲折中发展,20年代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大多数成员转向“工具论”便是一个明证,所以余虹认为,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性追求在政治和艺术存在的冲突中,变成了一种悖论式存在。
这种悖论式存在其实就是政治和艺术之间的矛盾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矛盾,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似乎成了一种历史遗留。陈思和在《重新审视5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几种倾向》中认为,1949年随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以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但是之后随着对胡适集团和胡风集团的批判和镇压,“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再无法产生出积极意义,“它凡能被毛泽东吸收到自己文艺思想体系去的部分因素,也只能通过毛泽东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而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关于干预生活和提倡真实、人性论的文艺现场,“‘五四’传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活。”这种复活表现在作家的来源多样化,他们的创作也出现了多元化:有胜利者唱出了高昂的政治抒情诗,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颂歌;潜在写作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实际上,工具论和自主论的悖论,政治和艺术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而1958年开始的“文艺大跃进”也成为这一悖论的生动样本。一方面,文艺大跃进成功解决了1957年中国文坛留下的一系列问题,也化解了1949年之后的难题,李新宇在《1958:“文艺大跃进”的战略》中认为,“文艺大跃进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中,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一道彻底扫荡了残存的知识分子话语,并决定了此后20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当政治权威话语通过民间话语对知识分子的文艺园地进行占有和改造,无疑使得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彻底消失,“大跃进民歌运动是权威话语支配下的民间文化的一次盛典,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葬礼。”另一方面,“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当毛泽东以这样的方式指出了诗歌未来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自主论也彻底被解构,尤其是所谓的文学现实主义被扼杀,在“浪漫主义”的大旗下,“粉饰生活、歌舞升平和以说谎吹牛为主要特征的“假大空”在理论上得以合法化。”
这一合法化的“浪漫主义”其实让文学进入到某种黑暗中,高旭东在《对“文革”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审视了这一段历史时期,在他看来,对文革文学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文革并非是大破坏留下的文化沙漠,也并非可以简单归为“封建主义”,“它追求的目标也不仅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另一方面在修正对文革的误读之后,也需要开拓空间正视文革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客观性,他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以儒道为代表的正宗的精英文化传统,继承并弘扬了从五斗米道、太平道到太平天国的民间文化;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置重,转而向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认同,无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文化影响。但是高旭东显然没有对文革的建构意义作充分的阐述,而张清华则以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为切入点,分析了这一历史时期“黑夜深处的火光”,他们是以黄翔、哑默为代表的“贵州诗人群”,是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的“现代派诗人”,是多多、芒克、根子、林莽、方含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是自主论的一种实践,也在启蒙意义上“写下了富有启示性、生命力与先锋意义的一页”,张清华说:“这个年代的真正属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精神反抗,那些在地下燃烧和滚动过的火焰与沉雷般的声音正是我们应认真继承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它们仍然隆隆地响在历史的暗夜里,燃烧在已消逝的时空与记忆中——当我们真正认真地去谛听、去寻觅。”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五十年代提出“双百方针”,从文艺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中国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写着自己的文本,或者它们在“工具论”中失去了自主的声音,或者在启蒙思想中遭到政治的压制,而沉默和压制结束之后的80年代,普遍被看做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春天,吴元迈在《20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走辩证整合研究之路》中回顾了百年来的中国文论所走过的道路,他认为中国文论是在对世界文论的不断吸收和引进中发展的,而在世界背景中,从上半期与“非人格化”的准科学主义文论对垒的人文主义兴起,到后期从语言到历史,从形式到内容的回归,对于中国文论而言,这一转折就出现在80年代,“80年代是20世纪文论进程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也是它的反思时期。”而许明在《回应当下性——关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也把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的转向时期定在80年代,所以他希望中国的学者在“回应当下性”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做出回答——当下性立足于80年代之后的90年代,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国情,却是80年代的延续和递进,一个不变的核心便是人,“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外延可以也应该包含广阔得多的内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内容,自然也应当包括在它的理论视野之中。”鲁枢元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更是重申了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并且将“人学”上升到更大的生态文艺学视野里,“在钱先生那里,人道与天道、艺术与自然为何能够如此自然地相互渗透在一起,在我看来,依然是得之于他那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并且颇具自然色彩的人性论。”
对于90年代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当下性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它无可避免和全球化有关,所以面对中国文学的当下性,就必须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为,程光炜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文学世界的重建,都市化语境中的“个人体验”和当前中国文学的叙事化倾向是调整和重建的方向,“这就使经过意识形态文化急剧调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言说方式,以面对这一世纪的全球化挑战。”是要在全球化中坚持本土化,还是让本土化具有全球化视野?对此,戴锦华在比程光炜更早的《山花》中“质疑全球化”,她认为全球化和本体化本身就是一种二项对立化的判断,而且全球化本身就造就了一幅整齐划一、因之单调乏味的世界图画,“生活其间的人们,一如执掌电视遥控器的手,似乎权能无限,却无法选择众多频道外的内容。”所以中国文学和文化要在质疑全球化中避免全球化,“借用一个极不严谨却颇为中肯的说法:最好的文学语言便是难于、或者说是不可能翻译的语言;于是,中国作家文学的自觉并置于全球化图景之侧,成为一份难于消解的深刻困境或者是难言隐痛。”贺绍俊和戴锦华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是一个缺乏内动力的“伪问题”,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需要的是对具体、个案的研究,需要的是独立的学术立场,需要的是对话精神和比较思维。
无论是对话还是比较,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审视中国文化的百年历程,立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当下,似乎又需要回到文学的本质性意义上,那就是“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这是一种自我的主体存在,是主动性的历史建构——九十年代已经远去,21世纪的一〇年代已经远去,只有那个不是成为“他者”的自我才会发出声音,才会书写文本,才会走在路上,才会一次次以自主的方式“进入”每一个新的年代。
 |
编号:H99·2010418·0573 |
| 作者: | |
| 出版: | |
| 版本: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 |
家庭藏书·全唐诗(光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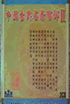 |
编号:H99·2010409·0571 |
| 作者: | |
| 出版: | |
| 版本: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 |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百部(光盘1)
 |
编号:H96·2010331·0570 |
| 作者: | |
| 出版:山东出版总社 | |
| 版本: | |
| 定价:40.00元 | |
| 页数: |
二十五史(光盘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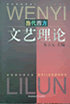 |
编号:H49·2010325·0569 |
| 作者:朱立元 | |
|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21.00元 | |
| 页数:438页 |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对西方文学艺术创作发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17种文艺思潮作了介绍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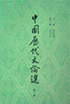 |
编号:H32·2010325·0564 |
| 作者:郭绍虞 王主生 主编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1979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44.80元 | |
| 页数:2018页 |
本书是高校文科教材,选录先秦至近代著名文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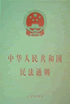 |
编号:H52·2010309·0562 |
| 作者: | |
| 出版:法律出版社 | |
| 版本:1996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3.00元 | |
| 页数:36页 |
我国《民法通则》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它的制定和颁布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国立法体系的确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