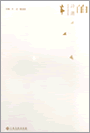|
编号:B83·2190319·1543 |
|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版本:2019年02月第1版 |
| 定价:72.00元当当43.90元 |
| ISBN:9787305209062 |
| 页数:445页 |
1957年,乔治·巴塔耶出版《色情》一书,相比其1950—1951年撰写,但并未完成的草稿《色情史》,这本《色情》展开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色情研究,系统地建立起了他关于色情的理论。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围绕禁忌与僭越,从内在体验、死亡禁忌、生殖禁忌、僭越、杀戮与战争、献祭等多方面分析了色情作为人类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些不同方面中的一致性;第二部分结合金赛、萨德、列维-斯特劳斯及巴塔耶本人的研究成果或文学作品,对色情主题进行了个案研究。巴塔耶循序渐进地分析多种形式的色情,从色情与死亡、神行、劳动与自我意识等的关系,以及人类如何僭越人为禁忌,不断探索生命的各种可能,追求好的经验,让色情这一庞大的主题从深陷的黑暗中脱身而出,从而揭开色情的秘密。
《色情》:越美,污秽就越深
一具尸体不是无(rien),但是这个东西,这具尸体从一开始就被标上了无的符号。
——第四章 生殖与死亡的相似性
一具尸体出现在那里,它是生命的终结,它是死亡的象征,它甚至变成了一种物:然后发臭,然后腐烂,然后归于寂灭。但是为什么乔治·巴塔耶要否定尸体具有的“无”?为什么要去除这个从一开始就被标注的符号?
无是什么也没有,当人死去变成尸体,在客观意义上的确不具有生命意义,它以物的状态存在,没有表情,没有思想,没有内心体验,是“无”的一个东西。但是尸体之存在,或者被成为尸体的时候,尸体其实是一种对象,而在尸体前面的则是那些活着的人,所以尸体对于生命来说,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当人们看见尸体的时候,想到尸体的发臭和腐烂,乃至最后的消失,一定会有某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便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尸体不能回应我们的任何期待,只能回应一种恐惧,因此这个东西还不如无,比无更有害。”
这是对于“无”这个符号的解构,尸体的腐败甚至变成了“我们所来自的世界和我们所要回到的世界的缩影”,它对应了生命的两种端点,在尸体中我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感,而尸体重回自然在循环之后又变成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它以出生的方式重新回归生命世界,这便是出生的羞耻感,“死亡超越这一毁灭,将宣告我重回生命的腐败。”也正是这种恐惧感和羞耻感使得死亡本身具有了一种禁忌,“不可杀人。”这一条《圣经》中的戒律便成为我们从根本上必须遵守的禁忌,而因为禁忌的存在,尸体所触发的便是一种焦虑,当人们看到尸体,其实已经在焦虑中感受到了一种死亡,这种焦虑并不是在恐惧中走向终结,还有一种称为“着迷”的情感,“每个着迷于尸体的人来说,尸体就是他自身命运的图景。”他从尸体身上看到了命运中的暴力,而且不再是杀死一个人,而是毁灭所有人的暴力。
所以,尸体之存在意义,在“他者”的层面上具有了死亡的双重含义,“一方面,与生命的渴求相关的恐惧感使我们远离死亡;另一方面,一种庄严又恐怖的因素使我们着迷,引发一种至上的混乱。”一方面是一种禁忌,制止了接触尸体的欲望,但是禁忌之后的焦虑甚至超越了禁忌本身,因为仅仅所注解的恐惧是即时的,是不可避免的,是无法抵抗的,在内心体验来说,则变成了对于死亡的一种暴力,“入侵死亡的暴力引出的邪念只有一层意义,就是将暴力嵌人我们内心,反对生者,就是让我们产生杀人的欲望。”也就是说,生命一方面给死亡定罪,排斥死亡,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一种禁忌,而另一方面,却有一种“反对禁忌”的行为,它变成了推翻障碍寻找内心吸引人的东西,“恐惧让我们远离被禁行动的同时,赋予这一行动以荣耀的光环。”
巴塔耶考察了与死亡相关的禁忌和生殖相关的禁忌,在他看来,禁忌总是对于暴力的否定,是一种理性行为,《圣经》中记载的两条戒律就是“不可杀人”和“肉体的使命只有结婚后才能完成……”这是人对于死亡、对于生殖的态度的结果,而它们的相似性也一目了然,除了一种暴力性之外,一种恶心感之外,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本性的一种献祭:“性活动和死亡只不过是一场自然行为的祭典的高潮时刻,自然有着各式各样无法穷尽的存在,性活动和死亡都具有无限度浪费的意义,与活下去的欲望相反,自然进行无限度的浪费,这是每一个存在的特性。”
恐惧带来的禁忌和禁忌之后的焦虑,总是连接在那里,巴塔耶引用萨德的话说:“没有什么能遏制纵欲……拓展和丰富其欲望的真正方法是给其加上边界。”无法遏制纵欲,即使在禁忌和赋予这一行动“荣耀的光环”之间加上边界,那种内心的暴力也无法变成像尸体一样,成为“无”的符号,“没有什么能遏制纵欲……或者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减少暴力。”而巴塔耶甚至更进一步,在他看来,人虽然用禁忌的方式让自身活动进入到理性世界,但是内心的暴力本质却不会改变,“自然本身就是暴力的,哪怕我们变得理性,也会有一种新的暴力再次控制我们,并非自然的暴力,而是一个理性存在个体的暴力,理性存在个体企图服从,但是抵抗不住内心不受理性控制的冲动。”
禁忌和僭越,理性和暴力,尸体表象中的无和死亡恐惧带来的有,似乎都在这一种对立中建立了联系,而这种焦虑和着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人获得了非一般的内心体验,而这种内心体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表现,除了死亡,便是和死亡具有一致性的色情。巴塔耶认为,色情在表面上是不停地在外部寻找欲望对象,但实际上,与欲望对象呼应的就是欲望的内在,它和动物的性活动的真正区别就在于,动物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为了繁衍后代,它不需要也不可能进入到内在生命中,只有色情是属于人类特有的,是人的意识中思考内在存在的部分。
从外到内,其实巴塔耶勾画出了色情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色情在寻找外部欲望对象的时候,它总是被设置成了一种禁忌,当人们被强制遵守禁忌的限制,就是和动物区别开来,而另一方面,禁忌之存在,使得内部的体验反而变得正当化——禁忌是为了消灭一种暴力,但是人天生具有的暴力情绪则摧毁了我们内心的平静,而没有平静,人类的意识也就趋向于无。所以巴塔耶认为,我们遵守禁忌,屈服于禁忌,实际上就不会意识到禁忌,而只有僭越禁忌时才感到焦虑,这种焦虑感又凸显了禁忌,“体验将人带向达成的僭越、成功的僭越,体验同时又维持着禁忌,为了享受禁忌的乐趣而维持禁忌。”
所以色情是一种失衡,在这种失衡中,存在本身有意识地质疑自我,而禁忌并不是让如色情、死亡等的内心体验达到平衡,只有禁忌和僭越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走向平衡,“僭越解除禁忌,但并不消灭禁忌。这其中隐藏着色情的原动力,其中同时也有宗教的原动力。”所以僭越不是对禁忌的否定,而是“超越禁忌并将其补完”,也就是在连接中达到人类精神的平衡。巴塔耶从僭越出发,以反向的方式回过来考察禁忌,禁忌看起来是一种束缚,是对于杀人、战争等非理性行为的否定,但是实际上禁忌也是一种非理性,“谁又敢说自己在人群中没有克制过杀人的欲望,就跟对性的渴望一样真实,或者说一样渴求。”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攻击性的勃发,是用以维持大规模的充溢,所以在战争中能够找到色情的本质,它也是一种战争,一种攻击性的勃发,一种维持大规模充溢的方式,所以当禁忌约束了这种勃发和充溢,在某种意义上,当禁忌产生,禁忌对象反而变成了一种神圣,所以在僭越这种补充行为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跨过禁忌这道坎回到自由的状态,而是和禁忌一起激发着迷的状态,甚至回到原初的神圣性,“禁忌和僭越与这两个矛盾的情绪相呼应:禁忌让人拒绝,但是着迷引发僭越。”
禁忌和僭越在平衡中达到的神圣性,才是巴塔耶对于色情考察的重点。回到内心体验这个所在,它就是一种连接的存在,色情就是在可能性中建立寻求人类精神的一致性,他在序言中说:“我的立场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即发现这些相互对立的可能性是可协调的。”从一开始,人类害怕自身,质疑自身,所以用惊人的禁令威胁人类精神,而对色情,和对死亡一样,自然感觉到恐惧,但是,“圣女惊恐地避开好色之徒:她不明白,好色之徒不可告人的激情与她自身的激情并无二致。”这便是人类精神统一的可能性。
从表象上看,无论是死亡还是色情,都是一种不连贯的内在,这是一个个体存在和林一个个体存在之间的“深渊”,这道深渊在带来“头晕目眩”的同时,也带给我们“着迷”,所以,“我谈个体存在的生殖和死亡,目的在于呈现存在的连贯性与死亡是一致的,两者同样迷人,而其迷人之处支配着色情。”人死亡之后,不是无,而是在腐烂之后重归大自然,并再次以生命形式回归,这是死亡带来的连贯性意义;生殖中的精子和卵子本是不连贯的生命体,当他们结合便建立了连贯性,这是一种融合,而超越生殖意义的色情,巴塔耶将其分为肉体色情、情感色情和神圣色情,他在这三种形式中寻找连贯性,寻找融合,当人脱光衣服展示赤裸状态,就是破除了封闭,“这是一种交流的状态,揭示出存在超越自我封闭、对可能达到的连贯性的追求。”
所以考察色情,巴塔耶提供了融合的视角,甚至是神圣性的观点,色情中的女性伴侣就如献祭中的祭品,而男性则成为祭司,“两者自身均消失在最初毁灭行动所建立的连贯性中”,看起来,献祭是一种杀戮,是一种原罪,但是在献祭中,它也是僭越,它是神圣的,“她丢掉贞洁的同时,丧失了将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让自己不受侵犯的那个屏障:突然间,她向在生殖器官中爆发的暴力的性活动敞开自己,向从外界侵入她的非人的暴力敞开自己。”也就是说,在献祭的僭越中,仪式反而进入到生命的内心世界里,同样在色情中,“我们得到了爆发的体验,“一种爆炸性的暴力体验”,所以性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僭越。而在禁忌中,人只有结婚才能进入性生活世界,一旦僭越,就变成了狂欢的色情,两者连接在一起,在人类精神的平衡中达到连贯性。
所以禁忌而献祭,献祭而狂欢,狂欢而色情,这一种融合不连贯而产生的同一性为色情相关的暴力提供了神圣的维度,巴塔耶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基督教的冲动与色情生活的冲动“实为统一”。在他看来,在基督教世界里,禁忌是绝对的,它用自己的方式划定了神圣世界的界限,那些不洁之物、污秽和罪恶都被排除在外,它们被丢回到了世俗世界。但是僭越却揭露了基督教所掩盖的东西,也就是和禁忌相混淆的神圣之物,所以基督教在宗教层面发展了一种悖论:“接近神圣之物的道路是恶;同时恶是世俗的。”而巴塔耶认为,基督教的原始宗教性里有着一种僭越精神,它是一种颠覆禁忌的狂欢,是触及狂欢的真相,“通过禁止有组织的僭越,基督教加深了肉欲造成的内心混乱的程度。”
内心混乱中,肉欲当然被认为是一种色情,当然是一种禁忌,而僭越精神又让色情具有神圣性,它颠覆禁忌,所以在欲望的对象中,一方面是产生了一种低俗化的低层妓女,在道德、宗教层面对对象进行了限制,而这样的欲望对象“比禁忌更加漠然”,“她无法达到完美的漠然,她了解别人所遵守的禁忌:她不仅堕落,而且被赋予了了解自己堕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宗教构筑了一个神圣世界,而在这个神圣世界里,却有一种叫做“神圣卖淫”的行为,它让羞耻心成为仪式,“并承担僭越的意义”。
这无疑是一种悖论中的割裂,是对于人类精神不连贯的道德运用,低俗卖淫和神圣卖淫其实是模糊的,它在色情意义上甚至建立了某种“融合”的可能,而巴塔耶认为,禁忌和僭越的最大作用就是保持平衡,就是完成连贯性,所以需要越界,“如果必要,我们会赋予界限的破除以客体的形式。”这种客体形式便是将对象纳入其中,就像死亡一样,它不是无,而是成为对象,“我们不仅用不着死亡,而且将对象纳入欲望,后者其实是死亡的欲望,这样我们就将对象纳入了我们持续的生命中。”越界而为一种客体,客体而为禁忌和僭越的对象,在人类精神中,成为丰富生命的形式而不是抛弃生命,而这种客体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在对象身上,正是美将对象指定给了欲望。”
美的价值和意义,是对象指定的,而在对美的追求中超越了断裂,达到了连贯性的努力:“美成为欲望的对象是为了令美变得肮脏。不是为了美本身,而是为了在亵渎美的确定性中感受乐趣。”这便是禁忌和僭越构筑的平衡世界,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没有永远美的对象,也永远没有丑的禁忌,当色情既是一种污秽,又可以达到欲望的满足,于是,在色情世界里,“越美,污秽就越深。”永远在禁忌和僭越的关系里融合,永远在美与丑的对立中平衡,永远在色情的二元性中维持,巴塔耶说,这是一首生命的诗歌,在战栗、欺骗中迂回前行,在欺骗和可能中相融,“诗歌将我们带向永恒,带向死亡,并通过死亡,达到连贯性:诗歌是永恒。那是沧海,融入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