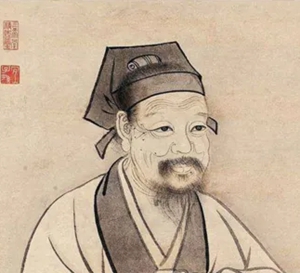|
编号:C22·2220421·1830 |
| 作者:[南宋]洪迈 著 |
| 出版:中华书局 |
| 版本:2021年12月第1版 |
| 定价:58.00元当当24.40元 |
| ISBN:9787101154481 |
| 页数:712页 |
《容斋随笔》是洪迈所著的一部古代文言笔记,内容涉及为政通鉴、人物品评、稗史杂记、职官选举、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二十类,是一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百科全书。洪迈在《容斋随笔》卷首中说:“余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先后,无复全次,故目之曰随笔。”洪迈读书治学用力专深,视野开阔宏通,学术触觉敏锐,大胆质疑,细心求证,对《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有辨误,使得《容斋随笔》有去伪存真的考订,也有入情入理的分析,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颇有见地,堪与《资治通鉴》媲美互补,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容斋随笔》写作时间逾经近四十年,本书甫一问世,就受到宋孝宗的褒扬,认为“煞有好议论”,宋人史绳祖推为“近世笔记之冠冕”,《四库提要》也说“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
《容斋随笔》:姑析其数端以为笑
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卷六 严州当为庄》
严州府的梅城,以最简单的游历方式出现在我面前:只是行走于梅州古城的那一条街道,在太阳炙烤下提前返回,没有登上严州府的城墙,没有发现梅花形之雉堞,走马观花之后匆匆返回。这是几天前的见闻,所见即所得,似乎对于梅城,对于严州,便已完成了一次造访。但是在念叨梅城以及严州的名字时,是有过略微的疑问:为什么那时叫严州?几天之后打开洪迈的《容斋随笔》,知道阅读至最后几张,看到这一则,才唤醒了前几日对严州之名疑惑的印象。
百科知识里说及这段历史:“宣和元年,升睦州为建德军节度。宣和三年,改睦州为严州,属两浙路,治建德,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青溪、遂安6县。”在《容斋随笔》中,洪迈似乎也简单地说及了此次改名,本名睦州改为严州是在北宋宣和年间的是,改名的原因是方腊起义,但是为什么叫严州,这里似乎隐藏着一段文史故事。传统的说法,严州之“严”具有威严之义,改严州就是取了此义。但是洪迈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改名为严州关涉的是一个人物,那就是东汉的严光,也就是严子陵,“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这是一重考订,但这也不是最终的结果,洪迈再深入考察,严光本来姓的是庄,因为避讳汉显宗孝明皇帝刘庄的名字,把“庄”改为“严”,所以史学家便写成了严光,这是第二重考订,洪迈深入其中,发现的是存在着的客观史实,由此从严州之名引出了隐藏的故事,洪迈便在这一则随笔之后提出了“后世当从实可也”的观点。
从实对待,这便是洪迈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这也是他读书所得——简单游离梅城,走马观花于严州,对名字不深入探究,或者根本不是一种阅读的方式,而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发现的是读书之用。从使金受挫、罢官归家而开始创作,历经40余年始成的《容斋随笔》似乎就是一本写给读书人看的书,或者是一本写给没有深入阅读的读书人看得书,这也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阅读方式,但是从一点点的疑惑,到一点点的深入,再到一次次的重评、辨伪与订误,追求的“从实”的实践风格便慢慢显露。40年的写作时间,并非是因为这本书写作之困难,而是洪迈在漫长的时间中一点一滴中积累下来,在卷一中,他开宗明义了此书的写作方式和态度:“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读书不多”当然是谦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是方法,这种即兴式的、随笔的记录方法重要的是“意之所之”——40年的积累,洪迈意到了哪些和严州之名一样的感悟?
没有关于写作目的的前言,短短几句话也是“随笔”风格的一种注解,但是简明的之语,随笔之记,所展开的是五集一千二百二十则的庞博世界,这里有政治通鉴、人物品评、稗史杂记、史论考辨、轶事遗闻,有职官选举、学校科试、典章制度、国计民生,动植物产,有经史掌故、诗词丛话、文章琐议、字韵训诂、碑帖器物,有天文地理、风俗节令、佛学禅理、医卜星相、灾祥术数……没有统一的编例,也没有清晰的条目,就是如洪迈自己所说是“随即记录”。比如第一卷所记,有关于乡邦掌故的欧阳询法帖,有关于父子同名的知识猎奇,有唐代宦官章兵开始的考证,有对于裴度卒年的考证,还有商榷格律、以诗证史、谈论诗艺等的内容,29则随笔已经呈现出内容广博的特点。但是书海拾贝式的随笔记录并非是良莠不分,并非是杂而糅之,一切可以被记之、思之、考据之、辩伪之,关键在有意,有意才能“意之所之”。
还是以第一卷为例,关于佛经中“半择迦”、六十四种恶口,关于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唐人重服章,都是读书摘录的知识点,所记是为了记录。但是29则中有很多却体现了洪迈的写作态度。第6则是关于端午的说法,“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八月五日为千秋节,之后指皇帝的诞辰,对此张说在《上大衍历序》上说:“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再引用《唐类表》中宋璟的《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的说法:“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由此洪迈认为,“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考查文本提出了千秋节和端午之关系,洪迈所得其实是打开了另一种可能:闻一多在《端午考》中引用了洪迈的这条随笔,以证“唐以前似乎任何一月的初五皆可称端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洪迈所引的两则材料中的关键字都是“端午”,但是清编《全唐文》却作“端五”,而张富祥注说《容斋随笔》中说:“古人以每月初一为‘端’,初二即称‘端二’,依次则称初五为‘端五’,也不知何据。”
端午或实为端五,洪迈之所得本身也留下了一种意,而他这种意又为后人开启了意,如此大约是随笔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第一卷的《浅妄书》一则,揭示了《开元天宝遗事》关于唐代记载的谬误,“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可笑之处在于,“《开天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所以洪迈认为,“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因为浅妄而毁之,这便是洪迈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随笔中便成为了“姑析其数端以为笑”的一种实践,那么,洪迈所要笑的究竟是什么?笑之后是不是还有一种期望?
文人轶事是洪迈《容斋随笔》中记录较多的内容,第二卷中关于文人笔下的牡丹,他引用的是欧阳公《牡丹释名》:“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但是洪迈考察所读之书,却并非如书中所言,白居易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有《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有讽谕乐府的《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又有《寄微之百韵》、《惜牡丹》、《醉归盩厔》等和牡丹有关的诗作;另外,元微之有《人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也有诗:“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的诗:“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这么多人写过牡丹,所以洪迈说:“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似乎在追问欧阳修之误。
同在第六卷,洪迈提出了关于仿作的问题,“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但是《七发》之后有许多的后继者,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崔骃的《七依》、马融的《七广》、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张协的《七命》构成了仿作的系列,洪迈认为,“规仿太切,了无新意。”但是,柳子厚的《晋问》用的《七林》之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为什么柳宗元用“七发之体”不落窠臼,就在于能创新,从而一扫文坛华而不实的弊病。所以很明显,在同一卷中,洪迈追问欧阳修之误和褒扬柳子厚之创新,就在于抨击“诸文士之弊”,以一种求实的态度读书。
在《文烦简有当》一文中,洪迈针对欧阳修的在《进<新唐书>表》中所提出的观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欧阳修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载史事较《旧唐书》为多,所用篇幅则较其为少,这是欧阳修对《新唐书》的肯定,但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是不是成为一种圭臬?洪迈的观点是:“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他举例《史记·卫青传》,其中写到:“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而《前汉书》对此段史事的书写是:“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比《史记》的五十八字省去二十三字,但是,“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文章之烦简必须根据实际来,并非只有一条标准,在某种程度上这要是在批评《新唐书》,批评欧阳修。而在《<史记>世次》中,洪迈则对《史记》所载周代帝王世次进行了辨驳,《史记》中所写的稷、契都为帝喾之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但是疑点在于:“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曰岁乃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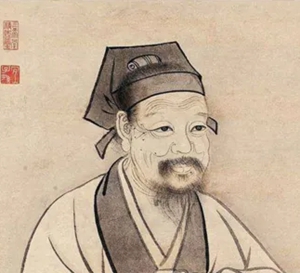
|
| 洪迈:意之所之,随即记录 |
洪迈为此批评道:“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追问是为了求实,抨击是为了求实,考据是为了求实,“后世当从实可也”成为洪迈的一种治学态度。在文人轶事上,洪迈考证了关于李白的两则轶事,在《李太白》一则中,世俗的观点认为:“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洪迈考察了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李华的《太白墓志》人为,“乃知俗传良不足信”,李白之死“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而在《太白雪谗》一文中,洪迈也记录了传统的说法:“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但是在阅读了李白的《雪谗诗》一章,洪迈认为,“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文人轶事之外,洪迈对一些字词典故也进行了考证,最著名的当然是关于“宁馨”、“阿堵”等的意义。“举阿堵物却。”“何物老媪生宁馨儿?”一般认为“阿堵”指钱,“宁馨儿”为佳儿,但是洪迈否定了这些说法,他举例前辈诗中有“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有“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帝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由此观之,“宁馨儿”怎么会是佳儿的意思?他认为,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就像在问“若何”也,再举例刘梦得的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所以洪迈认为这才是宁馨儿的真正提议,而且,“以宁字作平声读。”洪迈也考察了“凤毛”一词:“宋孝武嗟赏谢凤之子超宗曰:‘殊有凤毛。’今人以子为凤毛,多谓出此。按《世说》,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其事在前,与此不同。”关于“米牛”的来历:“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对于“不平则鸣”的疑问:“‘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
除了文人轶事、字词典故之外,洪迈的求实态度体现在对史实的考证了,他从历代经史典籍中对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在《张良无后》中洪迈将张良与陈平的历史命运进行0对比,提出了疑问:“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财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原因就在于张良说出了“养虎自遗患”的话,“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这无疑是一种咎由自取;历史典籍似乎把汉景帝称为“恭俭爱民”的贤君,但是洪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从博戏杀吴太子、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等事例而认为,“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
实际上洪迈考察历史,并非仅仅在于辨析真伪,而是古为今用,提出他的政治主张。在《秦用他国人》中,他认为,刘国所用之人都是宗族及国人,而秦国却多用他人,所以洪迈提出观点:“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对比曹参和赵括,曹参之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洪迈感慨到:“呜呼!将相安危所系,可不监哉!”在《拔亡为存》中,洪迈举出许多以一己之力转危为安的典型,于是他发问:“以今准古,岂曰无人乎哉?”《汉祖三诈》中他记述了汉高祖的虚伪,“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由此他认为丧失信用的可悲:“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燕昭汉光武之明》中,洪迈举出了“田单复齐国,信陵君败秦兵,陈汤诛郅支,卢植破黄巾,邓艾平蜀,王浚平吴,谢安却苻坚,慕容垂挫桓温,史万岁破突厥,李靖灭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室,李晟复京师”等有功之人,但是他们的命运还是“为谮人所谮”,所以洪迈认为平庸的君主不值得责备,真正可怕的是像“营营青蝇”一样的小人。
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洪迈的随笔实则具有经世之用,而这种现实考量的意义则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信近于义》等数条是对于阅读朱熹《论语精义》的随扎,但洪迈再《容斋随笔》中没有提及朱熹任何文字。“予切以谓义与礼之极,多至于不亲,能至于不失其亲,斯为可宗也。然未敢以为是。”在这里他指出了义和礼做到极致意味着真正人伦的丧失,只有亲近的人才是值得尊崇的,“能至于不失其亲,斯为可宗也。”在《刚毅近仁》中他提出了区分“近仁”“鲜仁”的关键:“刚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讷者,必不为巧言。此‘近仁’‘鲜仁’之辨也。”在《求为可知》中,洪迈批评了急切追求而为人所知的行为,“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为可知,则亦无所不至矣。”引用《论语·里仁》的观点,“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本领;在《陈轸之说疏》中,洪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战国权谋之士,游说从横,皆趋一时之利,殊不顾义理曲直所在。”在《忠义出天资》中则提出了忠义天姿说:“忠义守节之士,出于天资,非关居位贵贱、受恩深浅也。”《朋友之义》则强调了“朋友之义甚重”,只是历经本朝百年,“今亡矣!”
“今亡矣”是一种失望,而对于使金受挫、罢官归家的洪迈来说,自己所面对的不正是希望破灭的现实?但是用40年在阅读中积累,用40年“意之所之,随即记录”,不也正是对内心抱负的一种呼应?正如在《里仁》一则里所说,“仁之为道大矣,尚安所择而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