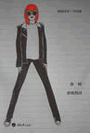 |
编号:S29·2130517·0987 |
| 作者:春树 著 | |
| 出版:重庆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45.00元亚马逊22.50元 | |
| ISBN:9787562469056 | |
| 页数:343页 |
“这是我写诗至今第一本个人精选集,我的所有能印出来的最好的诗都在里面。”作为第一本个人诗歌精选集,春树似乎要穷尽诗歌的写法,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从成为美国《Time》的封面人物到《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人物,从央视《面对面》将他称为是“一个有勇气、有斗志的人”到获第五界网络金手指网络文化先锋奖,他似乎一直在青春之路上行走,而封面那一抹红色似乎是青春的一种个性标签。“作为‘酷诗歌’的代表,春树的写作一直引人注目。在她身上体现出的所有叛逆、不满和愤怒,不掩饰的激情,不甘平庸的精神,永远在寻找出发点的挣扎,说到底都是极其可贵的青春气质,令人赞赏,也令人艳羡。”李以亮的这段评语或许可以在他的诗歌里找到激情和挣扎,和“我与你们都不一样”的自傲与孤独。
一个身上没有文身的人
心存许多秘密
他总是
害怕文身会暴露身份
——《独自发狠》
241页的诗歌,是一个人,也叫“某个人”,某个人的意义是“独自发狠”,独自有着暴露身份的“秘密”,“一个心存秘密的人/身上没有文身”,这是2009年2月22日写诗的春树,而在四年之后的2013年6月28日早晨,也是我一个人,面对一首文身的诗歌,以及不知道是不是有文身的春树,一个人对于一个人,是写作和阅读,也是秘密和无知,但是,必定和某个人文身与否无关。
我不知道春树是否也是文身,我只是在更大的无知里寻找属于某个人的秘密。春树——不是“他”?这是一个阅读的起点,太迟了,竟然在241页的诗歌里寻找答案,我的意思是我竟然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将春树当成了一个男人,一个“他”,该如何忏悔我的错误,该如何揭露无知带来的秘密?从搜索开始,似乎这是一条寻找性别秘密的最佳途径,就像用偷窥的心态检查某一个人的身体里是否有文身。“2004年2月,20岁的春树成为美国《Time》的封面人物,美国人称她为“新激进份子”。 这一期的封面特写,还报道了21岁的韩寒。”这是春树最革命性的一次露面,但是没有性别的“他”或者“她”,而我也没有订阅《Time》周刊(当然订阅了我也收不到);“2004年8月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被认为是‘一个有勇气、有斗志的人’”。这是第二条关于春树的介绍,依然没有“他”或者“她”,而且作为我自己孤陋寡闻的需要,从不看央视的这档节目;再接下去,是:“2004年6月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人物”,也没有性别;“2004年9月应邀前往挪威参加国际诗歌节”,没有;“2004年2月获得过第五界网络金手指的网络文化先锋奖”,还是没有;再继续,在中国现代诗歌文库编委2005年12月初版2006年9月修订编的《中国现代诗歌大全》中,是这样介绍的:“春树,1983年6月26日生人,2000年从北京某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曾经在‘诗江湖’网站掀起巨大波澜,其板砖被选入《南方周末》‘板砖爬行榜’;曾经被‘诗江湖’网站称为最年轻的优秀诗人。”还是没有“他”或者“她”。
随着搜索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我无知的可怕,也越来越觉得春树的秘密藏得越来越深,似乎一定要剥开所有的衣服,才能发现那个“暴露身份”的某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文身。还好,在维基里找到了,“春树(1983年-),原名邹楠,在《北京娃娃》一书中化名林嘉芙,出生于山东,当代中国作家,中国大陆80后代表人物之一。”这是文字的简介,而在旁边是一张标注着“邹楠”的照片,戴着墨镜,穿着连衣裙,涂着绿色的指甲油,尽管双手做保护状,尽管眼睛被墨镜遮住了,但依然能从远处的春光中感受到女人的某种妩媚,甚至在图片下面详细写着有关春树的现实身份:“笔名:春树;出生:1983年6月28日,括号29岁,山东;职业:作家;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裁:诗歌、小説、散文”。除了照片,在“经历”一段写道:“除了写作之外,春树也喜爱阅读,特别是诗歌,她曾说她对诗歌的爱好胜过散文与小说,还曾在‘高地音乐网’为捍卫诗歌的荣誉而与几十人舌战一周。此外她也热爱音乐,尤其是庞克与摇滚乐。”
终于出现了“她”,作为对照片的补充,我终于最终确定春树是一名女性,29岁的女性,而我在阅读她的这本《春树的诗》的时候,她正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在此也一并祝她生日快乐。但其实,作为一个读者,除了有些做作的“无知”之外,也是玩了一个关于秘密探寻的行为艺术,其实春树是“她”是一目了然的,我可以直接在“图片搜索”中找到诗人春树属于女人的各种妩媚照,也可以点击进入春树的新浪博客,在最近一首《诗一些,2012——2013》的左侧,在“春树V”的上面看到一张穿着无袖衫、没有戴墨镜的春树,甚至如果无聊,在读完这本《春树的诗》的封二“诗人简介”:“春树,80后最著名诗人。已出版五部长篇小说及个人诗集《激情万丈》。代表作《北京娃娃》,最新作品《光年之美国梦》。主编《80后诗选》(三册)。”之后直接翻到封三,会看见一张竖形的照片,剪着短发歪着头,赤裸着大腿支在凳子上,而她前面键盘,以及画面外正在写着小说、诗歌、散文,或者正在发布博客的电脑,除了不知道身上是否有文身,总之是一张女人的脸,是“她”的脸。
甚至在封面中,就是一个红头发,准备跳舞或者正在跳舞的“她”,那样子仿佛能在她的诗歌《翻滚着云彩的瑞典的天》里找到注解:“我侧着身/我穿着红色圆点的紧身裤/和绿色带骷髅头的长T恤/秀发掉了下来/遮住了眼//”紧身裤,长T恤,还有遮住了眼的秀发,“她”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我仿佛读着这首诗,完成了寻找。“一个身上没有文身的人/心存许多秘密/他总是/害怕文身会暴露身份”。当把诗歌中的“他”换成“她”,也是对于我这次寻找的注解,其实,我并不是要那么无聊地寻找所谓的身份,所谓的性别,他或者她,少女或者女人,29岁或者30周岁,对于阅读诗歌的某一个人来说,其实没有实质的意义,我只是想在寻找的过程中体会一种秘密,那个秘密的世界里有反叛的青春,有矛盾的爱情,有逃避的成长,当然还有在物质和精神中游离的诗歌,而那个关于“文身”的秘密只不过是个隐喻的开头:“洗掉文身/你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我的脑子被灌了水/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全磊聊天有感》)”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春树的确在进行着对于女人本体的怀疑,从曾经的辍学到后来的激烈争论甚至争吵,反叛一直写在春树的个人经历里,所以“她”的文身或许也是一种逃避的需要,一种解构的努力。“躺在床上的女人/和我有一点联系/是什么联系我也说不好/于是我信了那个人是我”,躺在床上的女人,只能被自己相信,像是一次无奈,也像是一种妥协,而在《梦中人》里,那个红裙子穿容光焕发的女人却“越来越苍老”,而这种苍老不是对抗时间,而是对抗着自己:“我不该长这么大/知道得这么多/我应该缓缓成长/用十年长一岁的速度/慢慢地/供你把玩”,缓缓成长,放慢速度或者也是对于成长的一次否定。但是“她”是不容更改的,“难道只是因为我是女人/我的月经迟迟未来(《月经》)”,是的,月经是“女人们不愿说出口的秘密和隐痛”,是属于“她”的身体属性,而且不仅是身体属性,生理属性,还是精神属性,既“沉重宏大”,又“卑微低贱”。
而当无法摆脱“她”的属性的时候,春树一定会把自己从固有的模式中挣脱出来,所以我读到了她的青春呓语,那些残酷而且锋利的青春不是只是对于岁月的反抗,更是对于自我的释义和定位。青春不是“听着罗大佑、喝着酒”,也不是因为相信而让一个“疯子哭了”,更不是只有朋克、摇滚、抽烟,对于春树来说,青春是“十六岁少年杀母事件”,是关于20美元可卡因的故事,甚至是“别他妈再说什么你看不起青春期了”的暴力。少年杀母,“我想我们最终也会碰到同样的处境”,但是这种看透的本质一旦说出来是不是也是“残酷青春”?而在2009年春天的“普通一夜”里,“在这个故事里/我试图讲述的/不是关于我/而是他们”,更像是一次逃避,一次对于青春的拒绝。同样是逃避和拒绝,除了“不是关于我/而是他们”的置换,剩下的就只有幻化,在《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里,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是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万人聚集在广场和街头/红旗随风招展/这是红色和绿军装的海洋/那些年轻的生命/洁白的牙齿/那些耀眼的青春//”这是幻化的时代,这是幻化的青春,革命或者狂欢,对于青春来说何尝只有耀眼的色彩,而春树甚至将自己进行了彻底否定,“你问我/可否记得上辈子是谁/我不犹豫/文革中死去的红卫兵//”而这无限接近虚无的自我又在哪里,对于春树来说,对青春的逃避只是一种呓语,一种甚至没有丝毫颠覆性只有暴力性的革命,而“我今生最想拍的这部电影和历史无关/我只关心这些少年的青春”,似乎是跳出了自我的窠臼,带着某种救赎的意义,但是自我都沉溺在虚无中,何来解救何来重塑?
而和青春有关的必然是爱情,是成长中的爱情,这里有女人的渴求:“我们走啊走啊/我一直没有理由牵住你的手/我想拉拉你的手//(《芦苇岸》)”,也有经历过的沧桑:“我迈出门去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那些刻在墙上的我爱你/慢慢褪色//(《皇后》)”而对于春树来说,却仍然是像青春一样被锋利刺痛的无奈:“如何保持/独立、完整、互不干涉/又深深地/相爱呢?//(《天使诗篇》)”独立、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和深深相爱之间的矛盾是个体和个体、青春和青春之间的矛盾,也是自我在逃避和选择,在爱与被爱之间的喟叹,只是没有答案,青春在路上,爱情在路上,成长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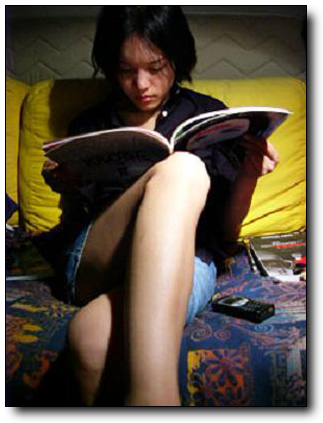 |
| “她”春树:有时候我把影子当成了文身 |
“哦,那就走走吧/你起码可以走在大街上(《他们睡在大街上》)”,这是生活的无力;“打碎了一只杯子/把它扔到了垃圾袋中/并在上面撒了一泡尿(《我打碎了一只杯子》)”,这是生活的无聊;“我凝固的微笑一直保持到无法再笑(《我的上一次自毁》)”,这是生活的无助;“遇到的事和人/都在帮助我自己成为我自己(《西班牙的雨不断降落在平原上》),这是生活的无奈……在这些无力、无聊、无助和无奈中,实际上是无意义,“兔子这种动物/没有意义/虽然没有意义/我还要写下去/因为生命也没有意义//(《兔子》)”。
没有意义的生命,而一旦写下来是不是就是意义?这其实也是春树的悖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到底是为了解构呢还是为了建构?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对于春树来说,这种矛盾就是处在物质和诗歌之间的矛盾,“想写诗/我不能以唐诗宋词的形式/也无法以下半身的态度/来描绘我的感受(《生活碎片·买烟记》)”,所以在春树看来,诗歌是“让喋喋不休的群众去死”,而不是像鸟诗人一样“以诗海战术打入诗歌圈”;诗歌是“带给我好心情”的良药,不是那些自杀的女诗人告诉别人“背诵我过去的诗歌”,诗歌是告别孤独,却也是享受孤独,诗歌是拒绝世俗,却也在世俗中挣扎,就像春树生命里的某种仪式,是被抛弃,也是在寻找,是形而上的坚持也是形而下的日常生活。
青春、爱情和生活,孤独、反叛和坚持,在春树的诗歌里其实并没有另类,在手淫、阴道、自慰等色情语言的背后是身体,在反抗、暴力、残酷等革命语言的背后是成长,在褪色、牵手、玫瑰等爱情语言的背后是成长,而在这些词语组成的青春岁月里,春树品尝的绝不是孤独,而是被遗忘:“这首歌是唱给你们的/唱给我们的 包括在大街上走着的 在呼吸着的/在迷惘着的 在享乐的 在痛苦的/每一个人/我们永远只是一个人//(《生命不容等待》)”因为害怕遗忘,所以要彰显个性,所以要反叛,所以要“比痛苦更痛苦”,甚至连一首诗的题目都以“没有题目啊”作为隐喻和象征。
“我和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是两类人了/我们看上去/都像变了一个人”,其实在解读中,我们容易把无意义当成了“伟大的隐喻”,也容易把失去的自我当成是个性,他和她到最后,其实都是被消融的个体被解构的性别,“都变成了一个人”,也永远是一个人,青春、爱情、诗歌,就像和身份有关的那些文身,或者是他的,或者是她的,或者已经洗去,或者是身上永远的秘密。而我在检阅完某个人的秘密之后,高喊一声:动物凶猛!然后就如诗中所说:
我拿她毫无办法
我并没有想好要说什么
只能合上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