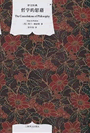 |
编号:B84·2150517·1173 |
| 作者:【英】阿兰·德波顿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版社 | |
| 版本:2012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30.00元亚马逊15.20元 | |
| ISBN:9787532756759 | |
| 页数:284页 |
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和尼采,这六位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构筑了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的主体,这是一次以其英国式的笔调引领我们进行的一次轻松哲学之旅,典雅风趣,阐述了哲学对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挫、缺陷、伤心和陷入困难的慰藉。哲学或者并不是枯燥的,阿兰·德波顿认为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微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阿兰·德波顿以自己驾驭文字的才华把通常是枯燥晦涩的哲学思想写得生动活泼而通俗易懂,把哲学从高头讲章拉下来,进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的文字在译者资中筠先生看来是“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
《哲学的慰藉》:我愿从斯人游
考虑以下两句话:愿死亡降临于我正在种卷心菜之时,我就可以既不为死,也不为未完成的种植而发愁。
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随笔集》Ⅱ,17)
——蒙田智慧试卷
死亡似乎是突然降临的,降临在我身上,降临在种卷心菜之时,所以死亡是一种毫无准备的终结,终结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一种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是当一切画上句号的时候,是对于死亡永不停止的恐惧,还是对未完成种植而发愁?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死亡却是一种期望的状态,是将一切终结的愿望,因为再也不会恐惧,再也不会忧愁,所以,对于“什么是对待死亡的明智态度?”的答案其实是解构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死亡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了,也意味着我不再受制于有形的一切。
但是,人生的问题并不在死亡降临的抉择中做出回答,“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这是一种现实,是完全解构死亡“明智态度”的现实,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何来种卷心菜这样一种劳动,何来未完成种植而发愁,又何来死亡的突然降临?没有机会进入种卷心菜这样的情境之中,也就意味着没有进入对于死亡明智态度的问题里,也就逃离了关于形而上的回答。这是“蒙田式的智慧的试卷”,相关的题目还有,一个无法忍受唠叨和妒忌妻子的村民用镰刀“把那撩起他妻子如此狂热的器官割了下来,甩到脸上”,到底该如何解决家庭争吵?妻子是在唠叨还是在表达情爱?一个绅士开玩笑说他宴请客人吃的是猫肉饼,最后导致一个年轻女士大惊失色而死亡,请问这件事的道义责任在哪里?一个人自言自语不会被认为是神经病,可是骂自己是大笨蛋的时候是不是自轻自贱,那么人应该给自己多少爱?
狂热的器官被割掉,消除了争吵却带来了厄运;宴会吃下猫肉饼,是一种礼节还是亵渎;自言自语而自轻自贱是不是一种对自己的爱?蒙田的智慧试卷仿佛都把人拉向了一些悖论中,既解构了因果又设置了可能,既消除了对立又制造了矛盾,而这种悖论在蒙田看来,却指向一种智慧,悖论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困囿于知识,受制于学问,期望从常识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这写矛盾和对立,这些因果和可能却和学问无关,和知识无关,而是对“智力重新排队”,排队的结果是“出现令人惊讶的新精英阶层”,而看来不入流的人却在这些智慧中超过了“那些久负盛誉而其实难副的传统候选人”,也就是说代表智慧的新精英阶层击败了代表知识的传统候选人,对于这一结果,“蒙田就无比欢欣”。
为什么这是蒙田想要的智慧,为什么这是蒙田认为的聪明人?蒙田就是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学问与智慧,所以对于他来说,“生活得快活而合乎道德,是一种智慧的知识。”而不是一直以来关于聪明人的评价标准:关于三角形X边长和X角之间的关系,关于主语谓语系词量词的分析,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第一动因的论据,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翻译。尽管蒙田在这些所谓知识的题目中也回答得很好,但却费时关于聪明人的唯一标准,他不喜欢神秘的书,不喜欢晦涩的理论,不喜欢形而上的命题,他把懒散看成是一种策略,他阅读好看、易懂的书,在他看来,在那个够格的、半理性的人的肖像里,可以不会希腊文,可以有时放屁,可以一顿饭后就改变主意,可以对古代哲学家一无所知,只要在善良而平凡的生活里,“努力寻求智慧而从未远离愚蠢”,就足矣。
 |
| 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藉中“无比欢欣” |
“不论我们的生平多么微不足道,从自己身上得出的洞见还是胜过从所有的古书中得出的。”所以在蒙田的智慧世界里,他们不是智力的缺陷者,而是智慧的享受者,就像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的人,如何去思考死亡降临时的种种恐惧和不快,如何回答对待死亡的形而上态度?所以真正有缺陷的反而是那些把只是、学问看成是人生资本并为之追求和努力的传统候选人。在他们这些抱着理性的人看来,那些够格的、半理性的人存在着各种缺陷,包括性缺陷,包括文化的缺陷,包括智力的缺陷,但是在蒙田看来,对理性的错误自信就是产生白痴的源泉,也就是说,这种自信间接地也产生缺陷。性缺陷可以重新在做爱时学会倾诉,学会抽调起羞耻感,“自始至终努力使我们与自己的肉体和解。”也就是从世俗的囚牢里,将自己从肉体的缺陷中解救出来,开辟一条通向寝室的私密忧愁的道路,把完整的、赤裸裸的肖像再次呈现出来;在文化的缺陷中,不要把陌生的风俗当成是一种野蛮和怪异的东西,它也是一种符合当地习惯的存在,看不见这些存在的其实是另一种缺陷,“蒙田能够为自己身上那些在当地罕见的特点找到合法性——罗马性、希腊性,更接近墨西哥人和图比人而不是加斯科涅人的一些方面。”
“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那写在天花板木梁上的57条语录,引用自泰伦斯,对于蒙田来说,其实是重返人类的一种智慧之路,在“无以解忧,唯有读书”的生活中,蒙田建造了自己的智慧王国,他远离那些价值,远离那些标准,远离那些知识,在法国西南部的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头上,在华丽的城堡式巨宅里,与妻子弗朗索瓦丝、女儿莱奥诺以及仆从和牲畜,住在一起,这是一种隔绝,一种逃避,但实际上却是在“对缺陷的慰藉”中寻找遗落的智慧,寻找人生的意义。
缺陷不是产生悲观,而是重新寻找慰藉,不是学问面前的无知,而是重新定义智慧,“我爱智慧”不仅在蒙田那里,在更多的哲学家那里都抵达着世界的本质和真相,“我爱智慧”也是哲学的真正意义,“通过哲学求得智慧。”这也正是在各种世俗的“缺陷”中另外建立如蒙田那个城堡的世界,“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一小群人是苏格拉底,是伊壁鸠鲁,是塞内加,是蒙田,是叔本华,是尼采,他们面对的是与世不合的现状,是缺少钱财的困顿,是遭受摧折的经历,是伤心悲痛的人生,是苦难发疯的世界,而在阿兰·德波顿看来,他们都在这一种“我爱智慧”的慰藉中找到那些通向人生真谛的话语。
智慧从何而来,意义如何阐述?在阿兰·德波顿提供的这几个给人以慰藉的先哲身上,都有着被传统世界定义的“人生最大的痛苦”,苏格拉底一年到头穿着一件袍子,几乎总是打着赤脚,妻子桑娣帕以凶悍著称,他身材矮小,长着大胡子,脑袋秃顶,扁鼻子、大嘴、肿泡眼,被人称为螃蟹、猩猩或者怪物,而且他长长对于那些天经地义的常识置之不理,向诸神祈祷祭祀、以多蓄奴隶为荣,在苏格拉底看来都被鄙视,而对于他来说,比这些仪式和常识更让他感兴趣的是:一只跳蚤能跳相当于它身体几倍的高度?蚊子哼哼是从嘴里还是尾部发声?“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一定是跳蚤问题——常识可能更值得深究。”对常识进行质疑和批判,使得他成为一个异类,阿里斯托芬在戏剧中丑化他,三名雅典公民对他提起诉讼,告他不敬城邦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
而伊壁鸠鲁的遭遇也一样,他的助手梅特多鲁斯的兄弟蒂莫克拉特散布传言,称伊壁鸠鲁一天要呕吐两次,因为他吃得太多了;斯多葛派的狄奥提马做了一件刻薄的事:他发表了50封淫荡的信件,硬说是伊壁鸠鲁酒醉之后性欲狂乱时写的。塞内加在指出了尼禄的残暴:“当然,谁都知道尼禄残暴成性,他弑母杀兄之后,只剩下杀师了。”他失去了家庭、朋友、名誉,政治生涯也从此断送,并被流放到科西嘉是广袤的罗马帝国中最荒凉的部分,“我不允许命运之神对我作出判决。”最后在自杀不顺利、学习苏格拉底喝毒药没起作用之后,最后放进蒸汽浴室窒息而死。而从6岁时就深陷在绝望之中的叔本华,一生就在伤心悲痛中成为一个受难者,1821年,叔本华与一名19岁的歌手卡罗琳·梅东坠入情网,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10年,但叔本华无意把这一关系正式化:“结婚意味着尽量做使对方讨厌之事。”但是他向往一夫多妻制,最后却变成了一种亵渎。而称大多数哲学家“卷心菜头脑”的尼采,把自己称为“命中注定,我是第一个像样的人”,他在一间可以眺望山景和松林的农舍里写作了7年,他在费克斯山谷中看见人类历史新的道路,他在酒神力量中痛斥基督教,最后在1889年的冬天彻底崩溃:“他拥抱了一匹马,随即被送回他的住处,他在那里打算刺杀德国皇帝,策划一场反对反犹主义者的战争,越来越肯定自己是酒神、耶稣、天主、拿破仑、意大利国王、佛、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伏尔泰、亚历山大·赫尔岑和理查德·瓦格纳——视几点钟而定;然后他就给塞进了一辆火车,运到德国的一家疯人院,以后由他的母亲和妹妹照看,直到11年后去世,享年55岁。”
但是这他们的苦难、伤心、悲情和死亡中,却始终有一种力量,一种远离世俗的力量,一种反对权威的力量,一种打开智慧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他们获得慰藉,让他们独行于世,甚至让他们不朽。“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苏格拉底在审判日这样解释真理和灵魂的意义。他拿着一杯毒酒却还在讲述着哲学,在雅克-路易·大卫1786年秋的画作上成为永恒,苏格拉底的意义就在于:“哲学家向我们指出一条路,可以摆脱两种强有力的错觉:应该永远听从舆论,或是决不听从舆论。”而把快乐看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的伊壁鸠鲁鄙视现实的快乐规则,鄙视不深入内心而凭直觉获得的快乐,“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对于他来说,喝水而不喝酒,一顿饭有面包、蔬菜和一把橄榄就满足了,也就是说,不处于现世的痛苦之中就是最大的快乐塞内加的挫折词典里有愤怒,有震惊,有不公正,有焦虑,有受嘲弄——从脚趾头绊了一下到死亡都能算,但是,在他看来,每一种挫折的核心都是因为主观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产生的冲突,在我们的脖子上“从来是套着绳索的”现实存在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理解挫折,并将其变成必然到来的遭遇而坦然面对。而叔本华在生命意志的理解中获得慰藉,“在他的生活和不幸的过程中,他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命运多于自己的命运,因而行为更像是个知者,而不是受难者。”同样是知者的尼采在费克斯山谷散步时看见了文明的曙光:“最野蛮的力量开辟了一条道路,主要是破坏性的;但是它的工作是必要的,为了以后更为优雅的文明能在此建造大厦。”
一杯毒药,一次放逐,一些疯狂,一种死亡,对于常识而言,厄运降临带来的是痛苦,但是在在分不清卷心菜和莴苣的智慧里,世界却以另外的方式被打开了,他们是受难者,也是享受者,他们在世俗和权威中遭受挫折,但是却寻找到了自我完成之路,即使“交媾之后立即听到魔鬼的笑声”,即使在达到完成的困难中甜蜜的抚慰是一种残酷,即使舍弃种种而几乎在禁欲之中,但是在哲学的慰藉中,在智慧的寻找中,真理、意义、理性和生命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就如尼采所说:“厄运和外界的阻力,某种仇恨、妒忌、怀疑、顽强抵制、强硬反对、吝啬、暴力,难道不都是有利的条件,无此则任何伟大,即使是美德,也难以成长起来?”
用挫折成就意义,用死亡理解智慧,人类的苦难并不止于此,人类的伟大也并非只有这些,“时钟的水从一钵滴满另一钵”,其实对于阿兰·德波顿这个活在现世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发现和继承,重要的是理解和慰藉,就是在这些前人的慰藉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愿从斯人游”——“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