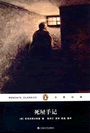 |
编号:C37·2151113·1242 |
|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45.00元亚马逊15.60元 | |
| ISBN:9787532154838 | |
| 页数:360页 |
“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被称作繁重的苦役,与其说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 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发表的一部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书中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见闻。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由于结构巧妙,交织成一幅沙俄牢狱生活的鲜明图画,勾画出各种人物的独特个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死屋手记》:每个人都是很苦的梦想家
“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是指一个被剥夺了个人意志的人,但是只要他能够花自己的钱,他也就拥有自己的意志了。
——《第五章 第一个月》
四周是无法逃离的高高围墙,戴着沉重的镣铐,接受各种肉体的惩罚,对于每一个被关在荒芜辽阔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监狱里的犯人来说,他们失去的是人身的自由,他们遭受的是身心的戕害,他们面临的是徒劳的抗争,可是如何去寻找那一点可怜的“意志”?意志是活下去并且期望走出监狱?意志是接受鞭笞却寻找逃跑的机会?其实,在一个被隔绝的世界里,在一个充满死亡阴影的地方,意志无非是一个个梦,它在虚无中变成希望,它在迷乱中成为安慰,而这个梦终究要破灭,而带着这个噩梦回到自由世界,所谓的意志也早就变成了一种非人的疯狂。
“是啊,人是顽强的!人是能适应一切的动物。”这是我在进入监狱,以致最后获得自由,对于所谓的“人”下的最好的定义。而对于一个有着贵族身份的人来说,这个定义的意义就在于自我认同里编织一种自由意志。在这个处在城堡边缘的城墙后面的监狱里,不管是一般的罪犯,还是终身在监狱里的“特科犯”,每个人起先都是一种绝望。这里有杀了营长格里戈利·彼得洛维奇的最大的军事囚犯希洛特金,有打死了自称“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少校的卢卡·库兹米奇,有得了肺病已经奄奄一息米哈伊洛夫,有杀死怀疑是不贞洁妻子阿库立卡的希什科夫,无论犯了什么罪,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命运都被终结在这样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在这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同一道围栏的缝隙,在同一个时间都看到同一堵土墙,同样的守卫,以及同一片小小的天空,而在年复一年相同的环境里,磨灭的正是一种生存的欲望:“有一次我在想,如果想要完全粉碎、摧毁一个人,对他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使最冷血的凶手也会不寒而栗的惩罚,就是逼迫他去做全然无用、甚至荒谬的工作。”
隔绝的世界,在那些囚犯最初进来的时候,是陌生的,但是陌生并不是可以让你拒绝,相反,你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些特殊的规定,那些自己的服装,那些特有的礼义和习俗,都让这里变成“一间活死人的屋子”,活着,想失去了一样,尤其是那些终身被监禁在那里的特科犯,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曾有过走出去的期盼,从来不曾有过自由的希望,“你们有期限,我们是终身在监狱里的。”所谓绝望,就是在看见了结局的世界里行尸走肉。当然,失去自由并不是最悲哀的事,最痛苦的是不断地有人受到鞭笞,五百,一千,甚至两千,有人甚至只想一死了之,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刑罚,那个叫亚历山大的囚犯,为什么固执得不配合治疗“不肯痊愈”,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治疗如何痛苦如何折磨人,也终究比不上鞭笞,而如果他的脖子康复之后,返回牢房就意味着要接受一千下的鞭笞。
鞭笞或者只是肉体的惩罚,而死亡阴影更是弥漫在其中,让人无从逃脱。“凡是判了刑的囚犯不管生什么病,都得一直戴着这副脚镣。”奥尔洛夫,这个已从棍棒下存活下来的囚犯,本来已经开始梦想逃跑、自由、田野和森林,但是在得了肺病之后,他终于没能让梦想成真,最后戴着脚镣在囚犯眼前死去。而另一个囚犯,终究无法承受下半身的刑罚,在出院两天后却又被送到了医院,最终在同一医院的同一张旧床上去世。因惩罚而死去,因折磨而死去,监狱无非是一个专制社会的缩影,“总而言之,对他人的肉体施行暴力的权力是我们社会的毒疮之一,是尝试湮灭民主的最强暴手段。是社会必将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的根源。”
实际上,在这个荒谬的围墙内,在被惩罚的监狱中,在弥漫着死亡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意志”,这是心灵的慰藉,也是对于专制的一种反抗。意志是犹太囚犯伊萨·弗米奇·蒲姆斯泰喜爱洗澡洗到浑身麻木、失去知觉的程度;意志是“最可笑的天真、愚蠢、狡猾、大胆、直率、胆法、自吹自擂和傲慢混合于他一身”的囚犯想着服完刑期后娶个新娘;意志是彼得罗夫“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住他”的那种疯狂激励;意志是达格司坦的鞑靼人阿雷和兄弟一起“从不与人吵架,大家也都爱他”的泰然;意志是在悲伤而沉重的日子里喝酒、哭泣、争吵和打架——监狱里走私酒,似乎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一种乐趣。
为什么在监狱里能够走私酒?这其实也隐射了一种社会问题,很多人因为走私罪入狱,但是在监狱里,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走私行为却并没有杜绝,甚至发展成一种产业,有人卖酒,有人买酒,“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在特殊世界里的特殊行为,反而变得正常,“有很多人是因为犯了走私罪入狱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酒还能被带进监狱里来。”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而其实,走私的意义就是隐秘的犯罪,也就是说,在监狱这个惩罚犯人的地方,却成为另一个滋生犯罪的地方。
而在意志世界里,更大的安慰便是宗教,莱慈根人努拉就非常虔诚于真主的信徒,在监狱里他神圣地作着祈祷。在他们心中,信仰变成支撑自己的一种力量,也变成丰富世界的一种表情,如果哭泣,就意味着失去了耶路撒冷,而在呜咽声达到最盛的时候,就意味着犹太人返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就需要转为患了、歌唱和笑声,而在朗读祷辞的时候,“大部分的声音应该尽可能地表达幸福,而且要在脸上表现出严肃和尊严。”依靠宗教的信仰和力量来抵抗监狱的生活,实际上也无非是一种悲哀,犯罪或者是一种善的泯灭,而通过宗教救赎来获得那种意志,陷入的是另一种茫然。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意志,而作为曾经的贵族,我的意志当然是一种身份上的强烈认同感,虽然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同样失去自由,都同样面临刑罚,但是贵族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却也延伸到这个封闭世界,在我进入监狱的“最初印象”中,对于前贵族,囚犯们都抱着一种阴暗、无情的心理,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监狱里起先是四个贵族,一个是卑鄙下流的家伙,一个是弑父者,一个是怪人,贵族群像似乎也都符合我的最初印象,所以我在进入监狱之后,作为一个新贵族,似乎需要融合,“我自己都希望能尽快地去做工,只是为了快点弄清楚,我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便开始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走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轨道。”走入“贵族”的生活,就是需要凸显一种身份,而在这个可以用钱买到走私的酒的世界里,钱也照样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
所以在监狱生活里,自然形成了一种“贵族意志”,当卖酒的囚犯格辛完成了交易,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身份的回归,“在监狱里喝醉酒有着一种特别的贵族气质。”而除此之外,贵族可以花钱雇人演奏音乐,可以让苏士洛夫我洗衣服,可以梦想着漂亮的女人,可以成功地贿赂卫兵,“假如我吃不惯官方的伙食,又有钱支付自己的伙食的话,每个月付三十戈比,约瑟夫就会每天为我做一道特殊的菜。”甚至在有钱的情况下,犯人也可以“交换”,苏士洛夫就是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而被送进了“特科”。这是一种交易,体现的无非是社会意义上的等级制,而对于贵族囚犯来说,正是因为可以花自己的钱,所以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作用就是减轻惩罚:“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要有稍微一点钱,也比没有钱的囚犯所受的痛苦要轻上至少十倍。”
贵族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其实在这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真正的意志或者是逃跑,两名囚犯冒险逃跑,他们的方式就是串通好卫兵科勒,实际上他们的确逃离了这个监狱,连同卫兵,但是最后依然在离监狱七十俄里的村子被抓获,而抓获回监狱,对于他们来说,就从一般囚犯变成重犯,而肉体惩罚是免不了的,五百下和一千五百下,是一种对于好人的宽容惩罚,但是在囚犯被抓获的同时,卫兵也成为了囚犯,甚至更可怜,他被挨打两千下,并接受了审判,而之后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逃跑被抓获,甚至变成重犯,这是现实中的逃往,而正像奥尔洛夫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逃跑的梦想中,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广阔的田野,有茂密的森林,但是梦想的意义就像贵族身份,就像宗教信仰,就像圣诞聚会一样,是空泛的,是虚幻的,就像囚犯的演出一样,为的是让监狱减少一些混乱,为的是更好地维持秩序,“从这些即兴演员身上,不禁会联想到在俄罗斯有多少这样的天赋和精力被扼杀了,有多少处于失去自由的痛苦命运中!”
意志而成为梦想,梦想而成为演出,在这间“死亡之屋”里,不可逃避的绝望和死亡,无可避免的惩罚和酷刑,看上去一切的秩序制造者是那些典狱长、卫兵,他们会像艺术家一样咒骂、侮辱你,“他们会试图把一句恶毒话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得不大令你反感,但其实却是更微妙、更恶毒。”他们会在鞭打和棒打凡人的时候享受一种乐趣,他们像“细腻的烹调专家”热爱执刑的表演艺术,所以在失去自由和享受惩罚之间,罪犯和当局的对立就无可避免,有人杀了少校,有人威胁典狱长,有人串通卫兵,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自我意志,就像M-斯基所说:“他什么都能做,假如他一时兴起,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的。如果他想杀你,他会杀掉你,不会皱眉,也不会忏悔。我常常认为他精神上有些不正常。”
但其实,杀掉那些像是机器的管理人员又有什么用?在这个谁也无法逃脱的地方,对于那些控制着监狱的人,何尝不是和囚犯一样看到同样的围墙,同样的缝隙,同样的天空,以及同样的死亡?何曾不是靠所谓的艺术、乐趣来寻找自己的意志?那个穿着制服的少校曾经是一个风暴之神,但是当他没有了制服,“看起来像一个奴才”,也就是说,他们靠的是这一身制服,才变成一种机器,而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种折磨,他们的自由也无法真正实现,他们的精神也被压抑着。
这是另一种囚犯,所以在这个荒芜辽阔的地方,在这个封闭压抑的世界,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制度的禁锢,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脚镣,一样的监禁”,这是监狱制度的最大荒谬,“我相信,这个著名的蜂窝系统给出的结果似是而非,是欺骗人的。它吸干了人的生命泉源,它削弱了人的灵魂,使灵魂受到惊吓,最后展现了一个悔过自新的典范——一具精神枯槁的木乃伊,成了半个疯子的人。”所以即使在关押了十年之后,获得了所谓的自由,对于曾经的贵族来说,却依然无法逃脱这样的荒谬,而在遭受了十年的压抑之后,却被通知其实是无罪的,因为真正的罪犯已经找到并自承不讳,“在如此可怕的控告之下,他从小就被葬送了一生。事实是太清晰、太不可思议了。”
而重新获得自由,也并非是一种意志的最终实现,在回到故乡之后,他多疑,他疯狂,他断绝了所有关系,“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这个曾经出狱时喊出的话到最后却换来了另一种囚禁生活,“他是在孤独中去世的,甚至不曾被送去给医生诊疗过。甚至现在镇上的人几乎都已遗忘他了。”被别人遗忘,也被自己遗忘,而这种遗忘的悲剧让所有的意志都变成了一种梦想,它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它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它只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习惯,“我们在监狱里意想中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还要更自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