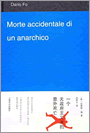 |
编号:X38·2160516·1292 |
| 作者:【意】达里奥·福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4月第一版 | |
| 定价:30.00元亚马逊15.50元 | |
| ISBN:9787532770892 | |
| 页数:139页 |
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一起爆炸案,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为凶手,审讯期间,他突然跳楼身亡。达里奥·福迅速对此事做出反应,在做出精细的调查之后,写成此剧。一名身患演员狂症的“疯子”在警察局偶然接触到无政府主义者“偶然死亡”的材料,他随机应变,乔装成法院的代表复审此案,终于洞悉内情。所谓“意外死亡”,竟是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严刑逼供,将其活活打死后从窗口丢下,造成的畏罪自杀的假象。该剧曾在意大利引起轰动,在两个演出季里,曾连演300场,观众超过三十万人次。达里奥·福说:“演出获取巨大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少,是源自权力机关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伪善谎言,特别是源自他们对国家制度的恣意践踏。我们清醒地知道,我们的铤而走险可能被告发、被指控、被起诉。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是值得的。”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让丑闻发生吧
我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到这里来是为了重新调查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案。要是咱们立刻开始,你们不会不高兴吧?啊,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加拉辛提·安东尼奥·加拉辛提·安东尼奥·菲利普·马可·马利亚·加拉辛提。
——《第二幕》
加拉辛提·安东尼奥·加拉辛提·安东尼奥·菲利普·马可·马利亚·加拉辛提,间隔号在中间,它串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家族,却仿佛连接变成了一种循环,不管是从姓到名,还是从名到姓,其意义是不是属于自我?当胡子和肚子被验明是真的,当法官的任务是重新调查案件,当名字在间隔号中成为唯一,看起来是新的开始,而其实是一种循环,它指向的是原点:依然是和疯子一样的演员,依然被怀疑胡子和肚子是假冒的,依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依然为了调查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而当最后四个警察跌倒在地的时候,当黑暗降临,音乐中断的时候,那剧本的提示上分明写着:闹剧结束。
是真的法官出现才让闹剧结束?是真的调查开始才让循环终结?疯子从窗口掉下去死了,女记者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警察面临着一件案件的调查,那么证据是更明显了,还是依旧隐藏在表象背后?或者说,记者和警察,甚至法官,是会让案件水落石出,还是继续让死亡变成一种悬案?但是在一个有人进来有人退出的舞台之上,不管是疯子还是警察,不管是记者还是法官,他们都变成了演员,真实和表演,模糊了界限,或者让真实在舞台上看起来更真实,是演员的功劳,而把一种表演变成了对于真实的追求,更像是一个悖论,就像疯子和法官原来是同一个演员,却在舞台之上站在不同的情景里,却要面对“众人”的广大观众,那么真实就是虚构,虚构也是真实,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表演得越真实,就越像一个演员,就越能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核心,就越能在其中做出判决。
表演,其实是被表演,被动语态意味着一个有观众的剧场,一个有证人的案件,一个有更正的剧情,一个充满着怀疑论的故事,而当“疯子”成为其中一个表演者的时候,他在被表演的舞台上就不再是疯子,他是,精神病医生,曾任职,帕多瓦大学兼职教授,扮演过,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也曾把自己当成,警察局科技处上尉,最后甚至成为,穿便服的大主教……在每一个角色之前,都有一个逗号,就如疯子自己所说:“逗号是行文的关键!”所以应当把动词和职务之间留下一个“充满讥意味的鬼脸”,一种“发出嘲讽的嘟哝声”的间隔,实际上,就是把演员的身份隔离开来,就像那个间隔号,被放置在名字中间,意味着一种从真实到虚构,又从虚构到真实的循环。
“你曾经两次冒充外科医生,一次自称狙击兵军团的上尉……三次伪装大主教……一次自称造船工程师……这是第十二次……”数字的排列就是一种循环,一次、两次,三次、十二次,其实是从开始而走向一个没有穷尽的未来,而这个循环只有当疯子变成演员的时候,才变成可能,而这种循环在警长看来是乔装打扮的欺骗,在疯子自己看来却是一种真实的毛病:“我喜欢不断地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不过,我追求的是真实可信的戏剧,因此我的剧团里的演员,必须全是实实在在的人,不会装腔作势地演戏……”把自己当成一个演员,是为了追求真实可信的戏剧效果,所以这是主动的改变,而当这种主动改变被警察定义为欺骗的时候,就是被表演。
但是在疯子看来,追求真实可信的戏剧,除了像一个演员之外,还在现实中具有巨大的合理性,正是因为成为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才可以在十六家精神病医院里住过,也才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从事精神病医学十六年的精神病科医生,才可以从容接受病人两万里拉的钱,所以疯子的逻辑是基于一种表演,在自己的舞台上走向和现实不相同的真实场景,所以对于疯子来说,他对于表演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法官而不是律师,律师意味着防卫,而法官则意味着审判,“我喜欢审判……判决……镇压……迫害!”审判的意义就是“掌握着随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毁灭或者拯救某个人的权力”,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至高意义,超越凡人,超越警察,也超越律师,超越犯人,当然也超越疯子。
这是一种理想,所以要实现这个理想就要从“疯子”这个固定角色中走出来,而其实在疯子这种表演经历中,他要突破的是三点,一是自己的表演才能,这涉及到自我的知识、学问、经历和经验,对于疯子来说,这不成什么问题,二是必须让自己面前的人信服,不管是警察还是记者,都要不怀疑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当然在这二者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潜性的规则,那就是观众的认可,也就是说,演出是否成功,还必须接受观众的评判,当评判像审判一样,却意味着在所谓的法官之上还有另一个上帝,另一个握有大权的上帝,另一个“掌握着随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毁灭或者拯救某个人的权力“的终极审判者。
表演开始了。二十年时间钻研法律的疯子在警察局趁警长不再的时候,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最高法院的法官要从罗马前来调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案件,这对于疯子来说,当然是现实自己要成为一名法官理想的最高时机,他可以成为“钦差大臣”,可以通过公众施加压力,可以对警察发号施令,“这倒是一个机会,向我和全世界表明,我具有渊博的学识,完全有能力打进那些号称永远正确无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官的行列……”于是他穿上了贝托佐警长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冒充来自罗马的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马可·马利亚·马里皮埃罗教授,在警察局长办公室进行了调查。
|
|
| 达里奥·福(1926 – 2016):死亡变成括号里的事件 |
这是他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而最大的困难是过警察这一关,贝托佐警长认识他,把他称作是疯子,因为不管是档案还是本人的面孔,他们都熟稔于心,即使疯子没有被判过刑的记录,是清清白白的,但是贝托佐警长还是发誓,要玷污记录,要把他的犯罪记录留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警察也是一个演员,一个表演者,一个制造谎言的人,而他们的欺骗不是在表演意义上,而完全在现实中。当疯子成为法官开始调查案子的时候,才发现其中充满了谎言。
一名铁路扳道工,被怀疑制造了火车站的导致16名无辜市民死亡的爆炸案,然后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名义被逮捕,最后在审讯中跳窗而死。为什么会成为爆炸嫌疑犯?警察局长的解释是,“我们掌握了一些可疑的线索,这米兰的无政府主义者、扳道工是唯一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很容易推断,他是……”什么线索?为什么用线索就可以确定他是唯一的嫌疑犯?其实根本没有线索,警察完全是推理,甚至是采用经常做出的欺骗手段,所以“法官”对于这个疑点的质问是: “如果火车站的炸弹是铁路工人放的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作出推断,罗马司法部大楼的炸弹,是一位法官放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前的炸弹,是警卫部队的军官放的;农业银行的炸弹,是一位银行家,或者一位农业主——由您选择——放的。”
除此之外,在查看对扳道工审讯中案卷,疯子也发现了从“起初他微笑,后来却突然变得恐惧”,发现审讯到自杀有四个小时的时间,疑点重重,而所有的疑点在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法官”面前,一一被识破,疯子把警察的这种行为叫做“做了一件蠢事”:从一开始就是警察随心所欲拘捕了一名自由公民,然后滥用权力,对他的拘留超过了法定的时限,后来又威胁说掌握了他用炸弹制造铁路爆炸案的证据,神经受到刺激之后,警察又故意制造出他的精神除了毛病的假象,然后说要将他解雇,最后,又打击他说在罗马的同志已经交代了案件,承认自己是米兰爆炸案的凶手。在法官看来,就是在警察滥用权力、谎言欺骗、制造假象和不断打击中,他从一名自由公民变成了嫌疑犯,再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最后在彻底的绝望中,喊出了一句“无政府主义完蛋了”,便跳下了楼。
法官理清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为掌握权力的人,实际上在权力体系里自然变成了事实,所以不管是警察局长还是穿运动夹克的警察,都在这出自己导演的戏剧里变成了“罪犯”,他们也承认自己杜撰了作案的情节,编造了爆炸的动机。警察无疑成了司法制度中丑闻的制造者和实施者,但是这被人耻笑的虚构,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狗日的世界”的愤怒就是在谴责“这狗日的政府”,因为如果不是有人鼓动他们,不是当局制造紧张气氛,如果不是因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那么这样的丑闻也不会发生,他们是实施者,也是受害者,更是牺牲者。如果这个案子按照事实的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真的变成罪犯。
但是疯子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力,当然他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权力让他们“赦免”,实际上,当疯子变成法官,他其实也已经成为制度和权力体系的一员,甚至成为了谎言的另一种制造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开始帮助警察洗清自己,开始了所谓的“反调查”,也就是说,要制造新的谎言,把事实推翻。在法官的提议下,原本不在场的警察局长必须在场,而且要以父爱的姿态,把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还要穿夹克的警察轻轻摸他的脸,对他说:“打起精神来……别这样垂头丧气……你瞧着吧,无政府主义不会死亡的!”最后,还要一起唱起一首歌。在法官看来,事实上的审讯是因为”缺少仁慈,缺少人情味“。
当对于自由公民的审判变成被审判,当对于警察的调查变成反调查,那个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当然也成了“被死亡”。在这被制造、被虚构的现实里,那晚的寒冷没有了,那晚的跳楼变成了意外事故,那晚的审讯变拥有了“开玩笑的方式”,充满了人文关怀,充满了人情味,可是被制造的事实总是会出现破绽,那晚其实是大降温,可是警察都说像春天,那晚警察抓住了一只鞋想要挽救,却发现掉在地上的死者脚上还有两只鞋。“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身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这是疯子的推理,所以那第三只鞋的解释就变成了:“毫无疑问,他穿的鞋当中有一只太大了,而当时他手头又没有鞋垫,于是,他先穿了一只瘦小的鞋,然后再套上那只肥大的鞋。”
一切变得可笑,而当女记者开始采访警察局长的时候,这种可笑变成了讽刺,“他马上瘫倒了,发出临死前的喘息,失去了呼吸的能力。于是,他们打电话呼叫急救车,与此同时又要想法子让他活过来,便打开窗子,把无政府主义者抬到窗台上,身躯的一部分伸到窗子外面,这样,午夜新鲜的空气能够刺激他,让他苏醒过来……”这是疯子帮助警察进行解释,而这时候他不是法官,在记者面前他是警察局科技处马卡托尼奥·班齐·皮齐尼上尉,也就是说,在死者的技术层面上,他是绝对的专家。所以在所谓的皮齐尼上尉的技术分析中,女记者得出的结论是:意外死亡。
意外死亡,却并不能掩盖越来越多的犯罪现实,疯子告诉记者,无政府主义者是制造了各种爆炸,因为“巴枯宁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所以记者的疑问变成了:“在迄今发生了一百七十三起爆炸案,平均每个月十二起,每三天一起;在这一百七十三起凶案中(念手中的一份材料),有一百零二起经查明是法西斯分子策划的,而在余下的七十一起凶案中,一多半有着可靠的犯罪线索,也同样是由法西斯分子或者相似的组织策划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是被法西斯分子利用,诱导他们去“实施一项其犯罪性质不容置疑的凶案”。而在这个时候,疯子又变成了政府的代言人:
百姓要求真正的公正吗?我们则采取行动,让他们满足于较少的非正义;工人们嚷嚷,要结束野蛮剥削的耻辱,我们则努力让这种削少一点儿野蛮的气息,让工人们不再感到耻辱,但依旧遭受剥削;工人们要求工厂里不再死人,我们则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并给死难者家属增加一点抚恤金。人们要求消灭阶级……我们则想办法消除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者说不让这种差异过于扎眼!人们需要革命……而我们则要去搞改良……五花八门的改良……把他们淹没在改良之中。或者说,我用种种改良的许诺去堵他们的嘴,因为连改良我们也永远不会去做的!
从疯子变成法官,从法官变成技术人员,从技术人员变成政府代言人,疯子就在这不同的角色间转换,而面对“那秃鹫一样贪婪成性的记者”的咄咄逼人,疯子又变成了大主教,因为他要拯救警察,而赶来知道疯子身份的贝托佐警长却被警察局长和穿夹克的警察封住了嘴。真相被封住了嘴,而且还被打了镇静剂,是让真相永远藏在表演之外,是让舞台全部交给演员,而实际上,这出充满舞台情景的闹剧,完全是在背离真相,而疯子,除了帮助警察“反调查”,除了认定嫌疑人“被自杀”,他自己也被推向了不可控制的“被表演”情景之下。
玻璃球的眼珠掉了,木腿和假手掉了,甚至还掉下一只女人的手,身体也是虚假的,也是伪造的,而坐在舞台之下的那些观众在被疯子认为是“真正的奸细”的时候,也见证了一出闹剧的真正落幕。“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我要人们都接受正义与真理,我将竭尽全力让那些丑闻用最轰动的方式爆发出来……”疯子用大主教的身份引用了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话,仿佛他也已经变成了俯视众生的上帝,而面前这个国家在他眼里自然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国度:“……你们不必害怕,从腐败中将建立权威。让丑闻发生吧,一个更持久的国家政权将由此诞生!”
丑闻的确在发生,警察滥用权力,记者恶毒攻击,法官制造假象,而疯子也满足了自己成为演员的欲望,诈骗者、冒名顶替者、演员狂躁症以及伪造者之外,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当疯子的谎言被戳穿,并不意味着真相的到达,那个看上去假的爆炸装置却最后在灯光灭掉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疯子“像一只疯狂的鲸鱼一样冲了下去”,从窗口,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像是朝着窗口扑下去,像是不小心跌下去,像是意外死亡,却其实,却是被权力、被谎言推了出去。
审判变成被审判,调查变成被调查,自杀变成被自杀,被动语态的舞台上,“我们既没有过错,也没有任何责任!”当穿运动夹克的警察这样说的时候,底下的观众回答:“没有任何责任!”一幕幕丑闻,一出出闹剧,真正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他们看见了一切,他们见证了现场,他们又做出了评判,而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疯子,都是骗子,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自杀的人。而当那个胡子男走上舞台,当法官出现,当胡子和肚子都变是真实,他对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调查,无非就是另一个循环的开始,因为,“没错儿,他就是个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