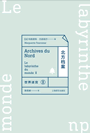 |
编号:C38·2170722·1400 |
|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 |
| ISBN:9787532773213 | |
| 页数:290页 |
关于父系的家世,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直接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然后缩小视野,集中在人物身上,从19世纪到第二帝国,从体面的夫妇到遭放逐的父亲,最后是一个女孩。没有子嗣,改变姓氏,她最终选择了与家族决裂的道路——家族的命运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历史纵然拥有作为佐证和借鉴的力量,但人类总是重复错误,悲剧性似乎不可阻止。这种被自己成为“相反”的回忆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只是“不再在一个家族历史硬邦邦的绳索上停留”,也正是将家族放在漫长的历史中,才会有一种接近现实的感觉,“这个家族,或者说这些家族,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父系家世,我将试着超脱地去处理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对于无限的时间而言,他们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
《北方档案》:让我们跨过尘埃
他专门请人为自己在左胳膊上刺上六个字母,那大概是在与贝尔特结婚之前的事,那六个字母是,ΑΝΑГКН,意为“宿命”。
——《宿命》
刺下的六个希腊字母,会有血流出来?或者会有灼灼的伤痛感?关于肉体的某种铭记会触及心里的某个角落?“宿命”是一种关于命运的延续:米歇尔已经像父亲或者祖父一样,在流亡生活里新招自我的意义,在冒险中开启生命的存在方式?“宿命”是对于家族故事的一次预言:妻子贝尔特三十八岁死在俄罗斯街的套房里,三十三岁的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也在那里死去,贝尔特之死使米歇尔在一年后娶了费尔南德,四年之后,玛格丽特因为灾难而降生?
不管是流血还是疼痛,为什么又是左边?左边是右边的左边,当一种“宿命”被刻写,米歇尔或者还在未结痂的时候凝望过着六个字母,那仿佛是一种必须被时时提及的符号,即使用衣服遮掩着,也无法从肉体里清除。选择左胳膊,一定是对于宿命的最好诠释,当和莫德的七年以肉体的方式开始的时候,逃脱世俗甚至秩序的生活,一定是他难以释怀的记忆:当他在那个温暖但灰蒙蒙的下午,用地上的那根绳子将自己的左手绑在休闲椅子的背上,然后随着一声响,中指终于耷拉下来,“只有一点点皮肉与第一节指骨连着,鲜血穿过金属椅子的孔眼滴下来,像从漏勺里漏出来似的。”
这是残忍的方式?比六个字的“宿命”流了更多的血,有了更多的痛感,但是为什么对于米歇尔来说,这截下的断指翻到成了滑稽的“纪念物”?医生把它用手帕包起来,他却把它扔到了小女佣的脖颈里,在他看来有趣,小女佣却吓晕了过去,只是最后的痛感和流血还是让他在坐上农用马车的时候晕了过去。这像是一个游戏,起先是毫不在乎,甚至带有恶趣,但是最后却成为了一种无法愈合的伤痕,在肉体世界里变成了永远的符号。
左胳膊的字母,左手指的伤痕,自戕或者自残,对于米歇尔来说,是个体意义的“题写”,而实际上,对于莫德抱怨的反击,费尔南德结婚之前的忽略,肉体之于女人,似乎永远是一个悖论式的关系,即使在手指留下永远伤疤的时候,他后来还是认为:“如果说为一个女人去自杀是美好的话,那么为她而牺牲两个指节却是很傻的。”所以在七年没有结束的新生活里,两个人又像是曾经承诺时一样甜甜蜜蜜,“他俩常去伦敦,她逛商店,他则去买书、上剧院,而且对欧文和埃伦·特里十分着迷。”傻傻的自杀,其实只是伤了一个指节,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冒险从来不会去牺牲整体,从来不会断命,而一种宿命被注解,在走进和贝尔特婚姻世界之前,即是一种续承,也是一种突围。
米歇尔之前是米歇尔-夏尔,米歇尔-夏尔之前是米歇尔-多纳西安,米歇尔-多纳西安之前是米歇尔-达尼埃尔——这是玛格丽特父辈有关的族谱,当在《虔诚的回忆》追溯了和母亲费尔南德相关的历史之后,《北方档案》就必然是以父亲为轴线展开“世界迷宫”,只不过和对于母辈历史追溯的方式不同,在这里直接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回忆:“在这本书中,我想采用相反的办法,直接地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最后,逐渐缩小视野(但仍是精确的),更多地集中于人物身上,直写到十九世纪的里尔,直写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大资产者和一个坚定的女资产者——那对体面而不太和睦的夫妇,最后再写到我的那位老遭放逐的父亲,再写到一位小姑娘,她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在法属佛兰德的一处丘陵学习生活。”从蒙昧时代到梳理出谱系网络,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似乎更接近家族的传承,而实际上,玛格丽特的用意似乎就是于在那个被刺在左胳膊上、流过血、存在过灼灼伤痛的六个字母:宿命。
“这些已不复存在的人,这些尘埃,让我们跨过他们,直达尚与他们有关的那个时代吧。”跨过尘埃,是面向现在以及未来,当未来成为未知,只有尘埃的世界才是已知的,即使被覆盖在那里,只要轻轻挥去那些尘土,世界也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降落而沉淀,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再无被改写的可能。所以,从过去向现在,这样一种时间轴线和方向,就明摆着那一个宿命观,而对于宿命之存在,玛格丽特其实并非是安于宿命,作为一种活着的“我”的审视视角,在时间的脉络中希望看到的是尘埃之下的那些真实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被抽空了细节的历史整体,“我并不把历史当成一种荣耀,对今天已是法国北方地区的几户默默无闻的家族的拜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曲解的力量和利益几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一代人活着,一代人死去,一代人出生,一代人成长,“太阳在烘烤着那薄薄的活泛的地壳,让蓓蕾绽开,让腐尸发酵,在从土壤中汲取水汽,然后再把它蒸发掉。”这也是蒙昧时代的转承关系,如果只是描述历史整体,关于先人无非是一串数字:“在父系中,唯一使我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四位曾祖父母,共和二年前后的十六位先辈,路易十四年轻时期的五百一十二位先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四千九百六十位祖先,一百万死于圣路易前后的祖先。”数字其实只是一种备忘,而家族谱系对于玛格丽特来说,从来不是一种“为人的虚荣心服务的科学”,因为那必将导致羞辱:“因为我们会感到在这么多人之中自己是极其渺小的,然后导致的则是眩晕。”
甚至在宏大叙事中,个体呈现的是一种脱离状态,从族谱到家谱,实际上是一种返回尘埃并试图跨过去的努力,而在这跨越过程中,那个左胳膊上的六个希腊字母便若隐若现地出现了。宿命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流亡”:高祖父米歇尔-达尼埃尔曾经度过七年的流亡生活,最后流亡归来的夫妇只带回来他们的消息阿尔-奥古斯丹,而米歇尔人-夏尔呢?或者并不能叫流亡,在他的生命中凸显的那个词叫毛冒险,叫旅行——那一次,他和表兄弟亨利便坐上了轻便四轮马车出发了,夏尔-奥古斯坦给他们的一张一万法郎的汇票,成为他们旅行的所有开支来源,而这样的安排,并非是浪漫的,实际上就是一次冒险,“据说罗马乡村和西西里盗匪猖獗,无处不在的巫婆妖女会劫掠年轻男子,蒙骗他们,窃取他们的金银,在他们的血液中注入一种致命的毒药。”
实际上为什么冒险也是一个宿命的开始,当默东的那列火车发生车祸,一节车厢的四十八个乘客,却只有米歇尔-夏尔幸存了下来,这是生命最幸运的写照,当死亡就在眼前,甚至伸手可及的时候,活下来甚至变成了一种伟大,而这种伟大之出现更加凸显了命运之无常,暂时将宿命掩盖起来,享受着冒险带来的刺激和快感,这或许就是米歇尔-夏尔在生命转折中被刻上去的符码,“我们大家都被粘在其上的蜘蛛网的丝非常细:那个五月的星期日,米歇尔—夏尔差点送了命,或者说是侥幸生还,让他又活了四十四年。与此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包括我在内的后代,拼命地在撞那并不存在的大运。”
旅行几乎改变了米歇尔-夏尔的生命意义,他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面对着火山那白雪皑皑的陡坡和疲惫带来的死亡威胁,承受了双手双脚冻僵的考验——几乎已经走向了死亡,于是,和凡尔赛的那次车祸带来的痛楚经历一起,这种向死而活的状态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凡尔赛的冒险经历宛如一个分娩的宗教仪式,米歇尔—夏尔头先来到人世间;埃特纳火山的冒险则是死亡和再生的宗教仪式。这两次几乎是神圣的意外事件对一位伟人生平的开始是会有好处的。”在仪式之后,一切似乎都被归结为劫后余生的体验,所以他会厌恶那些所谓的舞会,所以他会反驳征服的特派员,所以,他会接连三次被解职,也所以,他会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利用放假之机带他到国外去做短暂旅行,”必须让孩子学会了解世界。”这是他对于自我的一次总结,也是对于下一代的期望。
而对于米歇尔来说,那次马车撞击事件似乎也像父辈经历的凡尔赛车祸一样,让生命充满了无常,米歇尔-夏尔的女儿加布里埃尔死于马车撞击,而几年之后,另一个女儿玛丽在她三十三岁时像她姐姐一样死于非命。这或者是留在父辈米歇尔-夏尔身上的宿命论,而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出走是对于陈规的厌恶,在一种渴望自由的欲望里,十五岁的他用一两个路易就制定了未来的计划:“去比利时(那是越境,这就够迷人的了),一直到安特卫普,在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邮船或货轮上当个见习水手、洗碗工或舱房服务员什么的,然后再去中国、南非或澳大利亚。”辗转而奔波,是一种逃避,却在接近自由的个人主义中开始了另一种带着极端的生活。
这或许是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凸显在和女人的那种关系上,米歇尔-夏尔在过了混乱的假期之后,开始整理旅行笔记,对于他来说,是归于秩序的开始,“以用一些古代大理石碎块做镇尺为乐的米歇尔—夏尔也许是个现实主义者。”当诺埃米小姐和马雷街二十六号成为他冒险之后的归宿,就是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开始,“这不是一桩伟大的婚姻,甚至也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这是一桩很好的婚姻。”“很好的婚姻”是关于名誉和地位,关乎财产和收入,但似乎并不关乎爱情,诺埃米被称为“平庸的深渊”,是“把自己的丈夫不是当成奴仆就是当作利害相关的人”的那种妻子,玛格丽特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岁,“身材臃肿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如同瓦尔特·德拉·梅尔一部小说中的那个在空荡荡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难忘的锡东阿姨,在看着她的孩子们的眼里成了死神或恶魔的化身。”在玛格丽特看来,她既不爱上帝,也不爱自己,甚至也不爱儿子米歇尔——当丈夫将他带去旅行的时候,她却将“每一分钱的花销都事先在家里计算好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刻薄、平庸、现实的女人为米歇尔提供了一种反证,所以这种逆向的生活方式在米歇尔身上变成了“反宿命”,而反宿命和宿命无非是一对双胞胎,其中隐含着的矛盾完全是一回事。当高中时期年轻的神甫将手悄悄放在学生的光腿上并往上挪的时候,有关欲念的回忆便在米歇尔心里挥之不去——甚至,这也变成了一种反宗教的实践。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在军中被解职,秩序对于米歇尔来说,已经荡然无存,他反而在双腿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秩序。
七年和莫德成为情人,从那张带印度床幔的大床上颠鸾倒凤开始,对于米歇尔来说,完全是在秩序和道德之外,而在离开家庭离开法国的自由旅行中,他完全释放了自己,成为一个流亡者,就像高祖一样——也是七年。“在这个不承认自己走错了道的年轻的流亡者心中,在安特卫普船坞边闲逛的少年情怀又再现出一点来了:对于这种桅杆和烟囱的交织,那些因海水侵蚀而生锈和结垢的船体,以及那些各个种族、各种肤色、有的头裹缠巾光着脚(肯定他们中有一个是向莫德的店铺提供黑色果酱的),穿行于红皮肤、黄皮肤或灰皮肤的土著人中的那些人的熙来攘往,米歇尔是百看不厌。”横渡大西洋,从美国回来,即使被医生“判决”存在巨大的生命隐患,米歇尔依然无法停止欲望的放纵。但是在七年的自由生活中,和一个有妇之夫颠鸾倒凤的生活到底会又怎样的结果?那一根断掉的手指似乎在书写着一种代价,“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好好的,在这间小屋的破炉灶上做饭,把她的纤纤玉手都弄糙了;米歇尔像所有法国人一样不光明正大,他甚至都不会为她牺牲一个指头。”仅仅是因为这一个抱怨,米歇尔便以自戕的方式回归到“宿命”的世界。而当和贝尔特结婚之后呢,从此开启的十三年是不是就回到了秩序?
无论是逃亡英国,还是和狂热的加莱成为朋友,无论是远离家人,还是泡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边的小赌场里,米歇尔对于人生的注解其实已经变成了荒唐,“他曾经经历过的、思考过的、承受过的或者喜爱过的,全都深埋在心底,那十三年是一个几乎全无配角的舞台,而且我们也不了解它的后台。”这或许是作为女儿的玛格丽特对于父亲的一种宽容和谅解,但实际上,米歇尔这种逃避式的生活最终还是付出了某种代价,贝尔特死亡之后,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死在同一套公寓里,他们的死笼罩在混乱之中,神甫竟然以加布里埃尔是离婚的女人,而以蛮狠的方式予以拒绝。秩序其实荡然无存,对于米歇尔来说也是如此,贝尔特死后一年娶了费尔南德,费尔南德又死于产褥热,对于结过三次婚有着很多情妇的米歇尔来说,似乎生命的秩序永远在无序中展开的。神甫那只从双腿间往上挪的手,父亲鼓励他去见识世界的冒险,都是一种宿命式的开始,而接下去的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未来为他保留着他最伟大的爱情,那是—个特别值得他爱的温馨女子,是他唯一为她写下几首保存下来的漂亮诗句的女子。他还有一个奇怪的恋情,也许并没有任何性欲的因素,那是他对一个怪僻的女病人的爱:她帮助德·克先生把他剩下的财富弄得个精光。”
结婚之前就刻在手臂上,结婚之后的漫长时间都没有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走出来,米歇尔提供的样本其实是关于历史中个体的存在方式,混乱也罢,自由也好,欲望也罢,贪婪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好,其实在只有一次的生命之途中,历史也只能有限地发生一次,而对于后代来说,当那种秩序已经存在,它必然是带有宿命的成分,从尘埃中跨过去,或者看见的是愚蠢、暴力和人的贪婪,也或者在疯狂之中能够找到足以冷静的力量:“自从人被疯狂攫住,自认为无比强大时起,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同另一种物种一样也只是一个物种的话,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和罪恶就会变成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