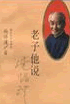|
编号:B52·2000826·0528 |
| 作者:(台)南怀瑾 | |
|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 | |
| 页数:173页 |
禅宗的博大就是最大可能地挖掘人的智慧潜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传播理念使禅宗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南怀瑾的意义就是把“不立文字’的学说通过禅宗发展中的故事给予它言说的权利,给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禅学以最民间的阐述。
“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问:‘对朕者谁?’师曰:‘不识’。”
——《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
一个“不识”,展现了达摩祖师的机锋,一个“不识”,又把自己隐藏在对话之外,避开谈及“圣谛第一义”,避开与帝王对话的“我”,似乎禅宗的义理在此已经显露出来,但是当发展到后来,禅师们以“念佛是谁”的回答形成另一种问题,是对于问答式传统教法的革新,还是对于“我”的重新认识?
当达摩大师从印度来到东土传授禅宗的心法,当面对“对朕者谁?”而选择回答“不识”,是因为站在达摩面前的是以帝王之尊舍身佛寺为奴的梁武帝,一个帝王不去做帝王应该做的事情,而专注于传播佛法,是不是一种失道?所以很明显达摩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梁武帝的提问,恰恰是一种讽刺——至少在南怀瑾看来如此,他在“新语云”这一对禅话故事做出评析的案语中说,梁武帝作为政治上的统治人物,却做着满足自己作为传教师与学着的瘾,多少是“违背大政治家的法则”,没有做到无偏党而“允执厥中”,也注定了他要失败的后果,而这种失败在南怀瑾看来,并非是梁武帝一个人的失败,甚至是中国佛教出现灾难的源头。
达摩来中国之前,般若多罗曾经告诉他三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是说,到中国传道之后将来悟道之士会多不胜数,在般若多罗去世后六十多年,将有一个灾难,犹如“水中文布”,所以要好自为之,不要在南方久耽,“因为南方的领导者,只是喜欢世俗有所为而为的佛教功德,对于佛法的真谛,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水中文布”指的就是梁武帝,因为他只是为了满足佛教的功德,所以会有灾难;而对于中国佛教以后的发展,般若多罗说再过一百五十年会有小灾难;同时支持另一个预言则是“心中虽吉外头凶,川下僧房名不中。如遇毒龙生武子,忽逢小鼠寂无穷。”——在南怀瑾看来,这个预言指的就是北周武帝废佛教废僧尼的灾难,这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又名的“三武之难”之一,而导致这一灾难的便是中国佛教僧众的“不知检点”。
般若罗多在达摩那里讲出了三个预言,所以达摩来到中国之后,面对梁武帝的发问,以“廓然无圣”否定了“圣谛第一义”,以“不识”避开了“对朕者谁”——当达摩成为“不识”的自己,禅宗似乎开始认识“我”的真正意义,而这个“我”从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是对预言的警示,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实证修行之路,导向中国佛教的另一条路。但其实,在南怀瑾看来,不管是警示还是修行,都表现了达摩祖师自我牺牲的精神,也以行动主义回答了“圣谛第一义”这个终极问题:“廓然无圣”指的是“空廓无相并无圣道的境界”,也就是直接否定了梁武帝舍身佛寺为奴,充当传教师讲解道书的行为,而达摩在中国开启禅宗历史,完全是遵循着如理如实的禅宗法门,四卷《楞伽经》的义理便是证明。
达摩开创的“达摩禅”,其要义便是“二入”和“四行”,“二入”指的是“理入”与“行入”二门,“四行”指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所以达摩的修行要义是以“行”为主旨,他确立的自我省察和自我修正的实证经验,成为中国禅宗精义所在,而且也是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融会为一的精神之所系。但是后世学禅的人,只看祖师的语录,只读禅宗的史书,只看禅宗的公案参机锋、转语才是禅宗的宗旨,实在是谬误,在南怀瑾看来,如果禅宗只注重禅定的功夫,欠缺“心行”和“行为”上的功德,那只能偏向于小乘,不能达到觉行圆满的佛国境界;另一方面,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有异处,但更有相同点,最重要的便是遵守着达摩初穿禅宗的“四行”,“如果确能依此而修心行,则太小乘佛学所说的戒、定、慧学,统在其中矣。”
而从达摩在中国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着这一修行要义:他到少林寺“面壁而坐”,并非是一种修道的刻板功夫,而是在寂寞无言里等待后来者,当神光大师到来并成为二祖,达摩的等待终于有了传人,“终日默然,面壁而坐”的沉寂被打破,不管是安心法门,还是断臂求道的公案,都是达摩借此接引神光悟入心地境界的做法——神光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我为汝安心竟”,除了一种启发性的教授法,更是“外息诸缘”等四句教诫性的方法,“这都是宗不离教,教不离宗的如来禅,也就是达摩大师初来中国所传的如理如实的禅宗法门,地道笃实,绝不虚晃花枪。”另一方面,达摩最后坦然面对个体灾难自愿饮毒,也体现了他实践“四行”之法而“心安理得”,在南怀瑾看来,达摩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真理而选择死亡的苏格拉底,困于陈蔡厄于鲁卫而传道的孔子一样,都是在艰危困顿中选择了大道,甚至二组神光临终受害,也同样是一种伟大的实践。
无疑违背大政治家法则的梁武帝被南怀瑾搁置在这种伟大实践的对立面,所以当达摩“廓然无圣”否定了“圣谛第一义”,实际上也是对梁武帝行为的某种漠然,因为梁武帝之行为只是为了所谓的功德,而失去了其作为帝王应有的使命。这一种对比其实显示了南怀瑾对中国禅宗的一种关照:实践达摩的“二入”“四行”,本就是佛学在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本就是禅宗修行的要义,本就是和中国文化融合为一的精神所系。南怀瑾举了一个和梁武帝完全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傅大士,他认为傅大士身为平民,为了赈灭,为了供养众生,舍卖了妻子,从而消灾集福,灭除罪垢,这一种精神就是不为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而梁武帝却只是为了学佛求福——一个是为众生着想,一个是为自我积德,如此便也是大乘和小乘的区别,所以南怀瑾认为傅大士可称为“南朝的奇人”,是中国维摩禅的大师,“傅大士悟到前缘之后,便发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所以他说出‘炉撬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的话。这话真如狮子吼,是学禅学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闲视之。”
傅大士说出的那句“学禅学佛的精要所在”的话,在南怀瑾看来,代表着中国本土大乘禅学的新面目:他不现出家相,特立独行维摩大士的路线,弘扬释迦如来的教化;而且“现身说法”,以道冠僧服儒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以“儒行为基,道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体现的就是以身设教的行为主义,南怀瑾认为,他“亲自写出—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而同时,南怀瑾认为达摩在来印度前说“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其实是指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修证禅定就具有“大乘”风范,“佛学的主旨,重在修证。而修证的方法,都以禅定为其中心。”这里并无是不是禅宗的定义问题,而本土大乘禅的代表人物,除了傅大士之外,还有宝志和尚、慧文法师等,他们的言行对于隋唐以后新兴的禅宗和天台、华严宗等都有莫大的影响,尤其是宝志禅师提出的十四相“不二法门”,影响了隋唐以后佛学和学术思想,南怀瑾甚至认为,唐代以后的禅宗,与其说是达摩禅的单一发展,不如说混合了达摩、志公、傅大士的禅宗思想。
禅宗修行要“二入”“四行”,“行”的要义就是对中国深层社会问题的关切,甚至体现以身设教的行为主义,而回到祖师禅,从达摩到神光,再到三祖、四祖、五祖,也都体现着中国大乘人的要义:三祖僧璨的《信心铭》,与志公大士所作的《大乘赞》、傅大士所作的《心王铭》等汇流,奠定了隋唐以后中国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正信资料,尤其是《信心铭》开场就提出了“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的警语,就是指出了世人不能自信其“心”的弊病,最后他又归结为“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为结论,所以南怀瑾认为,“禅宗自此开始,才完全呈显出中国文化的光芒与精神,学者不可不察也。”四祖则“纯以达摩禅的一脉为宗旨”,以“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十年”的笃实禅修,为行持的宗风,而且他为后世学者留下不慕虚荣,轻生死,重去就的清风亮节,成为世出世间的典范;五祖的禅宗法要体现在他的弟子所记述的《最上乘论》,它与达摩大师的《血脉论》和《破相论》,以及三祖僧璨大师的《信心铭》一脉相承;即使禅宗南北分立时,牛头山法融禅师的一系早就开创了北宗的风格,他们以注重笃实的行持与禅定相契为根本,既平易,又奇特,有机锋,有实语;南宗禅则在六祖慧能之后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之后的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一反历来死困在经论义理中的传统,渐启中国佛法的光芒。”
南怀瑾认为,唐初中国佛学已经茁壮成长,律宗有南山道宣律师为其翘楚,天台宗在初唐到中唐时开始盛行,华严宗的贤首和尚与清凉国师先后相继执持牛耳,密宗: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跃登宝座,净土宗已普入民间,而禅宗也已普遍流传……考察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发展,南怀瑾认为,“自汉末、魏、晋、南北朝到盛唐之间四五百年来的佛教,无论哪个宗派,只要注重实证的佛法,唯一的法门,都是以‘制心一处’、‘心缘一念’的禅观为主;而禅宗到了马祖一系,已经将极其高明深奥的佛法妙理,显现在乎实奇的日常应用之间,开放了中国文化特殊光芒的异彩,这绝不是对“二入”和“四行”的否定,绝不是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甚至在他看来,“所谓中国文化儒、佛、道三家的密意,统统都在马祖的言行和举止中表达无遗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南怀瑾并未展开论述,但是他用一段公案总结了“契合于无相三昧的真谛”的实践意义。
有一位大德问怀让大师说:“如果把铜镜熔铸成像以后,镜的原来光明到哪里去了?”大师回答说:“譬如你作童子时候的相貌,现在到哪里去了?”问:“那么,何以铸成了人像以后,不如以前那,可照明了呢?”大师答:“虽然不会照明,但一点也谩他不得!”铜镜铸像少了照明的功用,这只是“用”的改变,而铜镜之“体”依然不变,这“一点也谩他不得”的体便是“制心一处”、“心缘一念”的禅观,便是“二入”和“四行”的法门,便是观照现实的实践,在南怀瑾看来,或者也是“圣谛第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