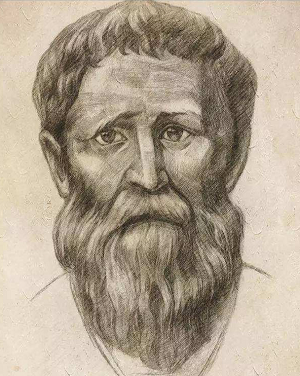|
编号:E32·2170319·1371 |
| 作者:【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
| 定价:39.00元亚马逊22.60元 |
| ISBN:9787100115629 |
| 页数:350页 |
“我不过是肉欲的奴隶,我戴着我的枷锁,还感到死亡的甜蜜,我害怕脱身,拒绝别人的忠告,好像解救我的手碰痛了我的创伤。”作为“世界三大忏悔录”之一,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阐述了他的原罪思想,也以他人的苦闷为自己的苦闷,用无比的真挚尝试解决其苦闷。一个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个被罗马天主教系统被封为圣人和圣师的思想家,看待“原罪”而实施忏悔更主要是从承认、认罪之外,发现另一种救赎,他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并在重大神学和哲学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影响深远的《忏悔录》也使得“忏悔录”这个词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本书共十三卷。
《忏悔录》: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
因此,我要忏悔我对自身所知的一切,也要忏悔我所不知的种种,因为对我自身而言,我所知的,是由于你的照耀,所不知的,则我的黑暗在你面前尚未转为中午,仍是无从明彻。
——《卷十》
因罪而忏悔,因忏悔而皈依主,而皈依主之后是为了在主的照耀中探索自身,这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从沾满罪恶的自身到被主照耀而明彻的自身,作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奥古斯丁其实建立了关于个体获得救赎的曲折路径:沾满罪恶的自身是一个过去的存在,被主照耀而成为他的一部分是现在的存在,忏悔就是为了从过去抵达现在,从罪恶抵达明彻,“这是我的忏悔的效果,我不忏悔我的过去,而是忏悔我的现在;不但在你面前,怀着既喜且惧,既悲伤而又信赖的衷情,向你忏悔,还要向一切和我具有同样信仰、同样欢乐、同为将死之人、或先或后或与我同时羁旅此世的人们忏悔。”也只有当受造物在忏悔的过程中达到现在的明彻,造物的主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才是一个不变得存在。
《忏悔录》写下,《忏悔录》打开,忏悔都不再是过去的标记,“忏悔已往的好处,我已经看到,已经提出。”重要的是“写这本《忏悔录》的时候我是怎样一个人”,我不是被那些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不是听过故事或被谈到过的我,而是有内心世界“真正的我”,这个“真正的我”是走向内心,是拥有爱的我,“爱告诉他们我所忏悔的一切并非诳语,爱也使我信任他们。”爱是主对我的爱,是我对主的爱,更是一种我成为主的一部分而变成整体的爱,只有在整体而不变的爱里,主之存在才唯一,才是永恒,才是绝对,才是“一切来自你,一切通过你,一切在你之中”。
“只有你是绝对的存在,同样只有你才真正认识:你是不变地存在着,不变地认识着,不变地愿意着;你的本体不变地认识、愿意着;你的理智不变地存在、愿意;你的意志不变地存在、认识着;在你看来,受你光照的可变受造物,要和你一样认识你不变的光明,这是不合理的。”奥古斯丁如此说到主,在这里,一个是“绝对的存在”,一个是“不变地存在着”——前者是名词性的,后者是动词性的,名词性指向唯一的本源,指向“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的存在,动词性指向永恒,“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是行为不息,晏然常寂,是总持万机,一无所需,是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是“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是“爱而不偏,嫉而不愤,悔而不怨,蕴怒而仍安”,“你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计划;你采纳所获而未有所失;你从不匮乏,但因所获而欢乐;你从不悭吝,但要求收息。”正是主的“绝对的存在”和“不变地存在着”,才使得忏悔永远指向那个现在的我,皈依的我,明彻的我,以及让人看见内心的我。
而从不知到所知,从黑暗到明彻,从忏悔的过去到忏悔的现在,奥古斯丁的信仰历程是不是就被分割成两部分?就像罪恶的自身和被照耀而明彻的自身一般,是两个不同的自我?或者在爱所缺失的岁月里,他如何一步步追寻那道光?为了抵达现在的我而回望过去的我,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检阅了自己所经历的人生之路,而在这段交织着黑暗和明彻的人生之路上,罪恶的自身成为他自我审视的一个对象,他就是将这个自身先放置在现在的对面,看见一个“真可恨”的人,看见一个需要怜悯和拯救的人,看见他身上的罪恶,才能使自己在忏悔过去而抵达现在中成为主的一部分,才能皈依于主。
“天主,请你俯听我。人们的罪恶真可恨!一个人说了这话,你就怜悯他,因为你造了他,但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主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罪恶来源于自身对主的无知?童年时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对父母发怒,还要打他们、损害他们、责罚他们;为了能日后出人头地,为了擅长于人间荣华富贵而听从欺骗的教诲;喜欢游戏,喜欢因打胜人而自豪,喜欢听虚构的故事;不喜欢读书,并且恨别人强迫我读书,还欺骗伴读的家人,欺骗教师和父母;从餐桌上偷吃东西,满足口腹之欲,或收买其他儿童从事彼此读喜欢的游戏,在游戏中又争强好胜,满足了日益向荣的虚荣心……这是童年的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而到了青年时代,欲望似乎并没有被遏制,“我青年时一度狂热地渴求以地狱的快乐为满足,滋长着各式各样的黑暗恋爱,我的美丽凋谢了,我在你面前不过是腐臭,而我却沾沾自喜,并力求取悦于人。”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和阴沉的情欲,在粪土般的肉欲中得到满足;追求恋爱的对象是因为“只想恋爱”;恨生活的平凡,缺乏滋养的粮食;在通向聚讼的市场中希望获得称誉,不惜信口雌黄……
“我把肉欲的垢秽玷污了友谊的清泉,把肉情的阴霾掩盖了友谊的光辉;我虽如此丑陋,放荡,但由于满腹蕴藏着浮华的意念,还竭力装点出温文尔雅的态度。”在奥古斯丁看来,这都是欲望使然,不管是争强好胜还是信口雌黄,不管是在勃发的青春中恋爱,还是在所谓教书中希望获得名利,不管是在谎言中朗诵一篇歌颂皇帝的文章,还是在追求知识上满足“目欲”,都是欲望的罪恶,“这些是主要的罪行,根源都由于争权夺利,或为了耳目之娱,或为逞情快意,有时源于二者,甚至兼有以上三种根源。”在被欲望劫持的生活中,奥古斯丁得到了满足,但是又充满了痛苦,“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爱缺点本身。”——这是一种忏悔于现在而认识到的罪恶,而这样的忏悔中,奥古斯丁其实在寻找着那个“伸手挽救我”的主。
这是一个思想和信仰逐步转变的过程,奥古斯丁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于母亲的信仰,对于基督教,奥古斯丁因沉溺于自我的欲望中而无视,“你通过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在我耳边再三叮咛。可是这些话一句也没有进入我的心房,使我照着做。”十六岁是离开家乡去往了“辽远的地域”,“这时,无耻的人们所纵容的而你的法律所禁止的纵情作乐,疯狂地在我身上称王道寡,我对它也是唯命是从。”后来在马杜拉城开始攻读文章和雄辩术,父亲的望子成龙又让奥古斯丁去往迦太基留学,在经历了辍学之后终于来到了迦太基,奥古斯丁又感受到了“周围沸腾着、震响着罪恶恋爱的鼎镬”。一篇西塞罗的著作《荷尔顿西乌斯》,使得奥古斯丁在“不再着眼于辞令”的情况下,开始走近主,“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但是在这本书里她找不到基督的名字,“一本书,不论文字如何典雅,内容如何翔实,假如没有这个名字,便不能掌握住整个的我。”
走近又离开,在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的九年里,奥古斯丁说自己陷溺于种种恶业之中,在自惑惑人,自欺欺人中生活;后来向当时的一个星士请教,在推演星命中将基督教真正的、合乎原则的虔诚排斥了;在教书的过程中,奥古斯丁一起研究学问的知己死了,“死亡抢走了我的朋友,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对死亡的害怕让他逃离了家乡,来到了迦太基的奥古斯丁写作了一本名为《论美与适宜》的书,当他把美和适宜分开来,其实是用思想“巡视了物质的形相”,“美是事物本身使人喜爱,而适宜是此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和谐,我从物质世界中举出例子来证明我的区分。”正是这种区分使得奥古斯丁陷入到了一种二分法的痛苦中,也是他思想是否突围的关键。
美和适宜的区分是奥古斯丁观察形相而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区分法,从物质到精神,更是一种二分法,所以奥古斯丁审视自己的罪恶时,也认为,恶是一种实体,而且具有生命,他把无性别的精神体吗,命名为“莫那特斯”,把罪恶中的愤怒、放浪中的情欲等的恶命名为“第亚特斯”,两种实体的存在,其实是奥古斯丁为罪恶的自己寻找借口,因为恶如果是一种存在于无灵之物的分裂的本体,它的对面就是善,而善自然也是一种本体,两种对立存在的本体完全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存在,这种观点在奥古斯丁接触了摩尼教之后更加深化了一步,摩尼教主教福斯图斯“优美的辞令”并没有吸引奥古斯丁,相反,吸引他的是渊博的知识和擅长自由艺术的声誉,并在这种知识体系中找到了恶作为本体的认识论,即使从迦太基到罗马,奥古斯丁也在摩尼教的影响下开始认识善与恶的本体:在摩尼教看来,恶是一团可怖的、丑陋的、重浊的东西,或是一团飘忽轻浮的气体,他们将恶命名为“地”,是“在地上爬行的恶神”,从摩尼教的教义中,奥古斯丁认为,善和恶是两个对立的本体,“二者都是无限的,恶的势力比较小,善的势力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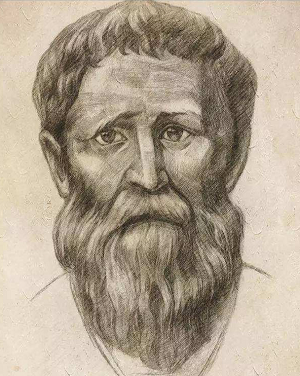 |
|
奥古斯丁: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愿意赞颂你
|
善与恶是独立的本体,是对立的存在,都是无限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其实是二元论的,在这个二元论的世界里,恶的出现也就成为了必然,而罪恶的人也只不过是被恶的本体和恶神所控制。一次偶然的机会,市长玛库斯派奥古斯丁去米兰,正是这次米兰之行,奥古斯丁拜谒了安布罗西乌斯主教,也从此开始了他关于信仰的真正转变:他又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认识到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形而上的神性”的真理,从这种神性中认识到了主的无限,“我已经确信你的实在,确信你是无限的,虽则你并不散布在无限的空间,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有者,绝对没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易,其余一切都来自你,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它们的存在。”他又读了使徒保罗的著作,保罗仰瞻主的神功伟绩,“我不禁发出惊奇的赞叹。”从安布罗西乌斯到西姆普利齐亚努斯,从柏拉图著作到基督的“道”,奥古斯丁终于慢慢从二元论的世界中走出来,世界不是有一善一恶的两个对立的灵魂,也不具有两种对立的本体,也没有两个对立的本源,甚至揭露这一切在奥古斯丁看来,就是主的意愿,“你,真实无妄的天主,你是反对他们,驳斥他们,揭露他们”。
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发病之后重新回到米兰的奥古斯丁开始接受洗礼,而这次洗礼仪式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奥古斯丁的私生子阿得奥达多斯,私生子的身份带着奥古斯丁罪恶的烙印,而洗礼就是将这种罪恶去除;那一年奥古斯丁人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便是母亲的病故,这个具有圣德的至诚灵魂离开躯体,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绝不只是母亲逝世的伤痛,而是让他认识到了皈依于主的决心,“通过我的忏悔而获得许多人的祈祷,比了我一人的祈祷能更有力地完成我母亲的最后愿望。”从垢污的深坑中爬出来,从错误的黑暗中站起来,作为上帝婢女的母亲给了他的就是一种永恒的爱,也在这灵魂离开躯体的最后死亡中,奥古斯丁彻底认识到了自己必须在忏悔中走进自己内心,必须从过去抵达现在。
奥古斯丁信仰的转变,并非只是对主的认识发生了变革,更重要的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彻底转变。在“过去”的奥古斯丁看来,善与恶是被分割开来的,它们各自拥有实体,而上帝之存在,也是一种实体存在,甚至是在一种空间中的存在,“按照这想法,天地大的部分占有你的大,小的部分占有你的小;万物都如此,则大象比麻雀体积大,因之占有你的部分多,如此你便世界各部分所分割,随着体积的大小,分别占有你多少。其实并不如此。你还没有照明我的黑暗。”所以不占空间的、不散于空间、不聚于空间的,被看成是虚无,而造物的大地、海洋、空气、星辰、树木、禽,和肉眼看不见的穹苍、一切天使和一切神灵,在奥古斯丁看来,也是在思想之前的存在。而在忏悔的“现在”,奥古斯丁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诠释《圣经》第一卷,其中就明显建立了一元论的思想体系。
上帝之道是什么?道是言,是创造万有的言,而言又是一切的存在,“‘道’,这‘道’是‘和你天主同在’的天主,是永永不寂的言语,常自表达一切,无起无讫,无先无后,永久而同时表达一切,否则便有时间,有变化,便不是真正的永恒,真正的不朽不灭。”道是元始,是真理,道就是“绝对的存在”,这种绝对的存在便是唯一,“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不造一物。因如果造,那么除了创造受造之物外,能造什么?”空间如此,时间也如此——奥古斯丁尤其对于时间的阐释,体现了唯一和永恒的道:时间是由主创造,时间不是被分割成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是一元的,是现在的,“将来尚未存在,尚未存在即是不存在;既不存在,便绝不能看见;但能根据已经存在而能看见的预言将来。”人们正是通过期望、注意和记忆的三个阶段来定义时间,“并非将来时间长,将来尚未存在,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去时间长,过去已不存在,所谓过去长是对过去的长期回忆。”
所以“绝对的存在”只有一个唯一的源头,唯一的造物者,唯一的主,而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期望、注意和记忆中体现的是“不变地存在”,“只能从空无所有之中创天地,一大一小的天地;由于你的全能和全善,你创造了一切美好:庞大的天和渺小的地。除了你存在外,别无一物供你创造天:一个近乎你的天,一个近乎空虚的地,一个上面只有你,另一个下面什么也没有。”而对于人自身来说,人有存在,有认识,有意志,“我存在,我认识,我愿意:我是有意识、有意志;我意识到我存在和我有意志;我也愿意我存在和认识。”但是三方面并不是可分割的,它是一体的生命,一体的思想,一体的本体,它就是自身,这个自身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的同一——自我之同一,也是主之同一,因为受造物都是主所造,“一切来自你,一切通过你,一切在你之中”;另一方面,自我的同一是主的制造,“哪一人能使另一人理解这一点?哪一位天使能使别一位天使理解?哪一位天使能使世人理解?只能向你要求,向你追寻,向你叩门:唯有如此,才能获致,才能找到,才能为我洞开户牖。”
没有过去和未来,一切都是现在,没有恶和善的本体,一切都是道,现在是一切,道是万物,而主便是存在和生命合二为一,“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所以在对过去的忏悔中,在个体的成长中,被看见而看见一种“绝对的存在”,看见而被看见一种“不变地存在”,“永恒的真理,真正的爱,可爱的永恒!你是我的天主,我日夜向你呻吟。我认识你后,你就提升我,使我看到我应见而尚未能看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