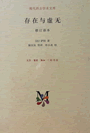 |
编号:B83·2150517·1171 |
| 作者:【法】让·保罗·萨特 著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14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68.00元亚马逊34.30元 | |
| ISBN:9787108050984 | |
| 页数:762页 |
“他人即地狱”是萨特流传深广的思想,个体有了自由,必须面对他人,我们两个人不能成为一个人,其根源就我们的意识多样性。而1943年《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出版则宣告了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的诞生,他开始运用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和哲学词语述说对世界的理解:人即自为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性,他永远处在变化中,而且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的。正是由于它具有时间性,“自为的存在”是一种总是显示为“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 面貌的存在,人是什么只是指他过去是什么,将来并未存在,现在是一个联系着过去和将来的否定,实际上是一个虚无。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正是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人赋予对象以意义,但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
《存在与虚无》:这场战争就是我的战争
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自我,而是自我在场,是其所是的存在不可能是自由的。自由,显然就是在人的内心中被存在的、强迫人的实在自我造就而不是去存在的虚无。
——《第四卷 拥有、作为和存在》
在场仅仅是存在物在场,它在我们曾经听说的书目里,它曾在老马的办公桌上,它曾是三联初版的图书,就在2010年的某个时间点被看见被记录甚至被拍摄,但是它在七年前甚至更久远地存在,并不是以显现的方式存在,或者说,它只是在一个相对的时间,相对的位置,相对的过去,相对的身体,相对的立足点,以及我和老马相遇的某种基本关系里出现——出现而不显现,甚至没有现象的观念,当然更没有带进存在的世界。
但是七年之后呢?让·保罗·萨特的著作显现了吗?2014年09月的新修订版表达了自身吗?762页的图书在场了吗?存在物之存在,是需要显现在现象里,是需要被显现为一种绝对的存在,当在一个自由拥有,自由阅读,自由进入自我时间里的一种存在开始作为的时候,是不是会看见虚无?是不是会显现乌有?是不是会进入自为?或者说会不会在其所是之外的行动中、在欠缺的否定性中真正获得自由?“自由,显然就是在人的内心中被存在的、强迫人的实在自我造就而不是去存在的虚无。”并不仅仅是从第一页翻阅到最后一页的作为,并不只是在自己支配中隐约看见在场,也不是以主动显现的方式去存在的虚无,而是在内心中洞察欠缺,在自我中看见责任,在存在中我思,超越七年,超越过去,超越存在,而在“一切就是将来”中走向本体论的存在。
七年,无非是时间的一种改变而已,而这样的时间是物理形态的时间,甚至是严格区分了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时间也变成了存在物,在被看见和被打开的最初意义上,存在物的存在其实并没有真正显现。但是存在物被显现为一种现象,并不是将存在纳入到了本体论范畴,而是要在“相对-绝对者”的观念里,让显露存在物的那些显象,既是内部的也是外表的,既是存在也是现象,也就是只有让两者成为同等,才是真正破解那些使哲学家陷入困境的二元论,成为其自身的绝对表达。
绝对的表达,萨特用了“系列的原则”破解这样的二元论,无论是显象还是本质,无论是对象还是存在,无论是潜能还是活动,在相对意义上,都设置了二元论的窠臼,甚至以一种内部和外表的方式割裂开来,而在“系列的原则”下,现象是什么,绝对是什么,也就是说,“它就是像它所是的那样的自身揭示”,现象就是本质,对象就是存在,潜能就是活动,而这样的原则并不是取消二元论,而是转化了一种新的二元论:有限和无限的二元论:有限的显现死为了在有限性中表明自身,但是它要求被超越的同时就已经走向了无限,从一个侧面走向另一个侧面,又从侧面之中走向侧面之外,它不是如康德所说的“返回存在”,而是“一种不再与任何存在对立的‘显现’”。
从有限走向无限的存在,是怎样一种本体论的存在?萨特认为,存在被揭示出来,并不是用对象构成本质,而是对象和本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本质不在对象中,而是对象的意义,是把它揭示出来的那个显现系列的原则。”存在物是其本身,而不是它的存在,存在不是在场,不在场也揭示存在,所以这种本体论的存在就具有一种超现象性,它超越的是感知和被感知的形而上学设定,超越的是意识和事物之间的对立,所以,“一切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作为存在着的意识存在的。”意识就是纯粹的显象,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和事物保持着真实的关系。也只有在意识中,存在才成为被感知的存在,才能有一个感知者,也正是由于存在表现为意识,认识才具有了本体论的基础,一切现象也都是相对的。所以萨特的本体论证明的轨迹已经清晰,那就是现象的存在有超现象性,不是从反思开始的我思,而是从感知者反思前的存在开始,所以对象在意识中是它的不在场,而不是它的在场,应该由于它的虚无,而不是由于它的充实。
“意识是这样一种存在,只要这个存在暗指着一个异于其自身的存在,它在它的存在中关心的就是它自己的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意义是使存在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意识超越存在物走向本体论,走向存在本身,它是非创造的,是自因的,是它自身,这种特性被萨特称为:存在的“自在如一性”,也就是说,存在是其所是,它脱离了时间性,所以现象的存在具有三个特点:存在存在,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
存在是其自身,存在是其所是,存在就是存在。这是存在的本体论,但是这样一种存在却并没有在人的意义上完成命名,也就是说,它如何在形而上学的“考问”中存在?我们的考问其实针对的是“在世的人”这个整体,它可以化为两个问题,在世的综合是什么关系?如果使任何世界的关系成为可能,人和世界应该是什么?这关涉到关系论的复杂性问题: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人的非存在与超越的非存在之间的关系。很明显,萨特引入了另一个概念:非存在,非存在是对存在的“否定”,是对存在的拒绝,而实际上非存在在本体论上也是存在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否定和拒绝指向什么?举列来说,当走进咖啡馆去找皮埃尔的时候,“皮埃尔不在”的命题指向的是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却以虚无的方式显现出来,否定是虚无的起源还是虚无是否定的基础?因为萨特发现,“皮埃尔不在”这个否定状态是急于从寻找的过程中凸显出来,“力图要独立出来”,但是结果却并不是在虚无中上升到基质之上,相反,却“重新落入了这个基质的未分化状态”,甚至消融在基质中——虚无从基质中独立出来,却最终消融在虚无中,这是双重虚无化的结果,这便是非存在的存在方式:“一个存在(或一种存在方式)通过否定被提出来,然后被抛向虚无。”而当虚无纠缠着存在便表现为非存在。
那么,虚无来自何处?虚无假设了存在,其目的是否定它,所以虚无不是产生存在的原始虚空,借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自知其无知)”,否定的“什么都不”其实是存在的整体一部分,也就说说,存在先于虚无并且为虚无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存在根本不需要通过虚无而被设想,人们能透彻地考察存在的概念,而从中找不到一点虚无的痕迹。”存在先于虚无,虚无又纠缠着存在,所以虚无的问题是:“只有在虚无中,存在才能够被超越;存在才组织成世界”。这样的虚无,就是人能够使自己独立出来的虚无,也就是一种自由的可能:“自由正是通过分泌出他自己的虚无而把他的过去放在越位位置上的人的存在。”
越位的位置,似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虚无是一种否定和拒绝,人在存在中如何使自我否定成为可能?如果把否定转向自身,是不是就是自欺?萨特认为,自欺并不是一种说谎,而是对我自己“掩盖真情”,也就是在一种区别中,甚至在一种逃避中,来发现同一,来肯定整体,也就是说,自欺“是使我按‘不是我所是’的样式是我所是,或按‘是我所是’的样式不是我所是”,它的可能条件是:反思前的我思,在反思中,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以“乌有”的方式“逃避人们不能逃避的东西,为了逃避人们所是的东西”。
所以,在存在的非存在现象里,“否定把我们推到自由,自由把我们推向自欺,而自欺则把我们推向作为可能性条件的意识的存在。”而这种自欺的自由就是进入到“反思前的我思范围”中来。我思故我在,当笛卡尔做出这样一个经典判断的时候,那个“我”其实像上帝一样,是“一个不是其固有基础的存在”,也就是说像上帝存在一样,具有偶然性,偶然性的存在被萨特命名为“自在的存在”:是它所是的存在,它不能“有”可能,在它之中没有自欺,也就没有自由。所以在自在的存在之外,要想达到自由,就必须有另一种存在,那就是自为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规律作为意识的本体论基础,就是在对自我在场的形式下成为自身。”
存在被抛入虚无,虚无的否定性是一个彼在的概念,也就是存在的一个洞空,“是自在向着自为由之被确立的自我的堕落。”而这种堕落也是消解的过程中“恢复自身”,所以说,自为的意义是是使自在的偶然性变成事实的必然性:“自为所以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由自己奠定的。”而这种奠定的方式就是“人为性”,所以很明确,从自在到自为,从偶然性到必然性,萨特所要建立的“人为性”,其意义就是超越笛卡尔我思的“瞬间的整体”,在自为和自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必然“欠缺”:“自为为了成为自我而欠缺的东西。”
欠缺在何处?在时间性里,在超越性里,瞬间的整体就是一种狭隘的“在场”,连过去也仅仅是“我作为被超越物所是的自在”,所以在自为的存在中,时间性的意义就在于未来:“只有一种存在,可能拥有一个未来,那就是要成为其存在的存在,而不是仅仅是存在的存在。”所以抛却静态的时间维度,在超时间性的意义上,“将来就是我,因为我期待着我,就如同期待一个对超乎存在之外的某一存在的在场那样。”这是自为存在在时间性意义上的命名,同时,在超越自身意义上,萨特所建立的存在模式是:为他。“既然我总在我所是的东西之外,是向我本身的将来,我面对其在场的这个就向我显现为我向着我本身所超越的某物。”
不管是我思故我在,还是超越时间的“我思,故我曾在”,我为我,实际上是一种唯我论,我遮蔽了一切,甚至虚无的否定,甚至欠缺的存在,我说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我所不是的尴尬和危险,所以“为他”并不是自为之外的补充,而是自为“人为性”的一种超越。他不是我之外的他者,不是不在场的他者,不是直观的经验对象,而是“注视着我就足以使我是我所是”的主体,他的存在就是破除“唯我论”的障碍:“我通过我的经验经常追求的,是他人的感觉,他人的观念,他人的意愿,他人的个性。”而这种我和他的关系其实是一体的,它呈现的方式是:被别人看见和看见别人。这两种方式也是一体的,而其目的,在萨特看来,是“我不再是处境的主人”:“这样,我的为他的存在,即我的“对象的我”,就不是一个与我相割裂的并困在一个异在的意识中的形象:而是一个完全实在的存在,是作为我的面对他人的自我性和他人面对我的自我性的条件的我的存在。”
从身体的揭示,到爱、语言、受虐色情狂等态度而衍生的注视、占有、自由,从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等态度,变成矛盾、斗争,无论是那一方面,只要是“他者”为我们提供了“为他”的人为性,提供了自为与自在的关系,提供了行动的永恒可能性,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显示自为的本质特性。所以在他人的在场而达到自为的我思,我在,萨特终于把真正的自由赋予一个永恒意义的主体,那就是“拥有、作为和存在”。在他看来,拥有、作为和存在都是人的实在的基本范畴,而它们都趋向于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自由才是所有本质的基础,因为人是在超越了世界走向他固有的可能性时揭示出世界内部的本质的。”所以自由的自我不是人的自我,而是自我在场,是在其所是的存在中也有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
但是自由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去存在的虚无,它总是被某种处境所制约,在给定物面前被照亮,这其中包括我的位置、我的身体、我的过去,我的立足点和我与他人的基本关系,而自由意味着这逃避这一切,这种逃避的动力就是自由的人为性,所以自由是自我造就,就是承担责任,就是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这场战争就是我的战争”,正如若尔·罗曼所说,“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而牺牲的意义就是“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够减轻这重量”。
我的战争是自由的战争,是存在的战争,是虚无的战争,从存在和对象,本质和存在,潜能和活动的二元论,到有限和无限的二元论,其实萨特的努力是从形而上学的我思变成了伦理学的自为:“自为永远是悬而未决的,因为它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延期。”所以在自由意义上,萨特所寻找的是一种“道德的前景”:“一种面对处境中的人的实在而负有责任的伦理学将是什么。”在这个伦理学意义上,萨特提出了关于自由的问题:“只是由于自由被当作就其本身而言的自由,它就能中止价值的统治吗?”“自由由于把本身当作目的,它逃避了一切处境吗?”“它越是作为有条件的自由把自己投入焦虑中、越是作为世界赖以存在的存在者收回它的责任,它就越是明确地、个别地处在处境中吗?”
存在在意识中被显现,非存在把存在抛向虚无,不管是自在的存在,还是自为的存在,自我在场的意义就是去除偶然性达到必然性,而自由的必然性需要一种人为性的“自欺”和欠缺吗?当给定物被照亮的时候,是不是就完成了去存在的虚无?当人在他者的注视下让自身在场的时候,是不是又重新跌入到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所以自为的延期,自由的悬置,对于萨特来说,似乎保留了另一个空位:“所有这些问题,都把我们推到纯粹的而非复合的反思,这些问题只可能在道德的基础上找到答案。”而道德的前景上,他或者已经想好了人为性的自为命题:“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