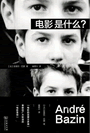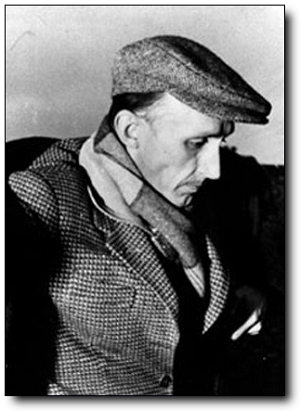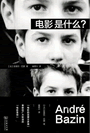 |
编号:Y22·2180319·1458 |
| 作者:【法】安德烈·巴赞 著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
| 定价:68.00元亚马逊53.50元 |
| ISBN:9787100125147 |
| 页数:396页 |
《电影是什么?》,书名是一个疑问句,当在这个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的特殊纪年,打开这一本被誉为 “电影圣经”的书,是不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种应景式回答? “电影的亚里士多德”安德烈·巴赞在电影理论研究中树立了一座卓越的里程碑,他的现实主义美学深刻影响了世界电影的发展,他宣扬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和真实美学也形成了与蒙太奇理论不同的电影美学体系,开拓了电影研究的领域。正是由于巴赞的努力,电影才成为严肃的研究课题。本书为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巴赞发表的一系列高质量影评和电影评论的结集,涉及电影本体论、电影社会学、电影心理学和电影美学等诸多话题,是研究巴赞和当代电影美学的必备读物。
《电影是什么?》: “隐形人”也应当披睡衣
把这种戏剧遮起来,我可看不下去!
——《戏剧与电影》
13岁的冬尼应该在奔跑:他沿着铁丝网向前,穿过树林,穿过石桥,穿过农庄,一直向前奔跑,即使前面是大海,没有路,没有船,被阻隔成茫然的世界,在没有出口的地方他依然要奔跑,在2分30秒的长镜头中奔跑,在自己的时间里奔跑,在电影里奔跑,即使电影最后落幕,一个渴望自由的孩子也依然在无休止地奔跑。
弗朗索瓦·特吕弗,《四百下》,99分钟的剧情,这些都是属于这部1959年上映的电影,但是,当电影终结的时候,为什么那种奔跑却没有终点?他跑出了银幕,跑出了时间,跑出了电影,他是否也跑出了我可能看见的世界?但是当这一部电影的剧照出现在一本名叫《电影是什么?》的图书封面上的时候,最后的奔跑是不是就此戛然而止?其实是一双眼睛,在封面的平面世界看着我,或者说并不是只有一双眼睛,当封面被截开而成为三个部分的时候,是三双眼睛,不是重复,是从大到小的演进——在这个被分隔而产生变化的世界里,看与被看是不是应该成为一种呼应?或者说,变化产生的运动是不是反而在静态的封面中对我造成了奔跑的感觉?
2013年观看的电影,其实离我远去了,就像最后的大海一样,在时间中被阻隔了,但是冬尼没有停下奔跑,他在自己的时间里奔跑,他在99分钟的电影里奔跑,他在画框之外奔跑,而这种奔跑就是在打破电影这种 “遮片”的局部性——当安德烈·巴赞把银幕说成是给观众的一个 “遮片”时,他就已经指出了电影的本质: “当人物走出摄影机的视野时,我们认为他只是离开我们的视野,而依然如故继续存在于背景中被遮住的另一个地方。”
所以,那一双眼睛,或者说三双眼睛的变化在封面上存在就是打开了 “另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所探索的就是本书的书名: “电影是什么?”一个问号,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入口,有形的入口,看起来就像是有限的 “遮片”,而在 “遮片”背后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是冬尼无休止奔跑的世界,是只属于他的独立世界。但是巴赞在这个入口所提出的问题是:电影是什么?而不是 “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电影,指向电影的可能形式和意义,它的中心词是 “什么”,而电影是什么,却指向电影的本体,它的关键词则是 “电影”——于是,巴赞很自然从这个入口的问题为电影找到了答案: “创造出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存的理想世界。”
解读这句话,无疑巴赞是区别了电影和现实,现实是现实,而电影则是一个理想世界,但是这个理想世界却不是脱离现实的,甚至也不是现实的摹本,而是 “符合现实原貌”,并且在 “时间上独立自存”的,它和现实建立了某种关系,但不是照着现实,而是在时间是独立存在,也就是说,电影具有某种 “木乃伊情结”——死亡是时间赢得了胜利,但是用木乃伊的方式却把人体外形保存下来,使其又超越时间,获得了某种永生,这种不被遗忘,甚至抵抗现实时间的做法就是摄影作为一种 “文明的进步”技术而产生的基础, “降伏时间的渴望毕竟是难以抑制的,文明的进步只是把这种要求升华为合乎情理的想法罢了。”而且,摄影和绘画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以独特的方式具有 “本质上的客观性”,也就是用摄影机的眼睛代替了人的眼睛,而人仅仅是看见,摄影机也便在看见而记录中远离了人的介入,这便是巴赞所说的影像心理学: “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任何绘画作品都无法具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
所以摄影机拍下的影像就是一种客体影像,它能 “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而且它摆脱了 “时间流逝的影响”,所以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就在于: “摄影的美学潜在特性在于揭示真实。”客观性和真实性,而且又具有时间的独立性,这是巴赞建立的电影本体论,而电影的这种属性就是把一个 “完整电影”的神话变成了现实, “支配电影发明的神话,就是实现隐隐约约地左右着19世纪从照相术到留声机的一切机械复现现实技术的神话。”这个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是影像上不再出现艺术家随意处理痕迹的神话,是影像不再受时间不可逆影响的神话,所以电影之发明并非是什么是创造式的幻象,而是回到它的起点, “貌似悖理的是,一切使电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无非是使电影接近它的起源。”而这个悖理完全可以表述为: “电影确实还没有发明出来呢!”
悖理完全可以解读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技术上,就是不断从不完善的起点靠近完善, “影片的不完善恰恰证明影片的真实性,影片欠缺的部分正是冒险活动的反面印记,犹如凹形铭文。”巴赞从探险电影的拍摄中来阐述这种在技术层面的不完善,托尔·海尔达尔拍摄的纪录片《 “康-蒂基号”历险记》,镜头里的影像是不完美的,甚至是粗糙的、模糊的、抖动的,但是巴赞却认为这是一部 “最美的影片”,因为它展现了影片拍摄过程和不完整的探险活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影片本身就是探险活动的一个侧影。这种一致性就是巴赞所认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正是有真实和客观的意义,所以它是一种记录,是美的纪录片, “电影的见证就是人在事件中能够捕捉到的内容,这就要求人同时亲身参与事件。然而,这些从暴风雨中抢救下来的残缺片段又远比那些安排得毫无纰漏和天衣无缝的报道所叙述的内容激动人。”相反,投入巨资拍摄的《斯考特在南极》,有冒险,有危险,有死亡,但是在巴赞看来违背了客观真实的特点,而成为一部 “重新搬演的纪录片”: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模拟不可模拟的事物,重新搬演本质上不能复现的情境”。
所以不完善,只是技术上的不完善,却是真实的,客观的,这个观点巴赞在《电影语言的演进》中再次进行了阐述。他提出的问题是:电影声音的发明所引起的艺术革命是否适应了一场美学革命?在很多人看来,有声电影的出现,使得有声和无声形成了对立,使得电影具有了更多技术的可能。但是巴赞认为,有声和无声从来不是技术问题,通过造型和蒙太奇,无声电影本身就是一门完美的艺术,而有声的出现,无非是起到了从属和陪衬作用,也就是说和世界形象构成了对位,而仅仅从技术角度来说,1938年或者1939年的时候,有声电影也已经堪称经典,甚至臻至完美。所以他认为,有声电影的出现,是和无声电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也就是说,是表现手法的根本不同产生的观念对立,而这种观念、流派、风格的对立就从技术层面走向了艺术层面,而艺术上的完善,所需要的恰恰不是幻象式的完美,而是真实性上的完善——无论是蒙太奇还是景深镜头,其实都是电影在艺术上的探索,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真实性,就是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为根本, “在默片时代,蒙太奇揭示了导演想要说得话,到1938年,分镜的方法描述了导演所要说的话,而今天,我们可以说,导演能够直接用电影写作。”
所以为了真实性,为了现实主义,巴赞提出了 “禁用蒙太奇”的观点。蒙太奇被称为是电影的本性,是一种影像革命,但是当电影用蒙太奇来制造幻象,来实现美学意义,甚至成为创造含义的抽象手段,那么蒙太奇就是一种 “典型的范电影性的文学手段”,因为这样的蒙太奇 “使场景始终处于自己必然的非真实性中”,让·图兰诺的电影《异鸟》就是通过蒙太奇使之成为了 “库里肖夫利用莫兹尤辛的特写镜头所做的著名实验的极好图解”, “论科学性,它最为虚假,论审美性,它最欠功力”,而影片《红气球》和《白鬃野马》,同样是表现动物的拟人化,却是在 “被禁用的蒙太奇”中具有客观和真实的特性, “拿《白鬃野马》来说,卡玛克岛的风光、牧民和渔夫的生活、马群的习性是这篇寓言的基础,是这个神话的不容置疑的坚实依据。”
巴赞并非是反对蒙太奇,否定蒙太奇,在他看来,蒙太奇必须 “用于确定的限度之内”,这样就提出了他的原则: “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当两个或多个运动元素同时存在,就意味着时间需要独立性,时间的独立性是现实主义的保证,是电影纯粹状态的标志,是严守空间统一的基础,所以即使有想象,也不能违背这个原则,也必须有真实的空间密度,所以在这样一种禁用的原则下,巴赞提出了电影在审美上具有完整性的条件: “必须让我们既知道事件经过了特技处理,又能相信事件的真实性。”蒙太奇是一种技术处理,它不能违反真实性,所以那部由法国著名海洋学家雅克-伊夫·库思托和导言路易·马勒合作拍摄的电影《寂静世界》,就成为成功的电影,里面那个幼鲸被螺旋桨打伤又被鲨鱼吞噬而惨死的场面是巴赞认为 “最富光彩的时刻”,而这个时刻的意义就是在蒙太奇的处理中保持了真实性: “把拍摄下来的那些猝然出现的事件事后安排组接起来,以便把这些事件展示得流畅清晰又合乎情理,不破坏其真实性,这才是影片中最成功之处。”
电影的现实主义就是罗西尼《德意志零年》中 “道德含义或戏剧性含义从不浮现在现实的表层”的 “风格现实主义”,就是《血战七强盗》中 “既无象征,亦无哲理性蕴涵,也不见心理学踪影”的 “严格的经典情节”,是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中, “所有事件都不是必然的,都可能不会发生”的新现实主义,就是意大利电影《游击队》中 “具有特殊的纪录价值”的 “事实-影像”——当巴赞提出 “事实-影像”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开始了对于电影作为一种 “遮片”的独立性阐述,他认为《游击队》的电影叙事单元不是 “镜头”,而是 “事实”, “这是具体现实的片段,而现实本身是多面的和多义的,它的确切含义只是在悟出它与另一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后才能逆推出来。”所以从事实到影像的链条不是简单的过渡,而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巴赞所说的 “保持联想性关系”,而更重要的在于充分挖掘影像的离心特性,以构成电影叙述的内在特性。阿仑·雷乃在电影《凡·高》里,将画家的全部作品处理成一幅长长的画卷, “摄影机像拍摄任何纪录片一样在那里自由漫游”,就是通过事实这个入口进入到独立的影像世界: “我们从临‘阿尔大街’的窗户‘进入’凡·高的屋舍,然后走近铺着红色鸭绒被的床榻。而亨利-乔治·克鲁佐的电影《毕加索的秘密》中,用创作的时间延续完成了对于绘画艺术的 “第二次革命”, “克鲁佐最终为我们揭示出的是绘画,即存在于时间中的、有自身时间延续的、有生命的和有时还会‘死亡’的一幅画一如这部影片结尾。”所以他把这部电影叫做 “柏格森式的影片”,绘画这一事实通过 “影像”变成了电影化元素,在本质上就变成了时间性元素。
这种联想性关系并非是影像必须依靠事实而存在,当它进入其中之后,其实反而以离心的方式隔离了现实世界,而这种离心的银幕空间正是电影的特性,它区别于舞台空间具有的向心性, “银幕不是一个画框,而是仅仅把事件的局部显露给观众的一个遮片。当人物走出摄影机的视野时,我们认为他只是离开我们的视野,而依然如故继续存在于背景中被遮住的另一个地方。”局部暴露给观众,电影用画框使自己成为一个遮片,但是遮片并非是有形的局部世界,当莫里哀在《伪君子》里说: “请把您的乳房遮起来,我可看不下去。”其实是一种虚伪,而巴赞以以异轨的方式来否定对于 “遮片”的误解,其实就是要打开 “另一个地方”。
人们总是认为,戏剧舞台提供了一个演员 “在场”的空间,认为戏剧性是戏剧特有的灵魂,认为 “真实戏剧”是存在的,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 “前电影”,所以在拍摄所谓的 “舞台戏剧片”的时候,费尽心思搞 “电影化”。实际上,这种种的观点都是误读了戏剧和电影的本质区别,把电影看成是对更古老和更具文学性的艺术抱有自卑感而出现的矛盾心理。巴赞认为,舞台的确制造了一个演员在场的空间,是一种完整的演出,但是电影的演员也在场,电影也是完整的演出,而真正的区别在于电影是离心的,舞台是向心的, “电影使观众平心静气,戏剧剧使观众心猿意马。甚至当戏剧唤起最低下的本能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群体心理的形成,阻碍集体性复现表象的存在,因为,它要求的是个人的积极领会,而影片只要求消极的参与。”戏剧的观众永远坐在舞台之下,他们处在那一盏脚灯的保护之下,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隔离的,观众有限地参与到戏剧动作中,它的表演心理学辐射到观众那里,它打通了舞台世界和个体体验世界。但是电影却不同,观众是消极的,他只是独坐在那里, “我们仿佛躲在漆黑的室内,隔着半开半掩的百叶窗,独自欣赏一场演出,这是一场全不理睬我们的演出,是一场与世界相通的演出。”
电影就在那里发生,它制造一种离心效果让观众心平气和,而在本质意义上,它只是在被看见的时候成为 “遮片”,但是却无限延展到另外一个世界,在画框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但是这种独立并非是建立了和现实不一样的幻象世界,在巴赞的现实主义中,这个 “遮片”外的世界当然也是真实的, “电影以展现给观众的事物的永久真实性为依据。”即使隐形人,也是披着睡衣,也是抽着香烟,也是现实的存在,所以巴赞认为, “一部影片暂时就是大地万物,就是大千世界,或者可以说,就是大自然。”电影不是嵌入世界之中,而是代替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赞批判了事实和影像之间建立象征关系,否定《卡里巴李博士的小屋》中的表现主义。
影像具有客观性,电影必须表现真实世界,当一部电影 “创造出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存的理想世界”的时候,巴赞赋予了现实主义电影一种独立性,只是如此建立一种电影本体论的时候,却忽视了电影的观众心理学,在他看来,观众就是旁观者,就是通过锁孔窥见了事件, “锁孔里窥测就像闯入私宅,这是近乎淫猥的‘观看’。”当观众如摄像机一样 “仅仅是旁观者”的时候,所谓的真实性,所谓的客观性,所谓的现实主义如何评判?被动接受导演意图,被动进入不参与的世界,甚至去除想象、象征等主观性解读,或者 “遮片”真的是遮片,在画框之外的 “另一个世界”只是导演的另一个世界,甚至只是演员的在场,所以当观众像伪君子那样说: “请把您的乳房遮起来,我可看不下去。”或许真的不是虚伪,而是和那个理想世界的隔阂——偷窥而关闭,冬尼就永远在不可见的世界里,奔跑和不奔跑似乎都在不可见的世界里,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