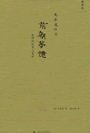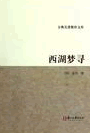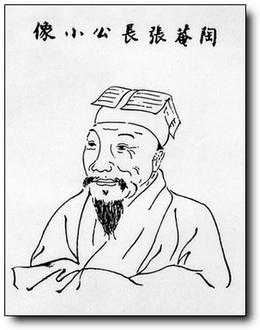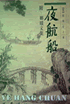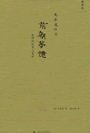 |
编号:Z58·2170419·1381 |
| 作者:史景迁 著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
|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
| ISBN:9787563385393 |
| 页数:212页 |
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尔后他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终。他反复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雾笼罩的路径,于眼前重现,诸多以往的嘈嘈低语,也咆哮四起……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无法切割。史景迁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层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借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前朝梦忆》:于是恨史之不赅也
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
——《前言》
历史是五十岁时的破床、病琴、残书和缺砚,以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的叹息;历史是六十七岁时看到梁鸿“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而发出“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的感慨;历史是近七十岁时安排好了身后之事,“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历史是最后自己写就的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那历史是看见的,是经历的,是预知的,最后却是如隔世的寂然,变废人的颓然,要葬身的凄然,成梦幻的枉然。
对于张岱来说,不管是经历还是预知,不管是身前事还是身后事,都是个人的历史,都刻印着““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的个人标签,而当一切成梦幻的时候,却也是折射着“国破家亡”的宏大叙事。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不仅是一个落魄文人的浮华与苍凉,更是一个国家的浮华与苍凉,而在这个体与国家的双重转变中,张岱的意义更是为17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标本,史景迁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到书写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思考朝代之更迭”,而张岱的《陶庵梦忆》给了他一个方向,“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能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思索的并非只是生活与美学,当明朝覆灭清朝更替,那场“梦忆”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只像《夜航船》一样,发现那个被忽视的小僧用“伸伸脚”的方式建立知识的独立品格?还是如《西湖梦寻》中“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的怀念?当史景迁把张岱定义为“史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张岱的个人历变中寻找国家叙事的脉络,从“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的个人经历中发现“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的历史思考,而当张岱用毕生精力完成《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三百万字的明史文本便成为浮华与苍凉的集体写照。
浮华与苍凉,其实是史景迁对于历史分野的注解,“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关于张岱我们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飞烟灭。”1644年,随着明朝的覆灭清朝的建立,国家历史横断为两种形态,而张岱的一生也被划定为两个阶段,前面的47年大体就是浮华的生活,而后面近40年便都是苍凉的生存。“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虽最后变成了张岱口中的梦幻岁月,但是却在其一生里成为浮华的见证,“在张岱眼中,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这是“书香门第说从头”的开始,这是“人生之乐乐无穷”的继续。
那时的张岱喜欢琴声,他发起缔结了“丝社”,他迷上了斗鸡,创立了“斗鸡社”,他喜欢看戏,精研唱腔、身段、扮相,还组织了戏班,“以余而长声价,以余长声价之人而后长余声价者多有之。”和伶人共娱乐,他还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他曾养过一头牛,研制做奶酪的方法,同样,他喜欢游船,喜欢赏月,喜欢喝酒,喜欢狩猎,甚至,他对于那些神秘女性也保持着足够的兴趣,那时和艺伎王月生常伴出南京城,游历燕子矶等胜景。四十一岁时,他还趁着吊祭故交的时候去观海潮,滔天巨浪奔腾而来的时候,张岱大开眼界。
四十一岁感受到的滔天巨浪,只是自然界繁华世界的一种映照,那时距离“一切都灰飞烟灭”的1644年还有六年,所以即使六年后历史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对于生活在“便寓、便交际、便淫冶”的张岱来说,仿佛也是极遥远的事。但是此种的纨绔子弟的生活在史景迁看来,也是张岱对于人生走向的一种注解,“张岱的癖好常常变来变去,难以持久,但是他写到这些癖好时,却仿佛是入迷极深,足以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安身立命的依托,是对于繁华的一种执迷,也是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化。
其实,这些繁华的背后,是张岱探寻精神意义归宿的努力,“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而已。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张岱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念“白衣大士咒”,这种祈求观音菩萨保佑的经咒也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第一种声音,“振海潮音,如雷贯耳”,即使母亲在万历四十七年去世,张岱的耳边也还会回响着诵经之声,“虽遭劫火,烧之不失也。”张岱到了晚年还说:“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之声。”而其实,这种声音使张岱更早地体悟了生命,万历三十三年,张岱的弟弟山民出生,这个早产儿身长不满一尺,体重只有几斤,气息甚微的他几乎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厄运写照,但是在之后的成长中,山民却成为集学者、诗人、艺术鉴赏家于一身的人,对此,张岱的感悟是:““吾弟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凡读书多识,不专而精,不骛而博,不钻研而透彻”。万历三十九年,张岱的祖母朱恭人到绍兴看三舅,结果突然去世。这突然的变故又加深了张岱对于人生无常的理解,在他为外祖母所写的祭文中说:“其生平丁骨肉之戚,抱零丁之苦,自为女、为妇、为媳、为母、为姑,未尝履一日之顺境,专一日之安闲。”特殊的生和死,特殊的生命意义,张岱所感悟的是那种韧性和坚忍,而这自然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重要一部分。
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则是在私人藏书楼里找寻和探索知识,对于张岱来说,家族对于功名的执着反倒让他感到厌烦,虽然祖父一直鼓励他,但是他始终没有通过乡试,也使得他从此和功名无缘,这是一种从科举制度化生存转向内心世界的改变,“他虽对科举制度心存芥蒂,但似乎借着对典籍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深刻看法,而能从祖父的功名中得到慰藉。”钻进藏书楼里,把自己的青春付之于此,并非是准备科举,而是在图书里发现内心的精神世界,所以张岱抛弃了祖父靠注疏读书的习惯,而是在书本中感悟:“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图书组成了张岱精神世界的一种景观,而身处其中,获得的东西远比所谓的知识,所谓的功名来得丰富,而这也是张岱转向内心世界的一种证明,所以当天启五年祖父逝世的时候,那些藏书散乱不见的时候,张岱深深地痛心:“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
“张岱笔下的文人世界充斥各种矛盾:一边是令人目眩的名望与机会,一边是郁闷、沮丧,甚至肉体的衰亡。”从生命里的曲折里感悟到了韧性和坚忍,从科举功名的无缘中发现了图书的精神力量,这两方面构成了张岱内向面的生活,但是沉浸在内向面的生活,其真正的意义何在?这便是张岱的疑问:“如果说搜罗藏书如此不易,但是飘零四散却是转眼间事,那么书又如何能引领人探索更深邃的知识?”飘零四散成为书的现实,而其实在张岱发出这样疑问的时候,他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飘零四散的时代。
母亲和祖父谢世,自己结婚生子,如此的生活对于张岱来说,是平淡的,终于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当父亲中了举人,在绍兴的张岱决定离开熟悉的安逸江南,前往陌生的华北,出走,并不仅仅是从江南到华北这种地理意义上的转变,而是从内向面生活向外向面生活的拓展,而这种向外的转向也使得张岱开始脱离个人的历史文本,进入到国家视野。在鲁王府看灯赏灯时,张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在变幻的世界里,到底是王宫内的烟火,还是烟火内的王宫?疑问其实是形而上的,像是庄生周梦一般,何来客观的真实世界,何来主观的精神世界?张岱游孔庙泰山,到舟山进香,到定海赶集市,这种浪迹天涯的感觉让张岱从繁浩典籍中挣脱出来,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意义,而这种寻找又是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化而为一,就像他在舟山进香时的感悟:“余登泰山,山麓棱层起伏,如波涛汹涌,有水之观焉。余至南海,冰山雪蠍,浪如岳移,有山之观焉。山泽通气,形分而性一。泰山之云,不崇朝雨天下,为水之祖。而普陀又簇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离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无山焉,为之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是有血而无骨也。有血而无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山泽通气,是一陆一海两种经验的融合,也是现实和信仰,知识和精神合二为一的体现。
但是张岱所感悟到的山泽通气还是繁华世界的一种印象,当这个时代被推向乱世的时候,张岱也终于“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天启七年,即1627年,明思宗将魏忠贤免职,旋即下诏逮捕魏忠贤,而魏忠贤最终自缢身亡。这一宫廷消息传到张岱耳朵里的时候,他其实正在撰写《古今义烈传》,在书中他颂扬的是忠诚的道德立场,对于一个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与权力的冷酷无情厌恶的人,张岱终于听说了正在发生的罪孽,而在现实意义上,他也看到了乱世的征兆,“绍兴一带有好些村落受旱灾摧残,农民竞相乞雨,看谁最灵验。四年之前曾有狂风大潮冲垮房合,树木连根拔起,绍兴城里也淹水。”而在之后,当明末的战争爆发之后,他也亲眼目睹了北方流民饿死而曝尸于杭州街头,同时,“随着父、祖俱逝,张岱面对迎面而来的种种过往,总得赋予某种秩序。”
家和国,似乎都在这一刻走向了某种崩溃,而这并非是巧合,当个体历史和王朝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张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时代,“不管对大难不死的张家人,或对明朝臣民来说,暴力与死亡层出不穷”,随着李自成占领背景,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清军最后入关改朝换代,张岱一家也被卷入到了危机之中,当张岱从绍兴家中出逃,那些藏书“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矢”。
王朝之覆灭,家族之流离,精神之崩坍,这便是变故的历史。顺治三年,张岱隐居山寺,他以拒绝的方式走进这个新朝代,隐姓埋名是去除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披发入山,贓贓为野人”则是消除了个体属性,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而这种种的举动在张岱看来,是为了赎罪。“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他现在所经历的种种劫难,是往日骄奢淫逸的报应,“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苧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枨,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这种报应观其实还是立足在自我历史之中,即使忏悔,对于这个已然发生变故的时代来说,其意义又在何处?
那灯火阑珊的意象,那琴声悠扬的记忆,那曾经伶人的静默,那母亲喃喃的诵经声,那千金古玩的闹热,那与好友的谈诗论艺,这一切都成为过往,都已不再,“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但是当他之后返回绍兴,在快园里诉说前尘往事的时候,这种报应观渐渐熄灭,号“六休居士”的张岱说:“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垣败屋安则休,薄酒村醪醉则休;空囊赤手省则休,恶人横逆避则休。”这是张岱从个体困顿的历史走出来的标志,“张岱的境界显然超脱了‘报应’的想法,从绚烂归于平淡。”而平淡的意义不是苟活,而是在历史的变故中寻找“繁华靡丽皆成空”的原因。
那便是张岱成为史家的开始,虽然张岱的历史首先着眼于外祖父、祖父、父亲的家族序列,三部家族传记让他审视的是和自己最近的历史,但是这只是一种历史的索引,“能为史者,能不为史者也;不能为史者,能为史者也。”张岱在《石匮书》序文这样说,也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为史者”,“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他寻找明朝由盛转衰的时刻,他剖析明朝沦亡的原因,他探究历史发现的脉络,在“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中,他找寻的是架构历史的原则,同时将张家的小历史纳进国史洪流之中。“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缺。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所以他在分析明朝覆灭的原因时,并不是归咎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认为,明朝“譬犹蠹木,献忠啄之,自成殊之,实群盗钻穴之”,明亡又“譬犹逐鹿”,是许多人共同为之。
康熙三年(1664),张岱完成《石匮书》,全书共两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启崩殂,勾勒出明朝十五位皇帝对权力与篡位的态度、边疆与对外政策、令人折服的战术与迂腐不化的战略、税赋与军费的难题、杰出的艺术天分与宏伟的宫殿营造计划。加之后来的《石匮书后集》,张岱的明史共计三百万字。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张岱在铺陈战争及朝代沦亡的全貌中,企盼能阐释各类人的生活样态——朝廷的叛变者和拥护者,殉国者、勇士和变节者,女人和男人,贩夫走卒和冠盖之士,画家和阉官,而忠贞思想的意义和重要性一直是贯穿其间的要旨。
而当张岱完成明史著作,他并没有一种释然的感觉,甚至开始再一次转向自我世界,再一次关注身后事,而这种转变其实也印证了张岱的某种宿命论:“死则无异,其所以处死者,则有异也。”自我的不同,不管生与死,都成为历史的一个样本,而这个样本在亲历者那里,永远对于无法主宰的历史投以无奈的一瞥,过眼云烟,都是梦幻,都成隔世,张岱分析自己时说:“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而这种自我嘲讽也正是张岱至始至终的一种个性,史景迁认为,“他曾享尽富贵却也尝尽磨难,不过其珊存著作却透露,他甘于寓居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那一部历史写满了浮华和苍凉,写满了寂然、颓然、凄然和枉然,或者只有在肉体衰亡之时,精神寂灭之时,才能安然在看得见的历史之外,所以最后张岱选择在“琅嬛福地”中结束自己那段历史,史景迁评价说:“这是他心目中的清修之地。空间清幽,井然有序,树木蓊郁。有流水、小丘、花草,有曲径通往溪涧。亭阁可眺望群峰。”
从生之内心回到死之内心,张岱或许最后进入的也是那隔世的梦幻。